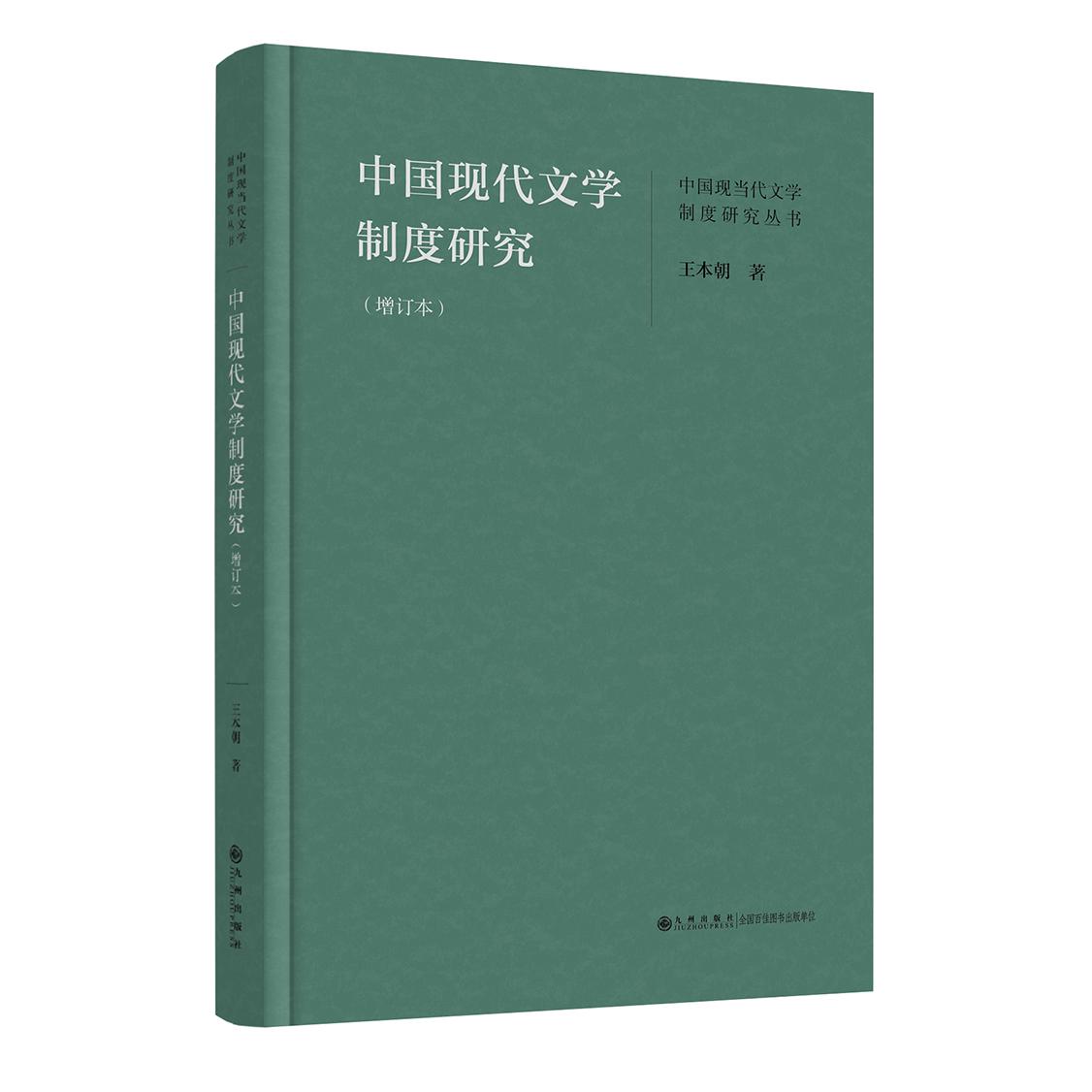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2.72
折扣购买: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ISBN: 9787522514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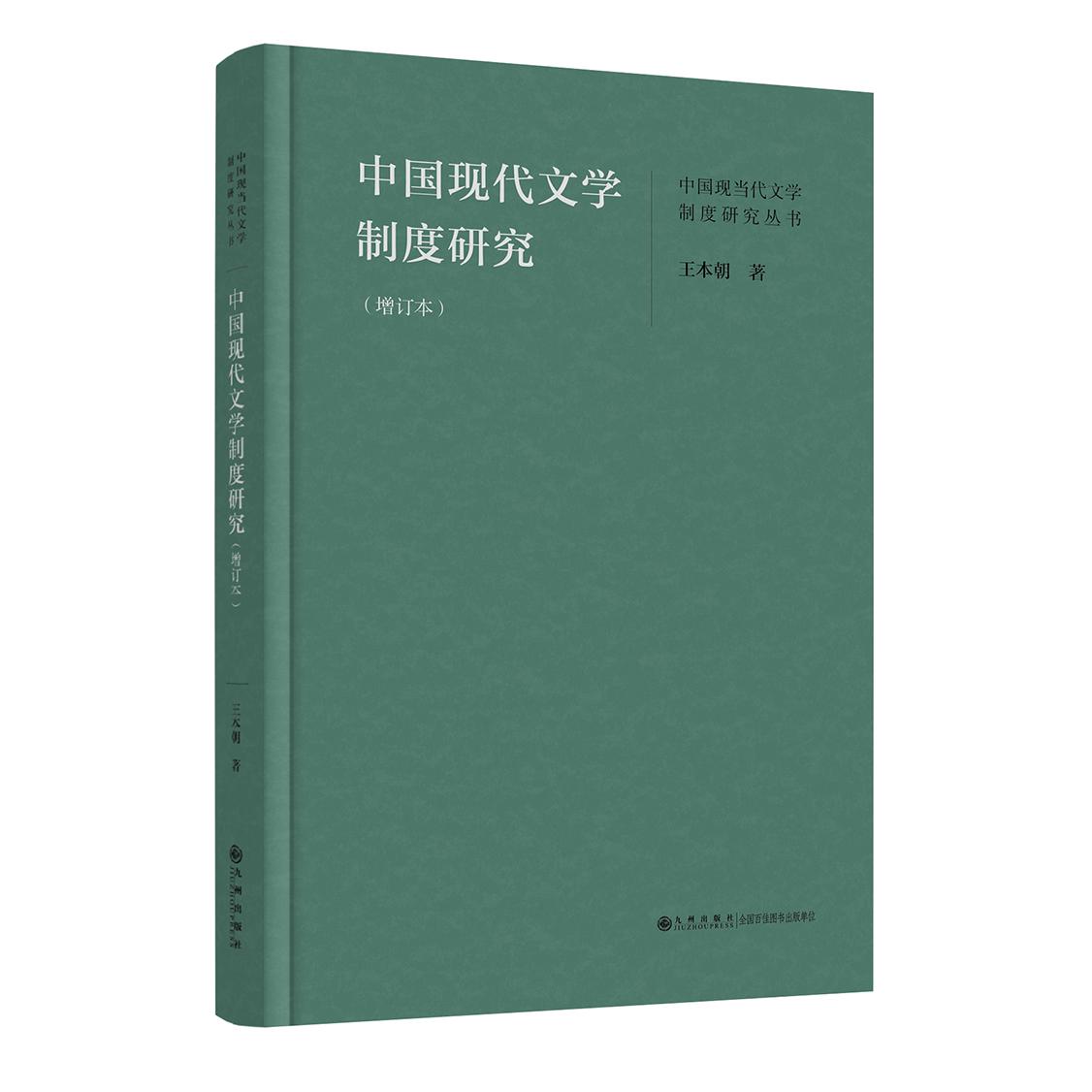
王本朝,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回到语言:重读经典》等10余种。
沈从文虽自称是乡下人,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也与文学制度生产密切相关。没有现代文学制度也就没有沈从文。当然,沈从文也超越了现代文学制度,他既在文学制度之中,又在文学制度之外,他比许多人要清醒得多。沈从文与现代文学制度的关系,是承受与反思、参与和批判的关系。有关沈从文如何在文学制度中成为新文学名家,创造出不少新文学经典,在此不作过多讨论。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在文学制度中得到认同和成功了的沈从文,如何看待文学制度,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刊物、文学作家和读者关系所提出的重造和重建性反思,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合理性与有限性。 一、新文学运动的重造 当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沈从文还在湘西的山山水水间奔走,在文学运动退潮之后,他即进入由文学运动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场域,拿起笔来尝试着写作,在新文学刊物上纷纷发表作品,并逐渐得到文学界的认同。后来,他又进入新文化的另一场域——在大学教书,于是,写作、编刊、教书成了沈从文参与的主要文学活动。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只是独立的文学个体,可谓文坛边缘人,但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了如指掌,有着执着的思考和呼吁,体现出过来人和旁观者的清醒判断。他曾经这样描述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变化,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他对新文学运动转向政治和商业,都持否定态度。后来,他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意见,且将新文学转向商品和政治看作文学“堕落”的体现,说它在写作态度上,“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几个业有成就的作者,在新的环境中,不习惯于‘商业竞买’‘政治争宠’方式的,不能不搁笔”。文学转向商业化和政治化,被沈从文作为新文学运动转向的标志。 在沈从文看来,“文运与上海商场和各地官场有了因缘,作家忽然多起来了,书店多起来了,社团多起来了,争夺也多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在发展,在膨胀,只是那点五四运动,却在慢慢的萎缩,从作者与读者两方面萎缩,末后只剩余一个零”。构成文学制度的相关作家、书店、社团、论战虽然多起来了,但文学作品却变得萎缩、凋零得很,因为“文学运动也就在商人、作家、票友、贩子、革命者、投机者以及打哈哈者共同支撑下,发展成像如今情形”。文学与商场和官场走在一起,商场的主人是商人,追逐的是金钱利益,文学被利益化和商品化,文学出版与发行所考虑的都是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商场的需求,满足社会大众的趣味,而不完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本身。 实际上,这种情形自晚清以来早已存在,还非常普遍,而沈从文自己也是依靠文学市场而成长起来的,依靠卖文为生而得以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他迫于生计,或为了养活家人,甚至以自残方式写作,损坏了身体,而出现吐血的情形。他在完成《柏子》后写道:“在北平汉园公寓作成,时年民国十六年。写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钧,即为用甲辰署名发表。两篇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着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如《某夫妇》:“在上海萨坡赛路写成,发表于《中央日报》之《红与黑》周刊,得七块钱稿费。”他因赶着写作而常流鼻血,也多次向友人报告病情,还想到了死,“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得勉强在支持。我常常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我活的意义”。“几天来一连流了两次鼻血,心中惨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 “打针失效,吃药不灵,昨天来流了三回,非常吓人,正像喷出。”他自己解释原因,“为什么缘故血又流了?是因为做文章,两天写了些小说,不歇息,疲倦到无法支持,所以倒了。在上海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像现代机器一样疯狂地创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 沈从文深受文学商业化之苦,但又不得不如此,因为他要依靠文学创作来生活。这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背景下,文学创作不同于古代的地方,《晨报副镌》曾有文章比较古今读书人写作的区别,“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当然,文学市场化,自然会影响到新文学的发展。对此,沈从文深有体会,“年来的商人,对于新诗的不尊敬处,反映出读者对于新诗的缺少兴味,略举小例:《梦家的诗》,是由自己花钱印行才可出版的。邵冠华的诗也是自己花钱印行。《君山》作者想把《君山》版权卖去,一时就无一个商人愿意承受。我为许多朋友,把诗集送到各处书店去问过,告他这诗白给书店印行也可以,书店主人似乎很聪明的打算了一下,结果还是奉还”。为什么书店不印行诗集?主要是读者太少,不挣钱,因为“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在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并且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实,便是从十三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来看,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反过来,符合大众趣味的,就成了流行文学,“现在说礼拜六派,大家所得的概念是暧昧的,不会比属于政治趣味的改组派,以及其他什么派为容易明白。或者说这是盘踞在上海各报纸附张上作文的一般作品而言,或者说像现在小报的趣味,或者……其实,礼拜六派所造成的趣味,是并不比某一种新文化运动者所造成的趣味为两样的。当年的礼拜六派,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文学的制度化生产,自有其利和弊。 并且,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产与五四文学生产也有分别,沈从文将分界线划在了北伐时期,包括文学报刊的衰落、职业作家的出现:“北伐成功却使副刊衰落,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原因是新的‘马上治天下’意识抬头,思想运动中缺少对于这个不祥之物的否定性,欲补救已来不及。商业资本复起始看中了文学,在一个不健全制度下形成一个新出版业。作家与商业结合,产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家与政治结合,产生了个政治文学。经营文学运动,为办杂志和死丧庆吊的集会,两者所作成的新的变化,即共同结束了副刊的生命。表面上即存在,也失去了本来的重要作用。何况事实上副刊由不足重视已慢慢消失。”北伐战争是一场国民革命,它制造了另一种革命文学,却被沈从文看作新文学生产方式的临界点。 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在上海,成了职业作家。他以每册100元价格将小说出售给上海街头小书店。仅在1928—1929年间,他的作品就遍布了上海所有的杂志和书店。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人间、春潮、中、华光、神州国光等书店都出版了他的作品集。1930年,沈从文以自己九妹的口吻所写《我的二哥》一文提到,到1929年底,沈从文创作了单独印行的作品“约计有三十七种,其中有十六种尚未出版”。对27岁的沈从文来说,这么大的创作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收到了“天才”“名家”等称号,却自称“文丐”。 ………… (注释略) 1. 以翔实的一手史料,客观分析、理性对待现代文学独特的制度与现象,充分挖掘其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扛鼎之作。 2.对原著全面增删修改,增订10多万字,体系完备,材料充分,分析丝丝入扣,结论鞭辟入里,读来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