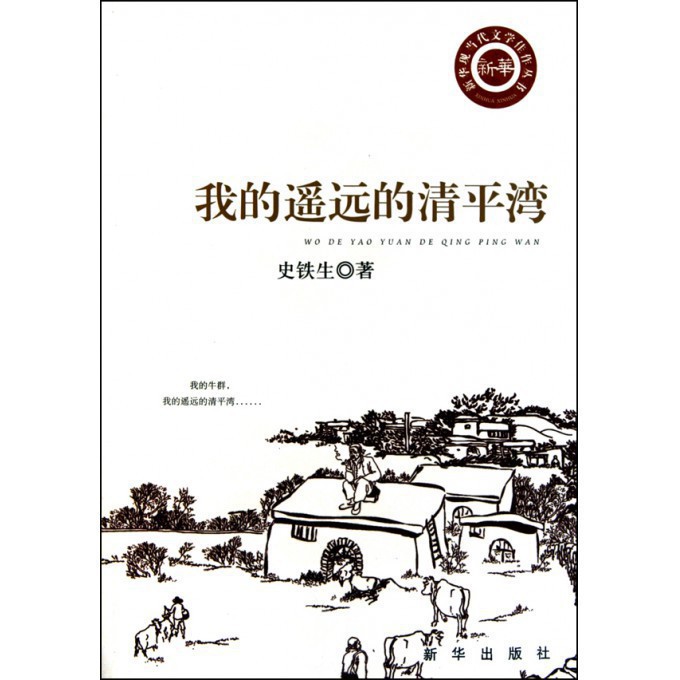
出版社: 新华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0.20
折扣购买: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新华现当代文学佳作丛书
ISBN: 9787501193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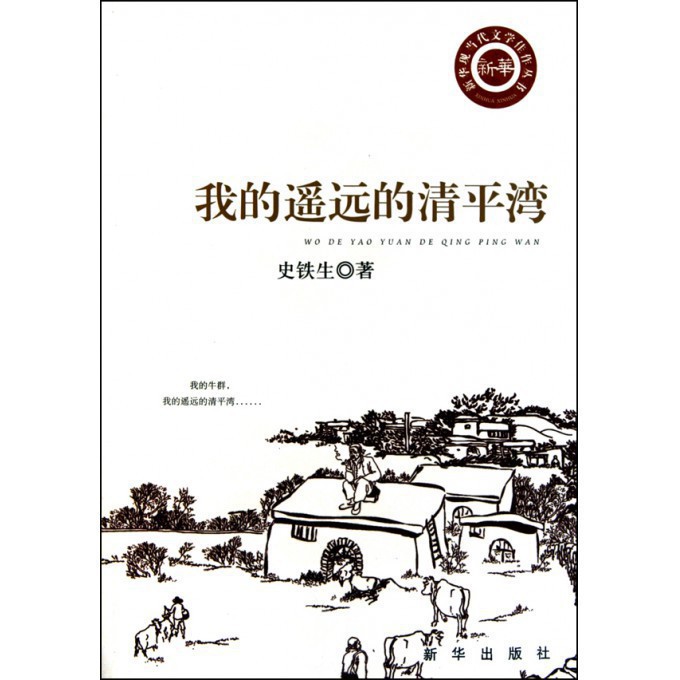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72年因双腿瘫痪停止在延安地区插队,回到北京;1998年又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 1979年后,他相继发表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等佳作;后又有《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新近有《扶轮问路》和《妄想电影》两部文集问世。 其作品曾多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1998年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奖;2002年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合散文奖”一等奖,随笔集《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作品奖。此外,他还获得过1994年庄重文文学奖。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川牛和南阳牛* 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漂亮,犄角 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 。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 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 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 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 。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 ,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 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 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 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 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 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 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 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 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 。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 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 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 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 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 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 ,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 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 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 永远是“*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 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 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 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 谷子都熟了,*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 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 ,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 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 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 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 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 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 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 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 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 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 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 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 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 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 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 。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 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 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 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 *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 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 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 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 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 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 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 文早已经定了。*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 ——”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 “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 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 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 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 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 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 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 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P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