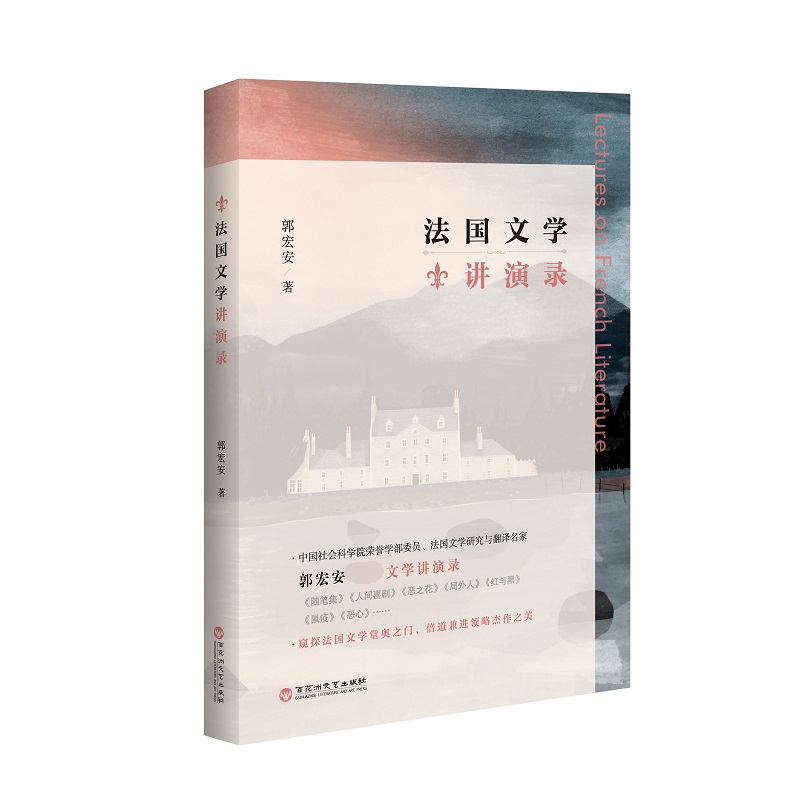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1.60
折扣购买: 法国文学讲演录
ISBN: 9787550042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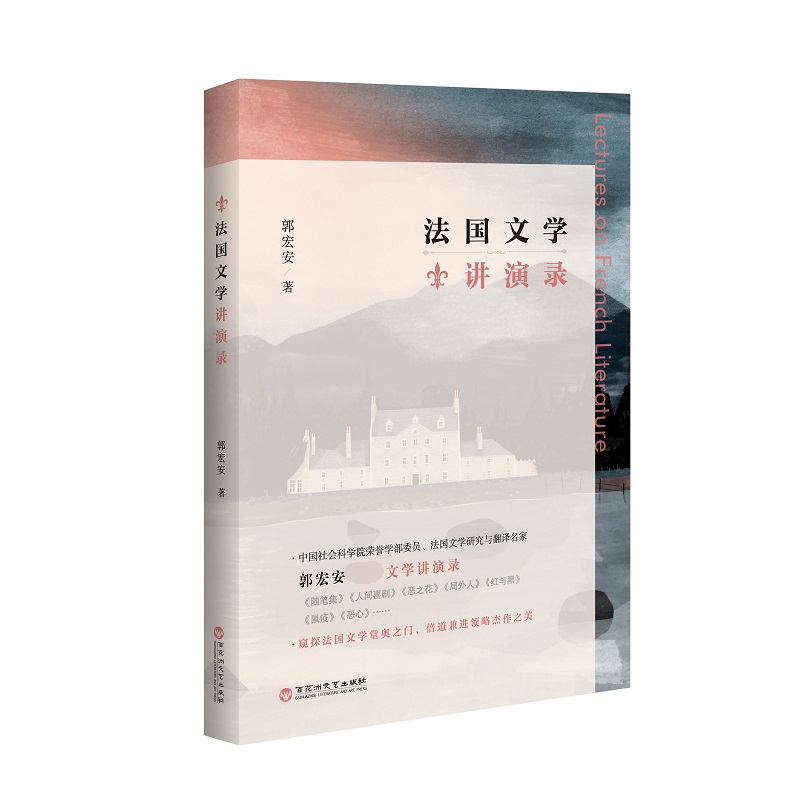
郭宏安、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专著及文学评论集《重建阅读空间》《从蒙田到加缪》《论〈恶之花〉》《从阅读到批评》《论波德莱尔》《阳光与阴影的交织》《第十位缪斯》等,文学随笔集《同剖诗心》《雪泥鸿爪》《完整的碎片》《斑驳的碎片》《塞纳河·莱蒙湖》等,译有《红与黑》《墓中回忆录》《大西岛》《波德莱尔作品集》《加缪文集》《批评意识》《反现代派》等,遵循“不苟作”的原则,研究、翻译和写作三驾马车永远在路上。
\"略说文学随笔 我今天准备谈一谈文学随笔的问题,我所谓文学随笔,指的是关于文学问题的随笔。在进入我的论题之前,我必须声明两点。首先,我之所以认为应该讲一讲有关文学随笔的问题,不是我认为我有这种资格,仿佛我已经是一个文学随笔大家,可以聚众收徒了,而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问题,我可以抛砖引玉,使讨论得以进一步深入。当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投入实践,因为理论问题早已解决了,我不过是在这里这时重新提出来罢了。其次,我在讲的过程中难免要举些例子,而这些例子又都是我的文章,这并不意味着我写得好,只不过因为是自己写的,查找、使用起来方便,有些真实和真切的体会。我并没有作一篇《论文学随笔》的文章的打算,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一些好的文学随笔读过了,却也找不到了,因此没有别人的随笔做例子,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别人的随笔。 两点声明做过了,我可以进入论题了。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文学随笔?二、什么是好的文学随笔?三、如何写好文学随笔? 一、什么是文学随笔? 什么是文学随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看看什么是随笔,文学随笔不过是随笔之一种罢了。假如我们拿到一篇文章,根据直觉,我们就可判断这是一篇论文或散文。假使我们认定这是一篇散文,我们根据其以说理为主还是以抒情为主,还可判断其为随笔还是小品。倘若我们判定一篇文章为随笔,我们一眼即可认出它是科学随笔、历史随笔、哲学随笔、社会随笔或文学随笔。当然更为有效的是,我们进行反面的判断,即判定某篇文章不是散文、随笔或小品。为了给我们的谈论一种公认的基础,我们不妨查一查《辞海》。《辞海》上说,随笔是“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故名。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十分流行,吸收了包括英国随笔在内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形式多样、短小活泼。优秀的随笔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语言洗练、意味隽永为特色”。这个定义看来颇适合中国宋代以来的“杂记见闻”之类,因为宋代洪迈写过一本《容斋随笔》,他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随笔”一词,大概是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里。前人评价此书“考证精审,议论高简”,可见作者说“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不过是一种谦辞罢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前人所谓“随笔”,是和“读书”有联系的,“读书”然后才“意之所之”,才“随即纪录”。这个定义还有“借事抒情”一节,与“五四”以来最为流行者相较,有些距离;与当今最为流行者相较,距离就更远了。因为今日所谓“随笔”,以说理为主,抒情尚在其次。当然,所谓“随笔”,并不排斥抒情,但是情在理中与直接抒情究竟不一样。除非我们把随笔归入小品文,否则我们是不能说随笔“借事抒情”的,倒是可以说,随笔是借事说理。“借事”很重要,没有“借事”,不成其为随笔。所借之事,往往从读书中得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品”“随笔”往往并称,似乎没有区别。所以有人说,“随笔中论理之成分是非常少的”,这与现代随笔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随笔与小品的区别,已有前人说起过,在此不必细谈。因此,《辞海》上的定义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定义。 《辞海》上说“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也用此名”这四个字,说得很含混,言下之意是,仿佛宋代以后的随笔不同于“五四”以来的随笔似的。其实,两种随笔都不脱“随手纪录”的实质。不过,自“五四”以来,三言两语式的“随即纪录”少了,有一定篇幅的多了,说理的或寓情于理的多了。这多与外国理论的输入有关。朱自清先生说:“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他所说的“散文”,包括随笔。不过,这种外国的理论一旦输入,就多少有些偏差。例如,周作人1921年发表一篇题作《美文》的文章,谈的是外国文学中的“论文”,尤其谈的是其中的一种,即“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周作人说的“论文”显然是法文中的“essai”,或英文中的“essay”,所谓“美文”是论文中之较短者。他没有说,所谓“美文”,也是以说理为主,我认为偏差由此而来。接着又有人谈“絮语散文”,英文所谓“familiar essay”,直接把法国的蒙田当作“絮语散文”的开山祖。接着又有人谈小品文,于是“絮语散文”和小品文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东西。对中国散文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人厨川白村论英国essay的一段话:“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于是,轻灵飘逸,幽默诙谐,一粒沙子上谈世界,半片花瓣上说人情,就成了人人追求的境界,就成了随笔的主流。偏差越来越大了,终于闹到把随笔中说理的成分赶尽杀绝的程度。国家的大事,家庭的琐事,个人的私事,统统在“废话”和“闲话”中化作“冷嘲”或“警句”,纵使有“滑稽”和“感愤”,也总是“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这就是说,随笔的要义,在于闲适。厨川白村是反对将“essay”译作随笔的,他的反对有些道理,因为法文中的“essai”来自动词“essayer”,有尝试的意思。但是,相沿成习,我们只好接受这种译法。补救的办法,就是发掘出“essay”的原有的含义,赋予随笔一种全新的意义。这样随笔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也不至于和小品文混为一谈了,因为随笔完全可以写上十万字,蒙田的随笔就有长达十二万字的。 所谓随笔的“原有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它不总是“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这“头痛”,不知是说的写的人,还是读的人,总之是和“暖炉”“安乐椅”“浴衣”“苦茗”之类不相称的东西吧。英国人的随笔,我读得不多,已觉得不尽是“即兴之笔”。培根的简洁紧凑中往往藏着“诛心之论”,这是王佐良先生的话。要让人看出这种“诛心之论”,写的人要用心,读的人也要用心,用心则难免头痛。所以,让人头痛,并不是英国随笔的缺点。法国随笔,我读得稍多,敢肯定少有“即兴之笔”。蒙田的率意铺陈中常常伴有伤时之语,写的人要有意,读的人也要有意,有意则必然头痛。因此,让人头痛,更不是法国随笔的缺点。这两家的文字嘛,都是看上去“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实则举重若轻,功夫下在“店铺后间”(蒙田谓人人皆须为自己辟一“店铺后间”)。“店铺后间”是腹笥极厚的意思,非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有得于心不办。随笔给人带来思想的快乐,思想着的头焉能不痛?思想的快乐中有头痛存焉。谓予不信,看看罗丹的《思想者》就知道了。 “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随笔当然是有的。洪迈的“老去习懒”之作大概是的,本·琼森说的“不过是随笔家罢了,几句支离破碎的词句而已”大概是的,戈蒂耶说的“肤浅之作”大概也是的。随笔,essai,essay,在中国,在域外,都曾被小看过,都曾带过贬义,蒙田也曾自嘲“只掐掉花朵”(言下之意是不及其根也)。肤浅,率意,“不至于头痛”,的确是随笔的胎记,不过也仅仅是胎记而已,倘若一叶障目,看不到随笔的全貌,势必将我们引入歧途。我所说的“外国的理论一旦输入,就多少有些偏差”,其意在此。写滑了手,率尔操觚,或者忸怩作态,或者假装闲适,或者冒充博雅,或者以堕落为潇洒,或者以媚俗为直面,或者以不平常心说平常心,或者热衷于小悲欢小摆设,或者以放在篮子里的就是菜,甚至以吸一口香烟或玩一圈麻将的轻松为标榜,那就是以为随笔尽是“废话”和“闲话”,那就或深或浅地染上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随笔习气”。 让·斯塔罗宾斯基是1984年欧洲随笔奖的得主,对随笔有独到的见解。斯塔罗宾斯基所谓“随笔”,指的是蒙田所创造的“essai”,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得已而译为随笔。根据斯塔罗宾斯基的考证和阐发,“essai”一词的含义有称量、考察、验证、要求、试验、尝试等等,甚至还可指蜂群、鸟群之类。总之,“essai即指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又指展翅飞起的一群语词”。蒙田在他的徽章上铸有一架天平,同时还镌有那句著名的格言:“我知道什么?”斯塔罗宾斯基认为,这种“独特的直觉”表明,“essai的行为本身乃是对于天平的状态的检验”。因此,蒙田的随笔实在是一种追寻和探索,一种对自我和他人(世界)的追寻和探索,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和保持平衡。经过培根、洛克、伏尔泰、柏格森等人的运用,随笔表明了一种著作,“其中谈论的是新的思想,对所论问题的独特的阐释”。这种著作提请“读者注意,并且在他面前展示角度的变换,至少向他陈述使一种新思想得以产生的基本原则”。随笔既是内向的,注重内心活动的真实的体验;又是外向的,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感知;更是综合的,始终保持内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塔罗宾斯基说:“写作,对于蒙田来说,就是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在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中,击中读者的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强烈地感知。有时也是突然地抓住他,让他恼怒,激励他进行反驳。”蒙田深知,“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有一半是听者的”。因此,蒙田的随笔展示了人和世界的三种关系——“被动的依附,独立和再度掌握的意志,认可的相互依存及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使随笔成为一种“最自由的文学体裁”。这种文学体裁有其“宪章”,那就是蒙田的一句话:“我探询,我无知。”探询而后无知,而不是无知而后探询,这是蒙田的思想的精义。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这种制度企图到处都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现代人文科学的广泛而巨大的存在“不应该减弱它的活力,束缚它对精神秩序和协调的兴趣”,而应该使它呈现出“更加自由、更加综合的努力”。总而言之,“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应该同时是对他者语言的理解和它自己的语言的创造,是对传达的意义的倾听和存在于现实深处的意外联系的建立,随笔阅读世界,也让世界阅读,要求同时进行阐释和大胆的创造。它越是认识到话语的影响力,就越有影响……随笔应该不断地注意作品和事件对我们的问题所给予的准确回答。它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背弃对语言的明晰和美的忠诚。最后,此其时矣,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毋庸赘言,这是对现代随笔的一种全面、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全面、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可见文学随笔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文学随笔正是这样的随笔的一种,它以文学的问题为对象,以精神的自由为阐释的动力,要求语言的明晰和对美的忠诚。\" 《法国文学讲演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名家郭宏安先生的首部文学讲演录。全书共收录10篇讲稿,作者对法国文学的文化蕴涵作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对法国文学的思潮流变作了颇具现实性的论述,并对法国作家的经典意义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书在通俗性的讲演中渗透着严谨而又深刻的分析,以生动的讲述方式把广大读者带入法国文学繁茂的历史情境之中。总体来说,是一部学术性、通俗性与可读性完美融合的讲演性文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