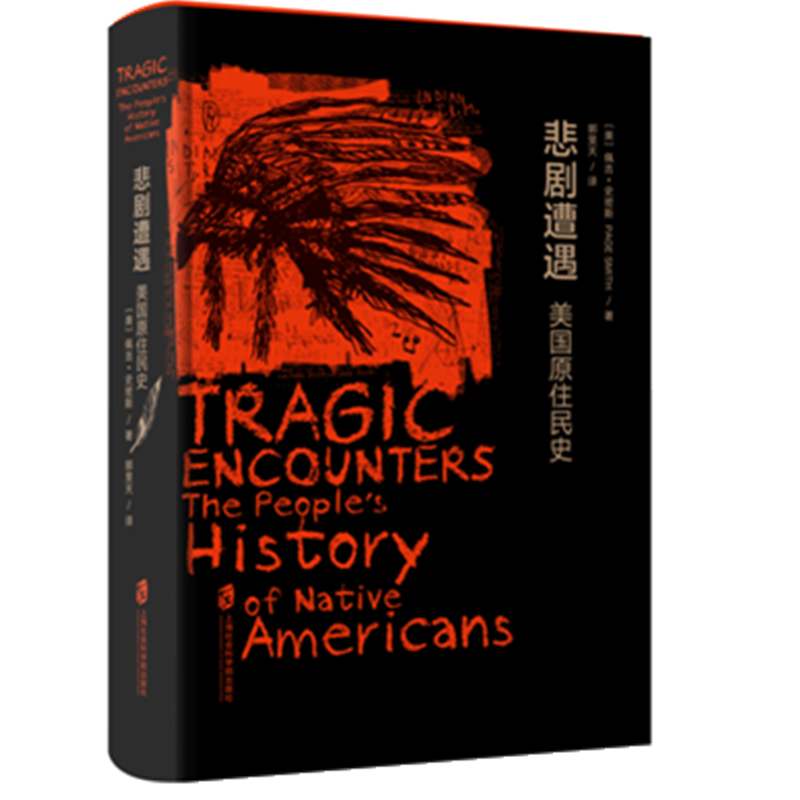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135.00
折扣价: 75.20
折扣购买: 悲剧遭遇(美国原住民史)(精)
ISBN: 978755202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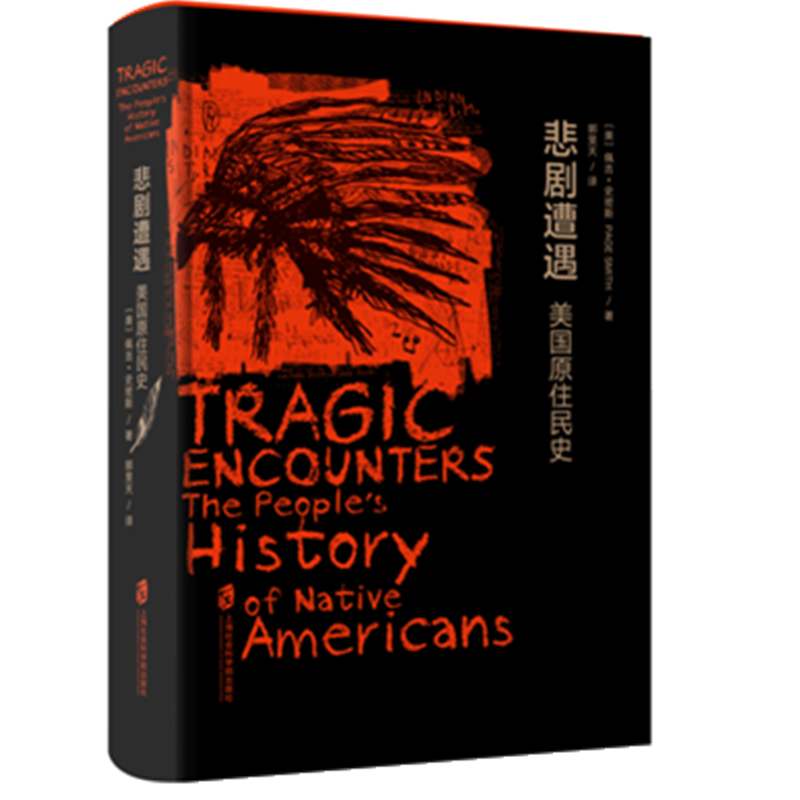
佩吉·史密斯(Page Smith),美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曾在哈佛大学师从海军史专家萨缪尔·莫里森教授,后于加州大学任教。著有《美国人的历史》(八卷本),另一部作品《约翰·亚当斯总统》获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 郭旻天,200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目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职。喜欢翻译工作,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有多部翻译作品在国内出版,代表作有《美国城市社会的演变》等。
早年遭遇 在世界历史上算得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场不同文明的遭遇,莫过于英格兰殖民者和美国原住民之间的狭路相逢。英格兰人因后者皮肤黝黑,而概称其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可被划分为不可胜数的部落,各部族的不同口音和方言达五百余种(美国原住民的这一情况也常被殖民者作为依据,推断原住民可能是以色列消失的部落。因为他们曾属于一个民族,但是因为他们狂傲自负想要造通天高塔被上帝诅咒,受到责罚分裂成不同部落,以及说不同的语言)。许多部落和别的部落之间战事频仍。那些从旧大陆来的人看到印第安人的文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认为文明处于持久不息的战争状态。战斗中的勇猛斗志以及对于严刑拷打的超凡忍耐力是生活在部落中的人的最高境界。几乎在任何方面,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总会表现出文化样式上的截然不同。在北美大陆的东部,大多数原住民都是能征善战的猎手,这些人特别骁勇,体力极其充沛。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逡巡,并没有地产权的概念,也没有正义的概念。残忍、暴力和无休止的战争是日常生活的本真。而且欧洲的思想家也前所罕见地着迷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引领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伏尔泰和卢梭,都认为人类社会腐朽而堕落,已经背离了自然人的质朴和简约。他们把野蛮人浪漫化,因为在他们看来野蛮人更贴近自然,他们的智慧也不会因为教士般的迷信,或是因为社会习俗、时尚、贪心或者野心弄得云山雾罩。伏尔泰曾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老实人》,是关于一个印第安人来到法国,在各个地方的各种遭遇以及如何看穿法国人生活的肤浅和虚假:无论是宗教、哲学、政府还是上流社会,都被揭露是空洞无物而且俗不可耐的。 以上是18世纪出现的一些现象。可是在前一个世纪的种植园主以及新大陆的定居者,他们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印第安人要么是等待被上帝无上荣光所拯救的可怜异教徒,要么是一个骇人的异域怪客和一种致命的威胁。大多数来到新大陆的英格兰探险家和种植园主都是满怀虔诚想要给美洲的野蛮人带来欧洲基督宗教的福祉。然而这项工作实际上却是出乎寻常的艰难。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约翰·史密斯上尉常年忙于和狡猾的波瓦坦人作战,而弗吉尼亚公司的头脑们常常奉劝他在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方面也多多建树。面对这种训诫,史密斯很生硬地回复说,他需要更多士兵,这样才能迫使印第安人听传教布道时更专心一点。如果一个印第安人正在向你射箭,或者就是想着要剥你的头皮,那就很难让其皈依基督。如果说定居者的基督教信仰并不能促使他们和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住民部落和平相处,简单的警惕心理却会让他们就范。面对敌众我寡,又缺乏训练,除了偶尔一两回,在战争理念上,他们竭尽所能地避免冲突,当然,他们也确实不熟悉印第安游击战士的鬼影遁形和兵不厌诈的战法。但是,维持和平这一问题,却因为原住民部落间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变得复杂,对于定居者来说,要避免这样冲突,真是难比登天。除此之外,法国和英格兰之间为了北美大陆的控制权已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冷战——在弥漫了一百多年的硝烟味之后终于听到了爆炸声,在1754年开始了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或称7年战争——不管是印第安人还是定居者,这一格局皆大为削弱了他们的士气。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格兰人都按捺不住地要把印第安人拿来当作他们争夺北美大陆控制权的棋子。法国人一再地鼓动他们的印第安友军去劫掠英格兰人的定居点,而英格兰人这边也同样玩着没有节操底线的游戏。 弗吉尼亚,是种植园主和印第安人初次遭遇的地方,也是约翰·史密斯上尉和印第安酋长波瓦坦(Powatan)以及他的女儿波卡洪塔斯(Pocanhontas,又译: 宝嘉康蒂)流传经久的奇遇故事的发生地。对于以下这个故事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波卡洪塔斯那个脾气不好又狡诈的老父亲波瓦坦准备要把史密斯打得脑浆迸裂之际,是她救了史密斯的命。当然,我们也只有史密斯上尉的一面之词,一些历史学家称其为臭名昭著的骗子(不过另外一些人,也用同样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以翔实的证据为其作了辩护)。至少比较清楚的一点是,在这位头发半白,一面像求偶对象一面像父亲一样的史密斯上尉和那位印第安公主之间的确有亲密和真挚的关系。而且她一定是位迷人的姑娘,也曾在印第安少女的狂欢队伍中,赤裸着横穿过詹姆斯顿的广场。印第安人在外交上的问题之所以变得引人注目,也是因为自史密斯上尉离开殖民地之后,波瓦坦就开始骚扰定居者了。而定居者的应对办法就是把波卡洪塔斯抓来作人质,迫使波瓦坦弃恶从善。就在波卡洪塔斯被羁押在詹姆斯顿的时候,一个叫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的人,或许是因为先前在广场上看过她做侧手翻,爱上了女孩,并且作了大量的思想斗争要不要娶她。他希望自己确信的确“谨受上帝意志之召唤”。并且他申明,按他的原话说,他(与波卡洪塔斯结婚)并不是受了“不受控制的肉欲情感”的引领,“而是为了种植园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我自己的救赎,以及为了使一个不信者皈依上帝和耶稣基督的真理”而这么做的。于是,这样的结合也就如他期许的那样变得顺理成章、不容反驳。罗尔夫于是就娶了波卡洪塔斯,并带着他的已经改名为瑞贝卡·罗尔夫并穿着英式优雅服装的印第安公主,回到了英格兰,然后被引见给英国女王,并被当作上帝造物的奇迹一般瞻仰。 瑞贝卡·罗尔夫在回弗吉尼亚的航行中过世了。她留下了一名男婴,按照一种浪漫的说法,许多今天的弗吉尼亚居民都是这个男婴的后代。上面这个故事是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既充满浪漫色彩又富有悲剧性的一个缩影:起初在罗尔夫和波卡洪塔斯结婚时看上去是如何的前景美好,但是在几番时而色彩绚烂时而血腥的波折之后,最终走向一个阴郁的结局。 在1622年,也就是波卡洪塔斯去世数年之后,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突然开始将矛头指向白人,并且几乎血洗了整个殖民地。那些幸存者只是因为一个印第安妇女的警报而幸免于难。而这一事实不免引出了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之中,最令人震惊的方面之一: 一群又一群的定居者,一次又一次因为印第安妇女的警报而躲过了印第安人的突然袭击和灭绝屠杀。这些妇女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定居者即将接踵而来的袭击。 约翰·劳森是一名绅士、一位测绘员,他与北卡罗来纳的印第安人很熟,他也特别喜欢印第安妇女,在他看来,印第安妇女(整体而言)简直堪比宇宙间任何美好之物。她们有黄褐色的肌肤,明眸忽闪而多情;她们笑靥动人,因而拥有世上无双的面容;她们都有一双玉手,纤小修长;她们面颊圆润,胴体浑若天成。她们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缺乏教养或者不可相容,她们也并非……缺乏柔情。 “贸易女郎”(Trading Girls)是一些没结婚的年轻印第安妇女,只要她们的家人和酋长同意,而且酋长能拿到一部分回扣(通常是一瓶白兰地),她们就能跟贸易商人睡觉然后拿到一笔钱。这些妇女并不会因此背上污名,通常干这个勾当一段时间之后就嫁给一个印第安战士,从此当上贤妻良母。那些和印第安人做生意的白人,“通常有一个印第安妻子”,劳森写道,“因此他们很快学会了印第安人的语言,与这些野蛮人建立了友谊。这些白人发现他们的枕边伴侣,印第安女孩们,除了能给他们带来床笫之欢,还非常好用,不仅可以照料他们的饮食,而且还能教他们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些关系所产生的一个不幸结果,至少在劳森看来,以这种媾和方式生出来的孩子,长大了还得是印第安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发现英格兰人和其他欧洲人已经习惯了和这些野蛮人妇女的‘交际’以及她们的生活方式,深深着迷于这种大大咧咧的生活。为了能一直待在他们的印第安妻子和她们亲友身边,只要他们还活着,就不怎么愿意回到英格兰人中间生活……”除此之外,劳森还观察到“印第安男子在恋爱中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精力旺盛又急不可耐”。印第安少女非常独立,而且“那些和欧洲男子‘交往’过的妇女,日后很少会把和本乡本土的男子的‘交流’放在心上”。 劳森所用的“交流”(conversation)和“交往”(conversing)这两个词指的是同居,包括两性关系。证明印第安妇女和白人男性之间存在着美妙的关系,也是通过许多很细碎的小小旁证而推出的。很显然,印第安生活最吸引白人男性的一面就是印第安妇女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部分是因为印第安妇女很容易接近,而且这种关系十分简单并且是自然而然的。不仅如此,印第安妇女很有主见又很独立,但又温柔可爱,并且对她们的白人“丈夫”非常忠诚。在印第安妇女看来,白人男性就意味着权力。 深沉难测和异域风情,这些东西无论是什么种族、什么年龄的妇女看来都是男性魅力的体现。在定居者和印第安的关系中,最让人辛酸扼腕的也就是白人男性和印第安妇女之间这种昭然若揭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通常也能拯救一个在双方前线的定居点使之免遭灭顶之灾。 可惜,极少有殖民者能有像罗尔夫先生那样的作为。威廉·伯德在其《分界勘定记》(The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一书中对此事颇感痛惜,“毕竟啊……”,他用着看似睿智,但毋宁说是滑稽的口吻写道,“……如今派到这些印第安异教徒,还有别的异教徒当中的传教士,最占风头的是这些活泼好动的情圣……况且,而今就算皮肤有颜色也不会受人指摘。话说,摩尔人要把肤色洗掉成为白人只要过三代,那么一个印第安人要把肤色漂白也只需要两代人。”伯德认为印第安妇女“就和他们早前从海外来的船只上买来的年轻女人一样,都能成为第一代种植园主的贤惠妻子……因此,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此慷慨地与一个印第安妇女共享一片印第安土地的所有权,并如此高尚地拯救了她的灵魂,那么拒绝拥有这样一位健康、坦诚的枕边人岂不怪哉”? 就算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结婚的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依然十分欢迎印第安人的来访。在17世纪90年代,威廉·杜兰德参加了一个在弗吉尼亚的婚礼,有很多印第安人也在场。杜兰德笔下的那些妇女穿着“某种衬裙,也有些人披着粗鄙蓝布衣服,而这种蓝布做成的毯子是他们在某些船上做生意来换鹿皮的。她们在蓝布片的中间挖个洞,把头穿过去,然后将布片包好身子,用鹿皮带束紧。她们自如地加入宾客之中,为典礼平添了一串‘多彩’的音符”。 印第安部落的一些成员如果与一个殖民地交好,那么他们很自然就会去拜访那里的居民,或者成为殖民地的座上宾。以宾夕法尼亚为例,他们的议会有几间公寓,就是为了印第安酋长拜访而准备的。在弗吉尼亚,招待过往此地的印第安人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了这一风气盛行的最后时光。据托马斯·杰斐逊回忆,印第安人经常来访威廉斯堡,并且来访者为数不少。这位弗吉尼亚人抽出许多时间来陪伴这些客人,他们也曾是伟大的切诺基勇士和辩论家欧塔希提(Outacity)的朋友。欧塔希提来往于殖民地首府的旅行中,经常和杰斐逊的父亲为伴。约翰·亚当斯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记得从小时候彭格博(Pungapog)和内蓬塞(Neponset)部落的祭司和首领——他分别称之为亚伦和摩西——就频繁来访。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这么魁梧的印第安人。”接着,亚当斯在他的长篇大论之后总会提到他家附近一户印第安人的棚屋:“在那里我总是能被招待吃越橘、黑莓、草莓,或者苹果、梅子、桃子,等等。因为他们在家周围种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水果。” 很不幸,要是和一个印第安部落成为朋友,那就得成为他们敌人的死敌。印第安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在这方面没有妥协的余地。如果你成为某个印第安部落的朋友,那你就是他们对抗敌人的盟友。只要背离了这一条,就是最可耻的背叛。弱小的或者附庸的部落总是希望和定居者建立盟友关系,希望能借此打败他们所附庸的部落。在加拿大地区的法国人,因为和休伦人(Huron)结盟,而和北美大陆东北部最强大也最好战的易洛魁(Iroquis)人成了敌人。之后,当欧洲列强将他们的战火延烧到美洲大陆的时候,这群休伦人的天敌则成了英格兰人的盟友。在康涅狄格,定居者受邀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造家园,这显然是那个部落希望可以增强实力一同打败敌人。康涅狄格的定居者在约翰·梅森和约翰·恩德希尔的领导下消灭佩克特人(Pequot)的行动,得到了该地最强大的部落,纳兰甘希特人(Narragansetts)和莫西干人的配合。定居者成功地和他们保持着整体上的和平友好关系。 在马萨诸塞湾的殖民地建立起来的时候,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把《圣经》翻译成印第安语言。但艾略特只是许多辛勤工作以改变印第安人的命运并使他们皈依基督宗教的传教士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特别建了一幢教授印第安学生的大楼。克莱布·切司哈陶穆克(Caleb Cheeshateaumuck)是第一个在此获得学士学位的印第安人。当威廉玛丽学院于1693年在威廉斯堡建立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印第安学院,当然,达特茅斯大学里也有。达特茅斯的印第安学院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印第安牧师和学者,沙逊·奥康(Samson Occom)。 这是一本介绍美国原住民历史的专题式著作,作者从欧洲入侵者进入美洲大陆开始,一直写到1890年美国印第安战争结束。全面介绍了印第安人在美国建立、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痛苦以及为此进行的抗争。作者佩吉·史密斯通过欧洲的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故事,记叙了印第安文化如何在此过程中与欧洲殖民者文化相互融合,最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众多冒险传奇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