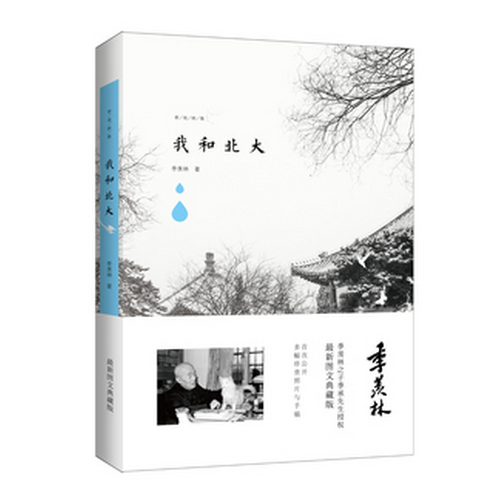
出版社: 青岛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1.79
折扣购买: 我和北大/季羡林集
ISBN: 9787555217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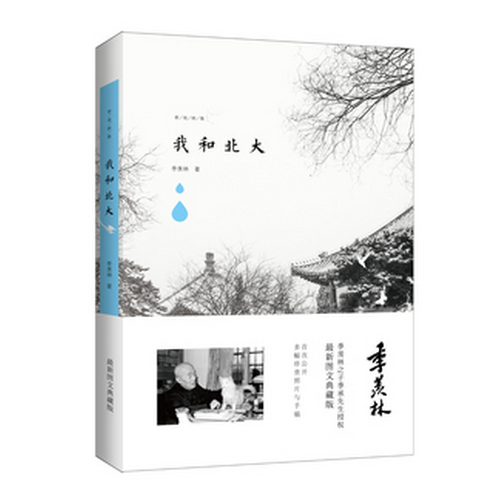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人。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其问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寸草心 小引 我已至望九之年,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亲属先我 而去的,人数颇多。俗话说:“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记 忆里。”先走的亲属当然就活在我的记忆里。越是年 老,想到他们的次数越多。想得最厉害的偏偏是几位 妇女。因为我是一个激烈的女权卫护者吗?不是的。 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说不清。反正事实就是这样 ,我只能说是因缘和合了。 我在下面依次讲四位妇女。前三位属于“寸草心 ”的范畴,最后一位算是借了光。 大奶奶 我的上一辈,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老大、老 二,我叫他们“大大爷”、“二大爷”,是同父同母 所生。父亲是个举人,做过一任教谕,官阶未必人流 ,却是我们庄最高的功名,最大的官,因此家中颇为 富有。兄弟俩分家,每人还各得地五六十亩。后来被 划为富农。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 我从未见过,他们父母生身情况不清楚,因家贫遭灾 ,闯了关东,黄鹤一去不复归矣。老七、老九、老十 一,是同父同母所生,老七是我父亲。从小父母双亡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母。贫无立锥之地,十一 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九叔也万般无奈被迫背井离 乡,流落济南,好歹算是在那里立定了脚跟。我六岁 离家,投奔的就是九叔。 所谓“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妻子。大大爷生过 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大奶奶有过一个孙子。可惜在 娶妻生子后就夭亡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因此,在 我上一辈十一人中,男孩子只有我这一个独根独苗。 在旧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环境中,我成了 家中的宝贝,自是意中事。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在我六岁离家之前,我就成了大奶奶的心头肉,一天 不见也不行。 我们家住在村外,大奶奶住在村内。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滚下土炕,一溜烟就跑到 村内,一头扑到大奶奶怀里。只见她把手缩进非常宽 大的袖筒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半块或一整个白面 馒头,递给我。当时吃白面馒头叫做吃“白的”,全 村能每天吃“白的”的人,屈指可数,大奶奶是其中 一个,季家全家是唯一的一个。对我这个连“黄的” (指小米面和玉米面)都吃不到,只能凑合着吃“红的 ”(红高粱面)的小孩子,“白的”简直就像是龙肝凤 髓,是我一天望眼欲穿地最希望享受到的。 按年龄推算起来,从能跑路到离开家,大约是从 三岁到六岁,是我每天必见大奶奶的时期,也是我一 生最难忘怀的一段生活。我的记忆中往往闪出一株大 柳树的影子。大奶奶弥勒佛似的端坐在一把奇大的椅 子上。她身躯胖大,据说食量很大。有一次,家人给 她炖了一锅肉。她问家里的人:“肉炖好了没有?给 我盛一碗拿两个馒头来,我尝尝!”食量可见一斑。 可惜我现在怎么样也挖不出吃肉的回忆。我不会没吃 过的。大概我的最高愿望也不过是吃点“白的”,超 过这个标准,对我就如云天渺茫,连回忆都没有了。 可是我终于离开了大奶奶,以古稀或耄耋的高龄 ,失掉我这块心头肉,大奶奶内心的悲伤,完全可以 想象。“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我只有六岁, 稍有点不安,转眼就忘了。等我第一次从济南回家的 时候,是送大奶奶入土的。从此我就永远失掉了大奶 奶。 大奶奶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母亲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 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 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 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 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 ,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 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 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 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 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 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 我只想写一件我绝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 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 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人土。我回到家里,看 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 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 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 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 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 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 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 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 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 “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 :“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 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 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 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号啕大哭 。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 ,连柳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 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 !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 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 。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 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 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 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 ,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 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 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 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婶母 这里指的是我九叔续弦的夫人。第一位夫人,虽 然是把我抚养大的,我应当感谢她,但是,留给我的 却不都是愉快的回忆。我写不出什么文章。 这一位续弦的婶母,是在1935年夏天我离开济南 以后才同叔父结婚的,我并没见过她。到了德国写家 信,虽然“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婶母”这个称呼 ,却对我来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直到1947年,也 就是说十二年以后,我从北平乘飞机回济南,才把概 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婶母(后来我们家里称她为“老祖”)是绝顶聪明 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我初回到家,她 是斜着眼睛看我的。这也难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 凭空冒出来了一个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 ?好不好对付?”她似乎有这样多问号。这是人之常情 ,不能怪她。 我却对她非常尊敬。她不是个一般的人。在我离 家十二年,我在欧洲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国 内经历了日军占领和抗日战争。我是亲老、家贫、子 幼,可是鞭长莫及。有五六年,音讯不通。上有老, 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 奉。有时候,经济没有来源,全靠她一个人支撑。她 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 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 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 给人看病。她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 老夫”。她的苦心至今还催我下泪。在这万分艰苦的 情况下,她没让孙女和孙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 总之,一句话,如果没有老祖,我们的家早就完了。 我回到家里来也恐怕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 叔父归天。 …… P2-5
首次公开多幅珍贵照片与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