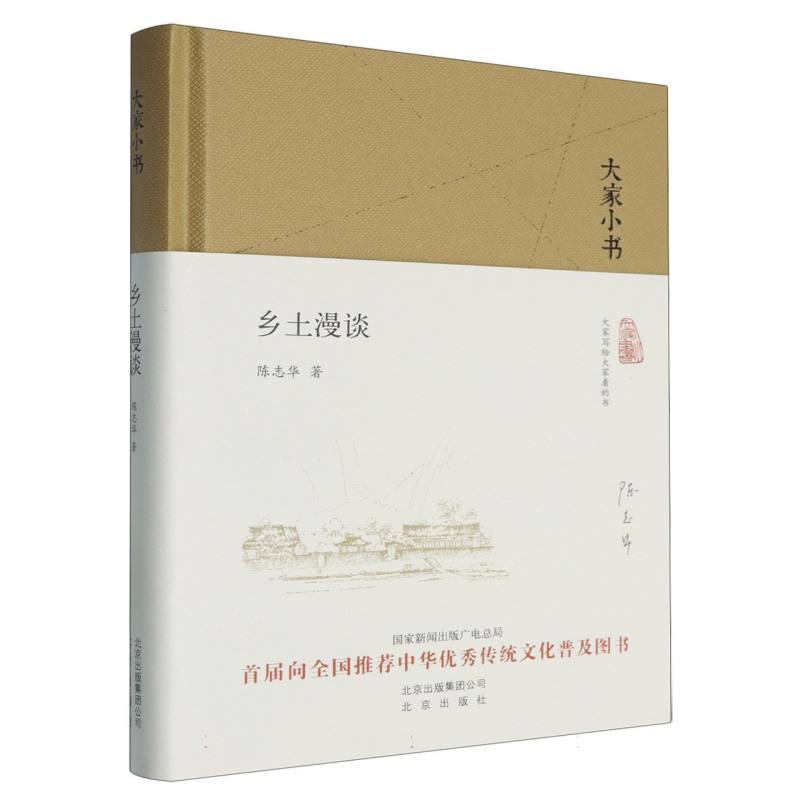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80
折扣购买: 乡土漫谈(精)/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39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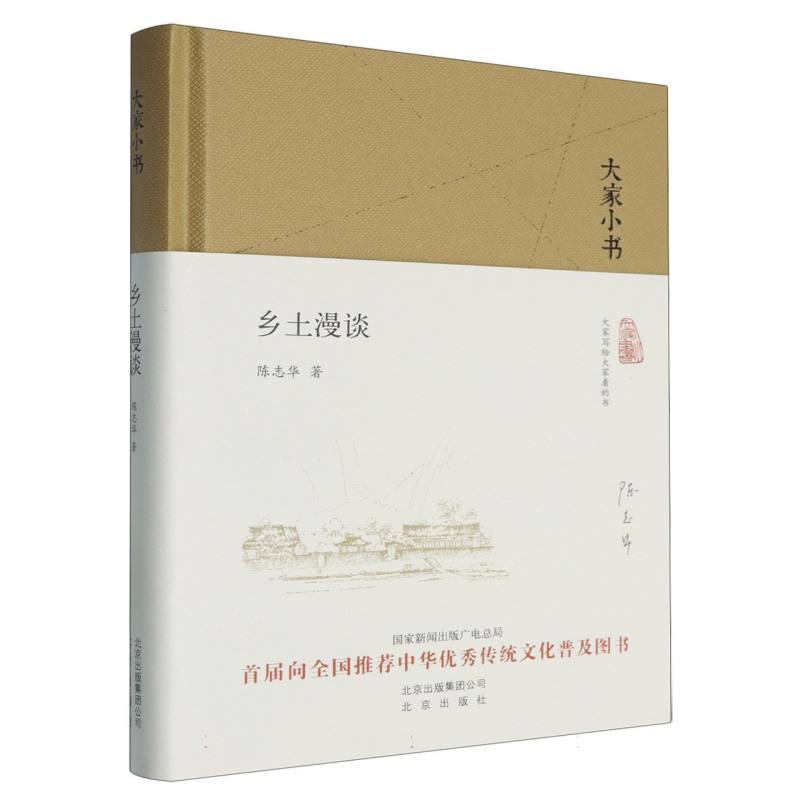
陈志华(1929— ),浙江省宁波人,祖籍河北省东光县。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转营建系。1952年毕业于建筑系,当年留母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主要专著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北窗杂记》《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外国古建筑二十讲》等,还编译了《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现代西方建筑美学文选》等书。1989年起从事中国乡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与楼庆西、李秋香共同成立“乡土建筑研究组”,出版《中华遗产.乡土建筑》系列丛书和《中国乡土建筑初探》等著作。
代序 年过八十,终于老了,这才体验到什么叫记忆力衰退,原来它不是“渐行渐远”,而是跟拉电灯开关一样,吧嗒一声,一件事便再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它也会有几次反复,说不定哪天就会有陈谷子、烂芝麻忽然闪进脑子,但是,那些似真似幻的故事要求证便难了。于是,有一些年富力强的朋友就逼迫我写几段回忆录,不写,便不给饭吃。不给饭吃,即使对我这样的老糊涂来说,也是怪可怕的惩罚,我便运气调息,想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有三个时期倒是还有点儿事情可记。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上山下乡搞乡土建筑研究时期。正好是少年时期、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前两个时期虽然也很有些重要的情节,不过那是全民族性的事件,我的经历跟许多朋友的一比,简直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不妨先把它们撂下。第三个时期,倒是有点儿我个人的特色,虽然未必能吸引多少人的关心,但也会有人觉得有趣。 其实,这第三个时期和前两个时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日寇侵略者在南京杀死了我的三爷爷和小姑姑,也把我从滨海一个中等县城赶到了农村。整整八年,随学校上山下乡,在祠堂里住宿,在庙宇里上课,在老乡家里洗衣服,煮白薯吃。那些淳厚的农妇,以仁慈的心对待我们这些连衣服都洗不干净的孩子。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几块小小的白薯请她们煮,她们会端出一大盆煮白薯来,看着我们吃下肚去。我们发烫的脸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对她们说声谢谢。这岂是此生能忘记的! 第二个时期,在学校里遭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的冲击,见到了恶,也见到了善。好在闹了两年多,学校里就要“斗、批、改”了,把我们一批人弄到农场去“脱胎换骨”。农场可是美丽的,有无边的水稻和菜花,有高翔远飞的大雁和唱个不停的百灵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爽的环境,心想下半辈子务农也不赖。看来我身上流动着的还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父母的血。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祖国苏醒过来不久,80年代初,我就凭着被农场生活唤醒了的对乡土的爱,去找了我在社会学系读书时候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询问他那里有没有机会让我去做乡土建筑研究。看来费先生还有很重的顾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叫我不妨去问问翁独健先生。我以前不认识翁先生,但还是骑着自行车进城到他家去了一趟。他正在藏书室里翻书,我说了来意,他没有停手便摇摇头,我只得辞了出来。这件事正好证明我的愚蠢,那正是“心有余悸”还担心“七八年来一次”的时候,闹什么新鲜事儿。 于是,老老实实回学校,仍然干我的外国建筑史和外国园林史的研究。“隔山打牛”,挺滑稽的,何况只能从老书本上识牛。 好在“上天不负有心人”,一晃几年过去,来了机会。1989年浙江省龙游县的政府领导人居然想到把本县村子里一些高档宗祠和“大院”拆迁到城边上的鸡鸣山风景区去,弄成一个“民居苑”。为了干好这件事,邀请我们建筑系派人去帮他们把那些要拆迁的房子测绘一下。系领导同意了。我从50年代起便负责一门叫作“古建筑测绘”的实习课,当然在奉派之列,带着学生去了。那年代的学生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很快便完成了任务,于是向我和另一位女老师李秋香提出要求,带他们到附近村子里再参观一些古老民居。这建议跟我的兴趣合拍,便答应了他们。 第一个想到的主意是到建德去。大约五六年前,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认识了建德市的叶同宽老师。他天分高,可惜“成分”也“高”,上不了大学,便坚持自学,终于成材,那时在一个什么政府部门做建筑设计工作。龙游跟建德相近,可是,他在什么部门工作呢,一点也不知道。但我还是带着学生到了建德。从火车站进城,上个长坡,迎面就是园林局,我们敲门进去打听,真是老天有眼,正巧叶老师就在园林局的技术科里工作。 叶老师是一位心肠火热的人,我们把愿望一说,他立即答应接待,先安排好了住宿、伙食,又立马带我们游了一趟千岛湖和一趟富春江,也看了几个小村子。 随后,我们到了杭州,住在六和塔附近,因为我们在六和塔上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把该做的工作做完,一身轻松,就到浙江省建设厅,找到了当副厅长的一位老同学。谈了一会儿,他知道了我们对乡土建筑有兴趣,就说,他老家永嘉的楠溪江流域有一大批很美的农村建筑,正好,他过几天就要去出差,如果我们乐意去,他可以带上我们。我和李秋香立即决定,先把学生们带到东阳、义乌看看,送他们上了火车回学校,我们就跟这位老同学到楠溪江去。 送走了学生之后,还有三五天时间,我和李老师都不是喜爱城市繁华的人,杭州虽然风光旖旎,毕竟还是一身城市气,于是,立即决定回建德再住几天,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好的老村子。这一回去,收获可大了,叶同宽老师把我们带到他老家新叶村,对我们此后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来说,这竟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我们当时见到的新叶村,简直是一个毫发无损的农耕时代村落的标本,非常纯正。当然,说的是建筑群和它的环境,不涉及政治和经济。它居然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一座文峰塔,据说,整个浙江省几百上千个村落就只剩下这么一座塔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过去倒曾经有过上百座。村子里其他各类建筑如住宅、宗祠、书院等等的质量都很高,保护得也很好。村子的布局,它和农田、河渠以及四周山峦的关系也很协调,简直是一类村子的典型。 我和李秋香都很兴奋,一面走走看看,一面就商量起怎么下手研究这个课题来。 待回到杭州,第二天清早搭上副厅长的车,一整天不曾太耽误,破路上磨磨蹭蹭,赶到永嘉已经天黑了,店铺都早已关上了门。小吃店也都打了烊,敲开一家,求老板给个方便,每个人吃了一碗面条,然后找了一家宿店睡觉。 第二天清早就下乡,楠溪江两岸的村落一下子就把我们抓住了。借一句古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是我们以后二十多年来对楠溪江不变的赞誉。初看,那些房子虽然都很亲切,又很潇洒,但是,似乎又都很粗糙,原木蛮石的砌筑而已。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什么吸引了我?哎哟,原来那原木蛮石竟是那么精致、那么细巧、那么有智慧,它们都蒙在一层似乎漫不经心的粗野的外衣之下,于是就显得轻松、家常。看惯了奢华的院落式村舍,封闭而谨慎,再看这些楠溪江住宅,那种开放的自由、随意的风格,把我们的心也带动得活泼有生气了,仿佛立即就能跟房主人交上好朋友。这真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我们是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再乘火车回北京的。路上,我们兴奋地把一个研究计划讨论定型,只待动手干了。但是,经费呢?怎么办?总得有几个车票钱吧。“一钱难死英雄汉”,这是武侠小说里的老话,连秦叔宝那样的好汉都被逼得上市去卖黄骠马,我们能卖什么呢?只有一辆破自行车!总不能带着学生一起行军吧,好几千里路呐! 几年前建议费孝通先生和翁独健先生领导起来去做的工作,难道还依旧是空想?放下不做,那可是太可惜了,农村里拆旧建新的风已经刮起来了,我们当然不反对造新房子,但总得留下几处这么美的老村子呀。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出了个奇招:先做新叶村,问问叶同宽老师有没有可能向建德的什么单位筹点儿路费。我们精打细算,把人力压缩到最低,第一次去四个人,要四个人的来回车票。 就这样病急乱投医,有点儿滑稽。不料宽厚的叶老师回了信:可以!很快就把钱寄过来了。那时候他是一位极其平常的普通技术人员,甚至还不是正式进了编制的人员。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了,我们跟叶老师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次面了,我从来不问他,这笔钱是他从哪里筹来的。我隐隐觉得,这钱是他私人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公款里报销这笔路费。找人去“筹”?没有一丁点儿借口!是叶老师开动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乡土建筑研究工作!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去返还这笔费用。数一沓钞票递过去吗?那是亵渎,我宁愿一辈子背着这笔债,活着,就努力干! 我们的工作得到的第二笔经费,是系资料室管理员曹燕女士把卖废纸的钱给了我们,这钱本来是她们的“外快”福利!钱不多,但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心意!我们买了胶卷、指南针、草图纸之类的文具。 第二年,1990年大约3月底,李秋香带学生动身去新叶村之前,我陪她到海淀街上去买一只摄影用的测光表。那时候我们都不会摄影,尤其估不准正确的曝光量。用的是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老相机,根本没有自动装置。一路上,我们细细地讨论了研究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估计他们这第一次的主要任务便是测绘,正式的调查放在秋天动手,那时候我便没有课了,可以一起去。他们走了,我这个年长的老教师,心里嘀咕着:从杭州到建德去的公路还在修,要乘多少时间的公共汽车?不知道!村子里没有电话,我家里也没有电话,整整一个月,生死不知。唯一可以给我一点宽慰的是毕竟有叶老师在那里,我们都信任他。 大约4月底,或5月初,忽然,一天,李秋香带着学生们回来了。在走廊里,她老远看见我就挥手,高声喊:“完全可以成功!”赶紧让她们坐下,问:“成功了哪些,测绘还是调查?”答:“都做了。”问:“可以写成文吗?”答:“可以,暑假后完成!” 大约9月份吧!她交出了一整本稿子,五万多字。我连忙看,好家伙,居然只要把照片和测绘图配上差不多就可以成书了。当然,这种工作要做好,去一趟是不够的,有些情况还不够肯定,有些大范围的平面图还要补测。那么,问题又来了,眼看着可以有大成功的事,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再请叶老师想办法吧? 恰好,台湾允许大陆的人去探亲了。我想也许我可以到海峡对岸去弄点经费来。我去了,带去一本《外国造园艺术》的稿子,在台北的重庆南路找到一家出版商,山东人,卖给了他,拿到几百美元。 回来,我和李秋香带着另外一批学生到新叶村去了,把该补的工作都补上,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已经有了铁打般的信心。信心一上来,就坚定地确认,这个乡土建筑研究工作,是应该在全国规模化展开的。全国的展开,不过是我们的傻念叨,但我们自己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坚持做下去,还是有可能的。 新叶村的工作快结束的时候,村里的几位老朋友们陪我们造访了十几个村落,最后选定了二十几里外的诸葛村作为下一个课题。楠溪江嘛,只好再待一两年了。 这时候,楼庆西老师自告奋勇,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组合中来,我们形成了“三人帮”。 第二年春节前夕,我带着新叶村的书稿又到了台北,找到了一个建筑师的组织,跟他们约好,由他们出书,有多少收入都归他们,但先得给我些钱,我好着手往下做。这是高利贷。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出了几本书之后,大陆的出版社也会答应做了吧。跟学院申请经费,那是不可能的,在一次学生设计作业评分会之后,有几位教授竟然大声评论我们的工作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吃饱了撑的”!我们只好听着,万一压不住火,抬起杠来,说不定会闹得连暑期实习的学生都不分配给我们,我们能找谁画测绘图呀!没有测绘图,书的价值可就差了一大截了。 这本书在台湾倒是出版得非常快,但是,想不到,书的作者署名竟是那家建筑师组织的头头了。从头到尾,书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为了几个钱的经费,我竟把书的著作权都卖了吗?但我怎么去争呢?隔三差五,警察局的小头目还要到我家找我“聊聊天”呐!我一百零五岁的老母,几十年不见,多少相思,但为了怕那个满脸堆笑的警官,竟舍得催我快回大陆。 正在为难的时候,台北一个大学的建筑系邀我去讲讲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我去了,讲了。特别讲了讲我们在新叶村工作的时候,只有四五里路距离的另一个村子里有一组日本人也在做咱们乡土文化的调查研究。他们照相是黑白的、彩色的各两套,一套是照片,一套是录像,一共四套。而我们却只有一个营造学社留下的照相机,用的是黑白胶片。那些日本人,见到我们的寒碜相,笑眯眯地对我说:“你们不必拍照了,以后要什么照片,向我们要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们。以后中国乡土文化的研究中心肯定在我们日本。”讲到这里,听讲的学生们就有了点儿动静。我这个经历过整个抗日战争的人心里很难过,大声喊:“不可能!我们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研究中心建在中国!”一下子,学生们站了起来,又鼓掌,又呼喊,非常激动,有几个男女青年,走上来围住我,说:“坚持下去呀!”“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可以去参加工作吗?”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哪儿有什么“两个中国”呀,我们又能在文化工作上一齐打一次抗日战争了! 当天晚上就有一家出版社来了电话,约我第二天早晨在某个餐厅见面。我准时去了。出版社的老板很客气,也不乏热情,说了许多恭维话,目标就是,把我们每年的成果交给他们出版,他们可以预支稿费作为我们的工作经费。我提了一个每年需要大概多少钱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马上给楼庆西打了个长途电话,问问学校这件事可不可以做。第二天,来了答复,说是完全没有问题,连什么什么人的钱都能要。于是,这件事就定了,我写了个条子,签上我的名字。我要的每年的费用比我们在新叶村的花销高一些,因为考虑到还要把工作面扩大,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开辟。那样,不但交通费要高得多,而且不可能都像在新叶村那样,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人总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吃饭睡觉都要花钱,这是硬道理。甚至,我还想到,如果能一年完成两个或者两年完成三个课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份书稿自己另找出版社,在大陆试试如何! 有了点经费,多了一个人,我们就同时开展了两项工作:诸葛村和楠溪江中游村落的研究。 工作经费有了,就要动手干。不料,一年前把我们带到楠溪江去的当副厅长的老同学却忧心忡忡来劝阻我们了。他说,他是用小车把我们带去的,那很安全,而我们带着十几个学生乘长途汽车去,那可不行。因为,这条路线上,当时的记录是平均每天要发生死人的车祸八次,太危险了。不死,丢一条胳膊也够呛! 但是,楠溪江的村落太美了,人文气息太可爱了,不写它们,我们的工作会留下永远的遗憾。我们横下一条心,非去不可。不过,我们让了一步,包一辆中巴车去,毕竟有了出版社的预付款。那天很早钻进车厢,门一闭合,我们多少还有点玩命的感觉,“风萧萧兮易水寒”,生死由天。那车太不争气,大约是烂泥公路太颠簸了吧,一路抛锚,一路修理,晨前五点从杭州出发,后半夜两点钟才到永嘉。车子在瓯江边上修理的时候,我们见天上好大一个月亮,才知道那天是中秋节。 到了楠溪江中游一个预约好了的蘑菇罐头厂,吃了一点东西,倒头睡下。天一亮,就起来,按计划开始工作。男男女女的同学们,利利索索,神气活现,不喊累,不迷糊,我们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就这样干了两年,成果出来了,厚厚的一份楠溪江的稿子,交给了台湾那家预付了钱的出版社。诸葛村的嘛,还得再干一年才行。 不久,书倒是出版了,美编大过了一把瘾,把正正经经的学术著作的版面弄得花里胡哨,“桃红柳绿”,像儿童读物。原来,这家出版社就是以出儿童读物为主的。署名呢,封面勒口里面倒是有短短一排小于臭虫的字印着我们所在学校的名字。要找我们几个工作者的名字可难了,原来印在勒口的背面,也就是从来都空着的夹缝里,称呼是“主持”,模模糊糊。字的大小嘛,大约和跳蚤相仿。倒是并不寂寞,因为有杂志社全体三十一位工作人员的名单陪着我们,包括资料、印务、业务、财务等。只是没有清洁工。 更叫我们心里难过的是这些书在大陆不发行,买不到,而我们本来是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引起社会注意,推动研究抢救下一些村子。 我们看了这部书很吃惊,但是,我们毫无办法,我们还需要他们的预付稿费,否则,我们怎么工作呢?对于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决不动摇,但我们的困难和坚持,有谁知道,有谁理解,有谁能帮助呢? 于是我们只好豁出去了,不动声色,继续向这家出版社交稿子,一年一本,换取他们的出版和预支稿费,更要争取乡土建筑被人认识和重视。当时,我们的共同追求,就是只要这件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能够逐步被理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毕竟是为了国家的文化积累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而工作的,如果仅仅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早就另干别的了。 不过,事情很不顺利,出了四本书之后,继续把一本又一本的稿子陆续送去,而且是题材比较好、资料比较丰富的,却一本又一本地积压着,十几年过去积压了将近十本了,还没有出版的消息。一次又一次的追问,都只有模模糊糊的应付。我们并不图因这些书的出版一下子成了大名人,发了大财,但我们确实希望这些书能促使更多的人认识乡土建筑的价值,一起来动手研究,一起来动手维护。我们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颐养身体而上山下乡的,我们为交过去的稿子像石沉大海而焦急。 好在我们还留了个心眼儿,那家台湾出版社每年提供的费用做了一个课题后还能剩下一点,我们拿余钱再做一个课题,精打细算,吃苦耐劳,一年或者两年可以另外多写一本书,这成果就可以由我们自己处理了。英国有一家基金会给寄了三次钱来,在依规矩交了学校什么科室的“提成”之后,其余全部都用到了工作上,而且仍旧是精打细算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参加了上山下乡做测绘的男女学生,吃苦耐劳,没有半句怨言。到福建去工作,一位学校足球队的队长,饭量大,每餐吃了一大碗干饭之后,就“暂息”了,等大家都吃够了,放下筷子,他再来把大碗小碗打扫干净。 又一次,在陕西,调查黄土窑洞,也有两位大小伙子没有吃饱。有一天,正好需要到县城里去找资料,就叫他们俩搭伴去,特别叮嘱他们,“工作细一点,不着急回来,午饭在城里吃,吃好一点,记得要发票,回来找李老师报销”。不料,午饭前他们就赶回来了,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李老师一看见他们就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了。 其实,同学们早就知道我们缺钱,总是帮我们节省。第一次到楠溪江工作的时候,乡间只有机耕道,也没有公共交通车。哪天工作的地点远一点,就得早早起身去抢雇一辆三个轮子的“蹦蹦车”。比四个轮子的便宜了一半多。车小人多,大家就站着,车底盘又很单薄,所以这一辆车上重下轻。机耕道上老车辙一层叠一层,“蹦蹦车”几乎是跳着舞走,真是“蹦蹦”得厉害,有过好多次险情。有一天,在我们前面有一辆“蹦蹦车”,扬起漫天尘土。我请司机开慢一点,跟前面的车拉开点距离。不料,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没有那尘土了。我们把车开上去,下车一看,那辆“蹦蹦车”掉进江里了。幸好天旱,江边露了土,没有发生大事。出了这样的险,同学们仍然十分镇静,没有过一句扫兴话。 诸葛村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就到江西省婺源县去了。楼庆西先从安徽过去,我和李秋香为了顺便看望叶同宽老师,便乘汽车从建德、开化过“十八跳”这条路。不料,到了衢州,再向前去就没有公交车了,因为这一路当时土匪猖獗,车辆已经停开了。小客店老板说,土匪怕官,所以都知道哪些牌号的车不能抢,这路上,一个礼拜总会有几辆不能抢的车来往,运气好了,可以搭上回头车。我们在路口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一辆回头空走的公家车。坐上车,司机叫我们把照相机、钱包等等放在明处,万一土匪来抢,立刻奉上,就没事。那天在车号的保护下,平安到了婺源,住在清华镇。后来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公安分局的头头们叫我们雇用他们的囚车跑点,可以万无一失,一天二百五十元,否则难保安全。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鬼哭神号般地跑村,但他们不给任何凭证。有这样几天的囚车经历,倒也是一辈子的有趣话题。 有学生们的努力,我们把出版社提供的费用精打细算,再加上中外朋友们的零星支援,终于陆陆续续又额外挤出了几本书稿来。这时候大陆的出版社有了点活气,三联书店、重庆出版社和河北出版社,陆陆续续把我们用余钱写的几本书拿去出版了。毕竟乡土建筑自有它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书多少引起了一些大陆学者朋友们的留意,产生了一点点影响。渐渐地,以村落为单位的综合了地理、历史、文化的乡土建筑研究终于成了乡土建筑研究的正宗、主流,取代了单纯的艺术性或者技术性的以单个建筑为题的研究,于是,乡土建筑研究的价值、地位大大提高了。在我们的推动下,乡土文物建筑的保护,也以整个村子为单位了。住宅、寺庙以外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必需的建筑,受到了研究者和保护者的重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依靠二十多年的经验,提出了乡土建筑作为文物时的保护原则和方法,这原则和方法也已经被文物主管机关认可、接受,成为主流而普及了。 从浙江省新叶村开始的乡土建筑研究终于成了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虽然我们最重要的代表作或者只在台湾印了几本,或者还把稿子压在台湾的出版社。 这时候,我们这个小组又添了一个罗德胤。 正在这口子上,发生了三件叫我们高兴的事。第一件,台湾那家出版社息业了,不得不把积压在他们那里的我们几本书的原稿送到大陆清华大学出版社来出版了,也因此不得不按照大陆的出版规矩标明我们三个人是这些书的作者了。一出版,就有两本书得了碰头彩,一等奖。可惜书的装帧设计还是那家台湾出版社做好了的,把书搞得很贵,又不成样子。第二件,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把二十年前我们在台湾出版过的四本书重新出版了,印制都比较精致大方,没有了儿童读物式的花哨,像正经的学术著作了。同时,也正式标出了它们的作者的名字。第三件,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我们得到了老同学主持的规划设计院的经济支援,谢退了台湾那家出版社的钱了,我们只要实实在在地工作,像一个真正的学术工作者那样实实在在地工作就行了。 但是,还是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咱们大陆的出版社忽然改制了,都要我们支付出版费才能出书,价码可不低,于是,我这个老头子就不得不再去募化。向人讨钱,毕竟不是愉快的事情,有时候难免斯文扫地。好在早些年已经把读书人的傲骨粉碎了,既然能在权力前为苟生折腰,当然更不妨为抢救文化遗产把腰对折,来个“百炼钢成绕指柔”。 乡土建筑研究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的方法原则也大体在前二十年里成熟了。我们国家有几十万个村落,乡土建筑变化多端,到现在连它有多少个大系统都没有摸清。应该做的事太多了,而在当前的建设中,开发中,乡土建筑又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日夜去抢救还来不及,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挣钱之余顺手做些工作是万万不行的。我们要的是工作成果,不是要出几个声名赫赫的“专家”“学者”,名留青史而又口袋饱满的。 真学者都是老实人,缺心眼儿的! 但是,家徒四壁,这最后一段黄泉路怎么走?唉! 2010年5月 陈志华先生的一生,在两个研究领域中均获得了很高的成就。1989年之前,陈先生一直从事外国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颇为丰厚,是从事外国建筑史研究中,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者。1989年退休年限一到,陈先生便放下了之前的工作,从研究外国的东西,一步跨界到了中国乡土建筑的学科,并成立了乡土建筑研究组,将学术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陈先生也成为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一面旗帜。 ——李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