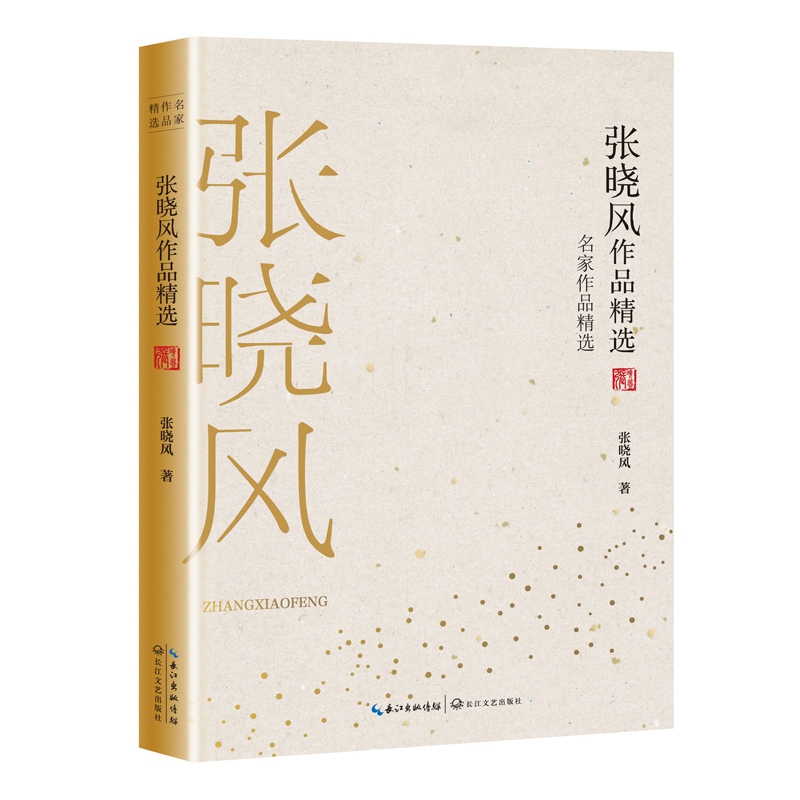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1.70
折扣购买: 张晓风作品精选(2019名家作品精选)
ISBN: 9787570212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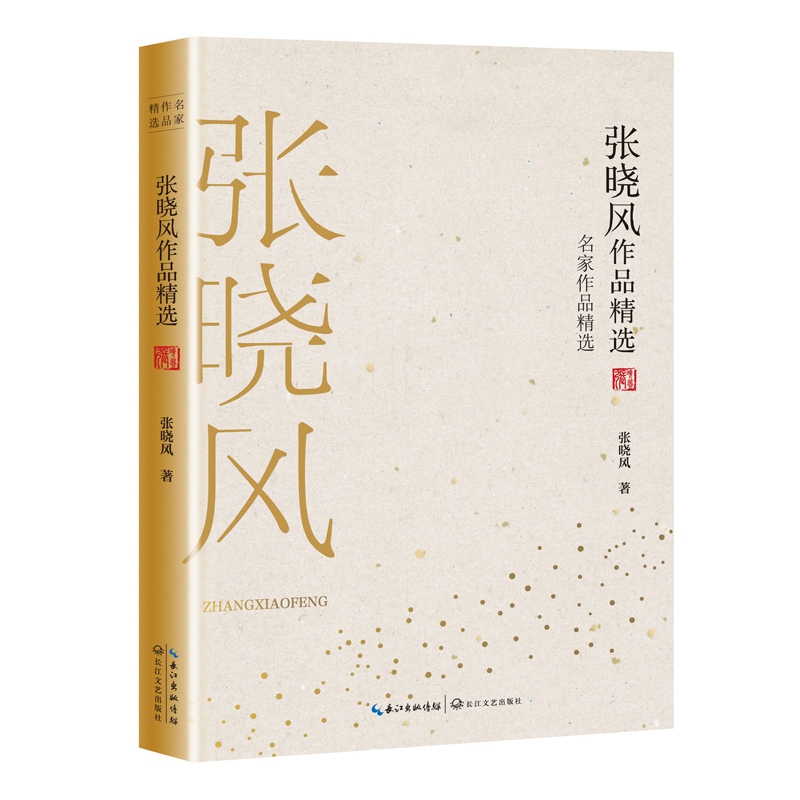
张晓风,台湾散文名家,原籍江苏铜山,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曾任教东吴大学和香港浸会学院、阳明大学。 张晓风创作过散文、新诗、小说、戏剧、杂文等多种不同的体裁,以散文著名,主要作品有《白手帕》《红手帕》《春之怀古》《地毯的那一端》《愁乡石》等。
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他们,他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忽然,我又看到他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了解他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还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唯一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 是的,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否则我们不必在春天勤生绿叶,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 当夜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里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红灯绿酒。而我们在寂静里,我们在黑暗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无论如何,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如果别人都不迎接,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 这时,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过来,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这就是我们最自豪的时刻了。是的,或许所有的人早已习惯于污浊了,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惜的清新。 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最快乐的,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虽然我们放弃了它。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 故事说完了,四下寂然。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可是,我听到他们深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故事至少感动了他们自己。然后,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 有些人 有些人,他们的姓氏我已遗忘,他们的脸却恒常浮着——像晴空,在整个雨季中我们不见它,却清晰地记得它。 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我连她的脸都记不起来了,但好像觉得她是很美的(有哪一个小学生心目中的老师不美呢?)也恍惚记得她身上那片不太鲜丽的蓝。她教过我们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但永远记得某个下午的作文课,一位同学举手问她“挖”字该怎么写,她想了一下,说: “这个字我不会写,你们谁会?” 我兴奋地站起来,跑到黑板前写下了那个字。 那天,放学的时候,当同学们齐声向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向全班同学说: “我真高兴,我今天多学会了一个字,我要谢谢这位同学。” 我立刻快乐得有如肋下生翅一般——我生平似乎再没有出现那么自豪的时刻。 那以后,我遇见无数学者,他们尊严而高贵,似乎无所不知。但他们教给我的,远不及那个女老师为多。她的谦逊,她对人不吝惜的称赞,使我忽然间长大了。 如果她不会写“挖”字,那又何妨,她已挖掘出一个小女孩心中宝贵的自信。 有一次,我到一家米店去。 “你明天能把米送到我们的营地吗?” “能。”那个胖女人说。 “我已经把钱给你了,可是如果你们不送,”我不放心地说,“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呢?” “啊!”她惊叫了一声,眼睛睁得圆突突,仿佛听见一件耸人听闻的罪案,“做这种事,我们是不敢的。” 她说“不敢”两字的时候,那种敬畏的神情使我肃然,她所敬畏的是什么呢?是尊贵古老的卖米行业,还是“举头三尺即有神明”。 她的脸,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遇到,我未必能辨认,但我每遇见那无所不为的人,就会想起她——为什么其他的人竟无所畏惧呢! 有一个夏天,中午,我从街上回来,红砖人行道烫得人鞋底都要烧起来似的。 忽然,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疲软地靠在一堵墙上,他的眼睛闭着,黎黑的脸曲扭如一截枯根,不知在忍受什么? 他也许是中暑了,需要一杯甘洌的冰水。他也许很忧伤,需要一两句鼓励的话,但满街的人潮流动,美丽的皮鞋行过美丽的人行道,但没有人驻足望他一眼。 我站了一会儿,想去扶他,但我闺秀式的教育使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如果他是疯子,如果他的行动冒犯我——于是我扼杀了我的同情,让自己和别人一样地漠然离去。 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那天中午他在眩晕中想必也没有看到我,我们只不过是路人。但他的痛苦却盘踞了我的心,他的无助的影子使我陷在长久的自责里。 上苍曾让我们相遇于同一条街,为什么我不能献出一点手足之情,为什么我有权漠视他的痛苦?我何以怀着那么可耻的自尊?如果可能,我真愿再遇见他一次,但谁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们并非永远都有行善的机会——如果我们一度错过。 那陌生人的脸于我是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对于代数中的行列式,我是一点也记不清了。倒是记得那细瘦矮小貌不惊人的代数老师。 那年七月,当我们赶到联考考场的时候,只觉整个人生都摇晃起来,无忧的岁月至此便渺茫了,谁能预测自己在考场后的人生? 想不到的是代数老师也在那里,他那苍白而没有表情的脸竟会奔波过两个城市而在考场上出现,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 接着,他蹲在泥地上,拣了一块碎石子,为特别愚鲁的我讲起行列式来。我焦急地听着,似乎从来未曾那么心领神会过。泥土的大地可以成为那么美好的纸张,尖锐的利石可以成为那么流丽的彩笔——我第一次懂得,他使我在书本上的朱注之外了解了所谓“君子谋道”的精神。 那天,很不幸的,行列式没有考,而那以后,我再没有碰过代数书,我的最后一节代数课竟是蹲在泥地上上的。我整个的中学教育也是在那无墙无顶的课室里结束的,事隔十多年,才忽然咀嚼出那意义有多美。 代数老师姓什么?我竟不记得了,我能记得国文老师所填的许多小词,却记不住代数老师的名字,心里总有点内疚。如果我去母校查一下,应该不甚困难,但总觉得那是不必要的,他比许多我记得住姓名的人不是更有价值吗? 到山中去 德: 从山里回来已经两天了,但不知怎的,总觉得满身仍有拂不掉的山之气息。行坐之间,恍惚以为自己就是山上的一块石头,溪边的一棵树。见到人,再也想不起什么客套词令,只是痴痴傻傻地重复着一句话:“你到山里头去过吗?” 那天你不能去,真是很可惜的。你那么忙,我向来不敢用不急之务打扰你。但这次我忍不住要写信给你。德,人不到山里去,不到水里去,那真是活得冤枉。 说起来也够惭愧了,在外双溪住了五年多,从来就不知道内双溪是什么样子。春天里曾沿着公路走了半点钟,看到山径曲折,野花漫开,就自以为到了内双溪。直到前些天,有朋友到那边漫游归来,我才知道原来山的那边还有山。 平常因为学校在山脚下,宿舍在山腰上,推开窗子,满眼都是起伏的青峦,衬着窗框,俨然就是一卷横幅山水,所以逢到朋友们邀我出游,我总是推辞。有时还爱和人抬杠道:“何必呢?余胸中自有丘壑。”而这次,我是太累了、太倦了、也太厌了,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鼓动着我,告诉我在山那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于是换了一身绿色轻装,趿上一双绿色软鞋,掷开终年不离手的红笔,跨上一辆跑车,和朋友们相偕而去。——我一向喜欢绿色,你是知道的,但那天特别喜欢,似乎觉得那颜色让我更接近自然,更融入自然。 德,人间有许多真理,实在是讲不清的。譬如说吧,山山都有石头、都有树木、都有溪流。但,它们是不同的,就像我们人和人不同一样。这些年来,在山这边住了这么久,每天看朝云、看晚霞、看晴阴变化,自以为很了解山了,及至到了山那边,才发现那又是另一种气象,另一种意境。其实,严格地说,常被人践踏观赏的山已经算不得什么山了。如果不幸成为名山,被些无聊的人盖了些亭阁楼台,题了些诗文字画,甚至起了观光旅社,那不但不成其为山,也不能成其为地了。德,你懂我了吗?内双溪一切的优美,全在那一片未凿的天真。让你想到,它现在的形貌和伊甸园时代是完全一样的。我真愿作那样一座山,那样沉郁、那样古朴、那样深邃。德,你愿意吗? 我真希望你看到我,碰见我的人都说我那天快活极了,我怎能不快活呢?我想起前些年,戴唱给我们听的一首英文歌,那歌词说:“我的父亲极其富有,全世界在他权下,我是他的孩子——我掌管平原山野。”德,这真是最快乐的事了——我统管一切的美。德,我真说不出,真说不出。我几乎感觉痛苦了——我无法表达我所感受的。我们照了好些相片,以后我会拿给你看,你就可以明白了。唉,其实照片又何尝照得出所以然来,暗箱里容得下风声水响吗?镜头中摄得出草气花香吗?爱默生说,大自然是一件从来没有被描写过的事物。可是,那又怎能算是人们的过失呢?用人的思想去比配上帝的思想,用人工去摹拟天工,那岂不是近乎荒谬的吗? 这些日子应该已是初冬了,但那宁静温和的早晨,淡淡地像溶液般四面包围着我们的阳光,只让人想到最柔美的春天,我们的车沿着山路而上,洪水在我们的右方奔腾着,森然的乱石垒叠着。我从没有见过这样急湍的流水和这样巨大的石块。而芦草又一大片一大片地杂生在小径溪旁。人行到此,只见渊中的水声澎湃,雪白的浪花绽开在黑色的岩石上。那种苍凉的古意四面袭来,心中便无缘无故地伤乱起来。回头看游伴,他们也都怔住了,我真了解什么叫“摄人心魄”了。 “是不是人类看到这种景致,”我悄声问茅,“就会想到自杀呢?” “是吧,可是不叫自杀——我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我站在长城上,四野苍茫,心头就不知怎的乱撞起来,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跳下去。” 我无语痴立,一种无形的悲凉在胸臆间上下摇晃。漫野芦草凄然地白着,水声低晃而怆绝。而山溪却依然急窜着。啊,逝者如斯,如斯逝者,为什么它不能稍一回顾呢? 扶车再行,两侧全是壁立的山峰,那样秀拔的气象似乎只能在前人的山水画中一见。远远地有人在山上敲着石块,那单调无变化的金石声传来,令我怵然以惊。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要开一段梯田。我望着那些人,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呢?当我们快被紧张和忙碌扼死的时候,当宽坦的街市上竖立着被速度造成的伤亡牌,为什么他们独有那样悠闲的岁月,用最原始的凿子,在无人的山间,敲打出最迟缓的时钟?他们似乎也望了望这边,那么,究竟是他们羡慕我们,还是我们羡慕他们呢? 峰回路转,坡度更陡了,推车而上,十分吃力,行到水源地,把车子寄放在一家人门前,继续前行。阳光更浓了,山景益发清晰,一切气味也都被蒸发出来。稻香扑人,真有点醺然欲醉的味儿。这时候,只恨自己未能着一身宽袍,好兜两袖素馨回去。路旁更有许多叫得出来和叫不出来的野花,也都晒干了一身的露水而抬起头来了。在别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山径上挥散着它们的美。 渐渐地,我们更接近终点。我向几个在禾场上游戏的孩子问路,立刻有一个浓眉大眼的男孩挺身而出。我想问他瀑布在什么地方。却又不知道台湾话要怎样表达,那孩子用狡黠的眼光望了望我。“水墙,是吗?我带你去。”啊,德,好美的名词,水墙。我把这名词翻译出来,大家都赞叹了一遍。那孩子在前面走着,我们很困难地跟着他跑,又跟着他步过小河。他停下来,望望我们,一面指着路边的野花蓓蕾对我们说:“它还没开,要是开了,你真不知有多漂亮。”我点头承认——我相信,山中一切的美都超过想象。德,你信吗?我又和那孩子谈了几句话,知道他已是小学五年级了。“你毕业后要升初中吗?”他回过头来,把正在嚼着的草根往路旁一扔,大眼中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神情:“不!”德,你真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羞愧。只自觉以往所看的一切书本、一切笔记、一切讲义,都在他的那声“不”中被否认了。德,我们读书干什么呢?究竟干什么呢?我们多少时候连生活是什么都忘了呢! 我们终于到了“水墙”了。德,那一霎直是想哭,那种兴奋,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人真该到田园中去,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原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啊,德,如果你看到那样宽、那样长、那样壮观的瀑布,你真是什么也不想了,我那天就是那样站着,只觉得要大声唱几句,震撼一下那已经震撼了我的山谷。我想起一首我们都极喜欢的黑人歌:“我的财产放置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远远地在青天之上。”德,真的,直到那天我才忽然憬悟到,我有那样多的美好的产业。像清风明月、像山松野草。我要把它们寄放在溪谷内,我要把它们珍藏在云层上,我要把它们怀抱在深心中。 德,即使当时你胸中折叠着一千丈的愁烦,及至你站在瀑布面前,也会一泻而尽了。甚至你会觉得惊奇,何以你常常会被一句话骚扰。何以常常因一个眼色而气愤。德,这一切都是多余的,都是不必要的。你会感到压在你肩上的重担卸下去了,蒙在你眼睛上的鳞片也脱落了。那时候,如果还有什么欲望的话,只是想把水面的落叶聚拢来,编成一个小筏子,让自己躺在上面,浮槎放海而去。 那时候,德,你真不知我们变得有多疯狂。我和达赤着足在石块与石块之间跳跃着。偶尔苔滑,跌在水里,把裙边全弄湿了,那真叫淋漓尽兴呢!山风把我们的头发梳成一种脱俗的型式,我们不禁相望大笑。哎,德,那种快乐真是说不出来——如果说得出来也没有人肯信。 瀑布很急,其色如霜。人立在丈外,仍能感觉到细细的水珠不断溅来。我们捡了些树枝,燃起一堆火,就在上头烤起肉来。又接了一锅飞泉来烹茶。在那阴湿的山谷中,我们享受着原始人的乐趣。火光照着我们因兴奋而发红的脸,照着焦黄喷香的烤肉,照着吱吱作响的清茗。德,那时候,你会觉得连你的心也是热的、亮的、跳跃的。 我们沿着原路回来,山中那样容易黑,我们只得摸索而行了,冷冷的急流在我们足下响着,真有几分惊险呢!我忽然想起“世道艰难,有甚于此者”,自己也不晓得这句话是从书本上看来的,还是平日的感触。唉,德,为什么我们不生作樵夫渔父呢?为什么我们都只能作暂游的武陵人呢? 寻到大路,已是繁星满天了,稀疏的灯光几乎和远星不辨。行囊很轻,吃的已经吃下去了,而带去看的书报也在匆忙中拿去做了火引子。事后想想,也觉好笑,这岂是斯文人做的事吗?但是,德,这恐怕也是一定的,人总要疯狂一下、荒唐一下、矫时干俗一下,是不是呢?路上,达一直哼着《苏三起解》,茅喊他的秦腔,而我,依然唱着那首黑人名歌:“我的财产放置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远远地在青天之上……” 找到寄车处,主人留我们喝一杯茶。 “住在这里怎样买菜呢?”我们问他们。 “不用买,我们自己种了一畦。” “肉呢?” “这附近有几家人,每天由计程车带上一大块也就够了。” “不常下山玩吧?” “很少,住在这里,亲戚都疏远了。” 不管怎样,德,我羡慕着那样一种生活,我们人是泥作的,不是吧?我们的脚总不能永远踏在柏油路上、水泥道上和磨石子地上——我们得踏在真真实实的土壤上。 山岚照人,风声如涛。我们只得告辞了。顺路而下,不费一点脚力,车子便滑行起来。所谓列子御风,大概也只是这样一种意境吧! 那天,我真是极困乏而又极有精神,极混沌而又极能深思。你能想象我那夜的晚祷吗?德,我真不信有人从大自然中归来,而仍然不信上帝的存在。我说:“父啊,叫我知道,你充满万有。叫我知道,你在山中,你在水中,你在风中,你在云中。叫我的心在每一个角落向你下拜。当我年轻的时候,教我探索你的美。当我年老的时候,教我咀嚼你的美。终我一生,叫我常常举目望山,好让我在困厄之中,时时支取到从你而来的力量。” 德,你愿意附和我吗?今天又是个晴天呢!风声在云外呼唤着,远山也在送青了。德,拨开你一桌的资料卡,拭净你尘封的眼镜片,让我们到山中去! 华语文坛大家张晓风半个世纪代表作品, 全面呈现作家散文、 小说、戏剧、杂文四个创作领域的重要成果 余光中、席慕蓉、蒋勋推崇的一代文学名家 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