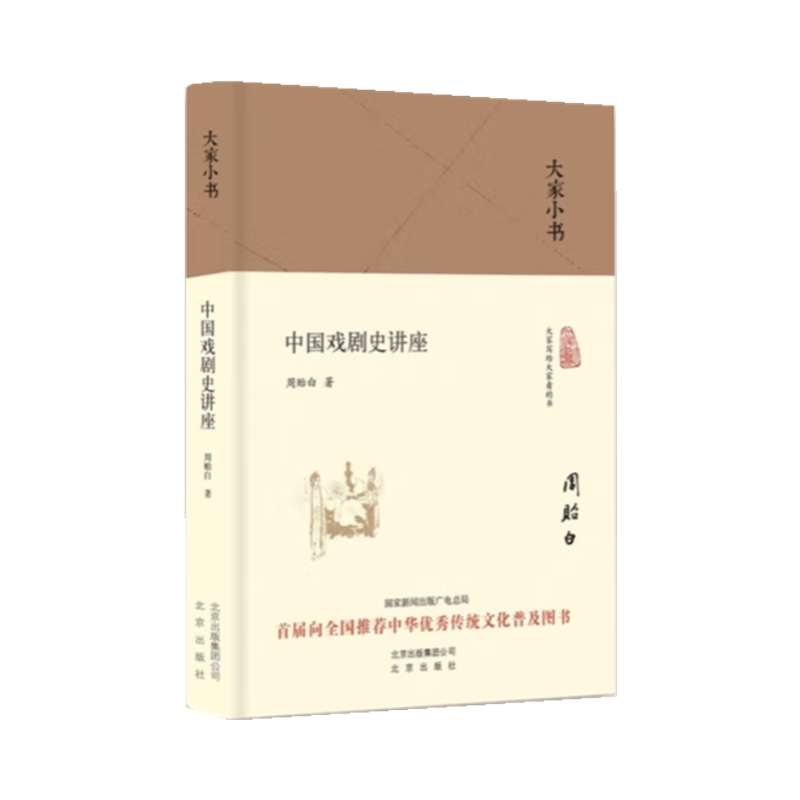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2.80
折扣购买: 中国戏剧史讲座(精)/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0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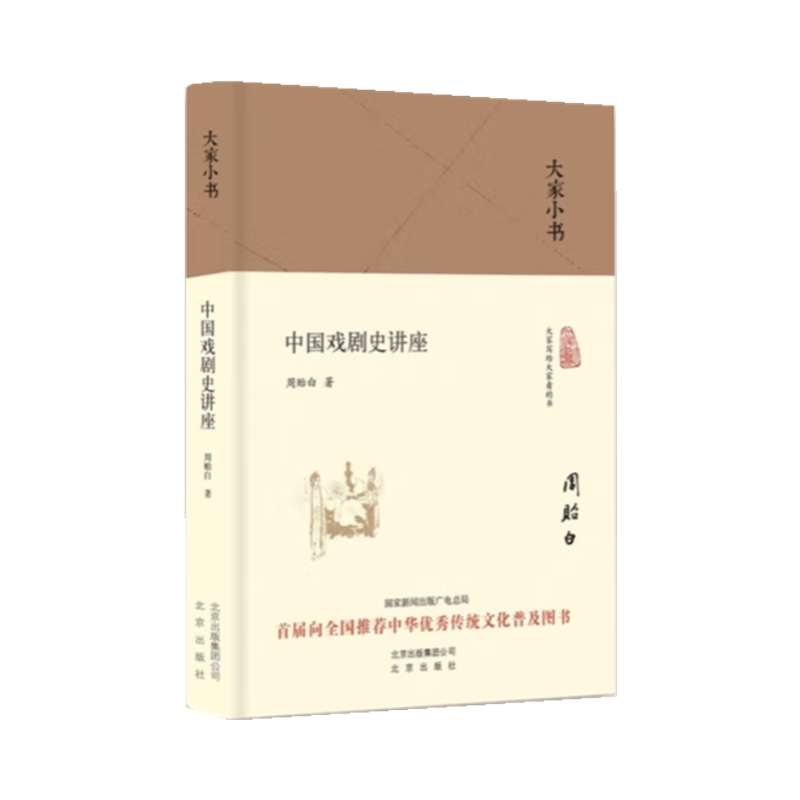
周贻白(1900—1977),湖南长沙人,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自幼家贫辍学,后搭班学艺,1927年参加田汉主持的南国社。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复旦大学、中央戏剧学院。曾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演出并出版的话剧作品有《李香君》《花木兰》《金丝雀》《阳关三叠》《连环计》《天之骄子》等;参与拍摄的电影有《苏武牧羊》《卓文君》《聂隐娘》《红楼梦》《李香君》等;著有《中国戏曲史略》《中国剧场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史长编》等。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时代(公元1101—1125年),蔡京为宰相,宦官童贯做上将,一将一相,在朝专权用事。太宰郑居中,起初和蔡京往来颇密,后来因他曾替蔡说过好话,蔡京没有酬谢他,遂意见相左。他因为母亲死了,暂时休官回乡守制。那时候,童贯领兵在燕蓟一带和辽兵交战,失败逃回。有一天,内廷宴会,教坊演杂剧。装扮着三四个婢女上场,各人的首饰头髻都不同:第一个是在额头梳着一个发髻,自称:“蔡太师家的。”人家问她:“你梳的头髻怎么这样?”她说:“我们太师每天都和皇帝见面,这叫朝第二讲 唐代传奇文与北宋杂剧 天髻!”第二个头髻偏在一边,自称:“郑太宰家的。”问她:“你这是什么式样?”她说:“我们太宰回乡守孝,不问朝政,这叫懒梳髻。”第三个把头发分开梳成许多发髻,堆满一头,自称:“童大王家的。”问她:“你这又是什么?”她说:“我们大王正在和敌兵交战,这叫三十六髻!”(髻谐计音,俗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意指童贯兵败逃窜。)(见《齐东野语》)这种以当时的现任官为题材,明指其人而致以讥讽,显然是单独一场戏;但以女婢三四人登场,其为男优所扮或女性所装虽未确知,但唐代“参军戏”在北宋发展成为“杂剧”,而“北宋杂剧”之不拘形式,由此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个例证,也是讽刺蔡京的。当时蔡京建议,铸造一种大铜钱,名为当十钱,一个钱当十个钱用。内廷宴会演杂剧,优人扮作一个卖豆腐浆的小贩上场,另一人上来喝了一碗豆浆,给一枚当十钱叫他找回九个钱。卖浆人说:“我刚上市,没零钱,您多喝两碗罢!”喝浆的连喝了五六碗,捧着肚子说:“喝不下去了!一个当十钱也不能找零,要是我们相爷改成当百钱又怎么办呢?”赵佶听了,也觉得不大对劲,由是不再发行大钱。(见《独醒杂志》) 以上举的这些例证,都是当时内廷的一些节目,但把这些节目联系起来,其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面对着当时的皇帝来讥讽或嘲骂一般朝廷权贵。因为这一些伶工都是教坊中人,属于官方的倡优,有职有俸,所以无法奈何他们。然而,这些伶工能够在政治上找题材,并代替人民说出心里的话来,像骂童贯,骂蔡京,则不仅为了逗笑而已。比方“当十钱”这个节目,把它放在一项故事表演里作为本身情节中一个过场的穿插,是不会太感凿枘的。所以,我认为北宋时代的杂剧,不一定都是简短的形式,三言两语就完了;其间也许有专门表演一个故事,而只以诙谐嘲笑的场子来作为穿插的。不过,在当时的内廷演出,却没有这类材料可作引证。其以故事情节为主,按照情节分别人物而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表演出来,实不在内廷而在民间。正如唐代的《踏摇娘》一样,当时的宫廷里歌舞尚未合一,她已经“且步且歌”了。北宋时代的杂剧在民间已作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表演,显然还是唐代《踏摇娘》一类的东西继续在民间发展的结果。同时在表演形式上也逐渐成为有歌唱、有音乐伴奏、有舞蹈,也有诙谐取笑,甚至有杂技,有武术。事实上已经和近代的中国戏剧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那么,在当时的民间杂剧,又是怎样一种演出情况呢?那就是在北宋时代,民间已经有了所谓“勾栏”了。 “勾栏”,本来是“栏杆”的别名,因其所刻花纹皆相互勾连,故有此称。并且在唐代已成普遍用语,如唐王建诗:“风帘水阁压芙蓉,四面勾栏在水中。”又李颀诗:“云华满高阁,苔色上勾栏。”在北宋时代,民间表演各项技艺的地方,一般叫“瓦子”。“瓦子”的意思,有人解释作“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事实上是一个广场,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故称“瓦子”,亦即“瓦砾场”的意思。当时一班流浪江湖、专靠卖艺营生的人,不管是“说唱故事”、“演杂剧”、“跑马卖解”、“摔跤”(当时名为“相扑”)或者表演种种“杂技”,统称为“路歧人”。“路歧”,就是指这班人日常东奔西走,徘徊歧路献技谋生。宋苏轼和周邠长韵诗:“俯仰东西隔数州,老于歧路岂伶优。”则专指扮演杂剧者,似未得其真解。这班“路歧人”自己的术语,管就地卖艺叫“作场”,也叫“做场”。其“作场”的地方,设有布棚,四周用荐席围上,或亦备有坐具如木凳之类,俗称“看棚”,或名“邀棚”。表演杂剧者,则于“看棚”中心另画一区,围以低矮的栏杆。因此,当时把这类有栏杆设备的“看棚”,通称为“勾栏”。这名称,一直到元蒙时代还沿用着。在元代,表演杂剧者女性占多数,因为生活所迫,有兼操妓业者;或本为妓女,偶一串演杂剧者。于是以“勾栏”作为妓院的代称,其实“勾栏”并不等于妓院,应当把它分别清楚。 勾栏虽然是民间表演杂剧的地方,但看棚就不一定专门表演杂剧。凡属一项技艺或多项杂耍在这种搭有棚帐的比较固定的地方演出,都叫“看棚”。一般是给钱入座或围立在所设的场子四周而由献技者在某一节目告终时收费,俗称“零打钱”。在当时的东京,有一个桑家瓦子,分为中瓦、里瓦,共有勾栏五十余座。有“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等名称,最大的棚子,可以容纳几千观众。当时亦称“勾栏”为“构肆”,则兼指一切表演技艺的“看棚”。因此,有专演杂剧的“看棚”,也有掺杂其他技艺的“勾栏”。换一句话说,这时候虽然有了“杂剧”这个称谓,还没有完全脱离“百戏”的范围,因而有些规模较小的杂剧节目,比方像内廷所演的那类玩意儿,便不够一场戏,所以只能夹在其他技艺的表演中作为一个节目。但因“民间的杂剧”,已渐包括其他艺术部门而走上综合艺术的道路,其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实为沿着故事表演的这条主线逐渐发展而来,故不至为“内廷杂剧”那种仍具有“参军戏”的形式所拘系。中国戏剧之能够形成一项独立艺术,这也是一个关键。同时,这时期的杂剧演出,既有专演杂剧的“勾栏”,又有兼演其他技艺和杂剧的一般“看棚”,这,正好表现出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时,在过渡时期的演出上的一种状态。根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说:“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很明白,这是一个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杂剧。这条记载虽然不到三十个字,却可以从当中看出一些情况来:第一,这个《目连救母》杂剧,是在一个专演杂剧的勾栏里演出的。第二,从七月初八起至十五日止,要连演八天。如果不是一本接一本地上演,而是每天都演的是这一个节目,那也可以说明这个杂剧在当时是如何耸动观众,所以才能够这样持久不衰地演八天。第三,根据旧日民间的习俗,“中元节”是旧历七月十五日,为追荐亡过的祖先的日子;还有一种意义,在佛典中,七月十五日是举行“盂兰盆会”的日子。(“盂兰盆会”的来源,就是由《目连救母》这个故事而产生的一种救拔或超度的仪式,俗称“放焰口”。)其于七月初八到七月十五上演《目连救母》杂剧,显然是为了照应这个民间习俗的“中元节日”。那么,这个杂剧,应为一种应景的节目。第四,《目连救母》这个故事,情节虽然不太复杂,但其间具有“救母”的一番经过,在这番经过中,大可以穿插一些“关目”(关目指部分的情节),因而连演七八天,也非不可能的事。有此四点,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当时的民间所演的杂剧,是和内廷那些节目不同的。至少,当时的内廷还不曾发展到根据一个故事的情节连演或每天如是地延续到七八天。如果不是在民间的广大观众面前,根据民间的习俗而取材,从故事内容出发而作编排,就不会有这类节目产生。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