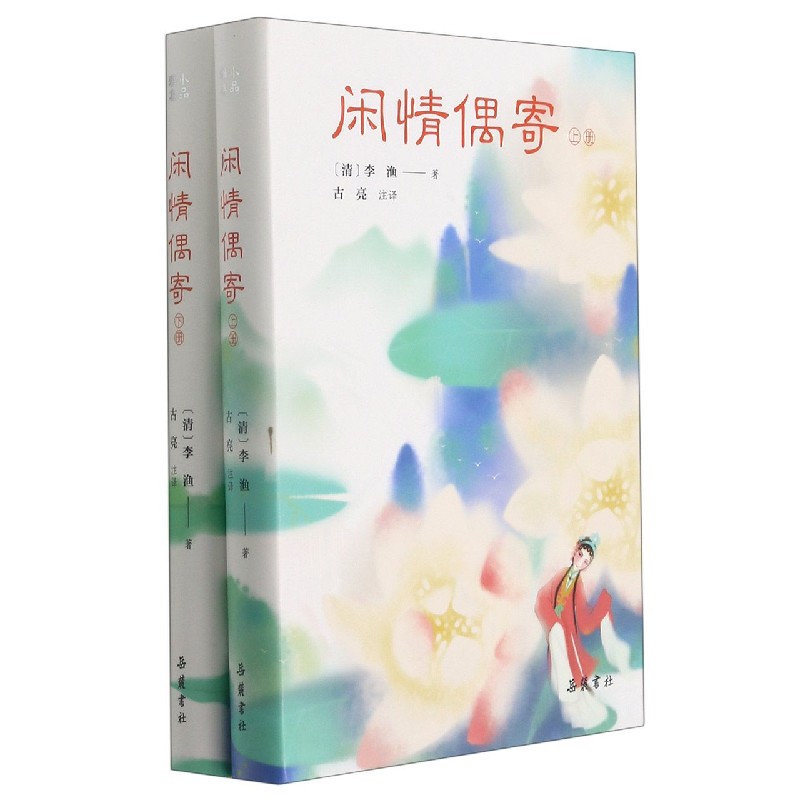
出版社: 岳麓
原售价: 85.00
折扣价: 52.70
折扣购买: 闲情偶寄(上下)(精)
ISBN: 9787553812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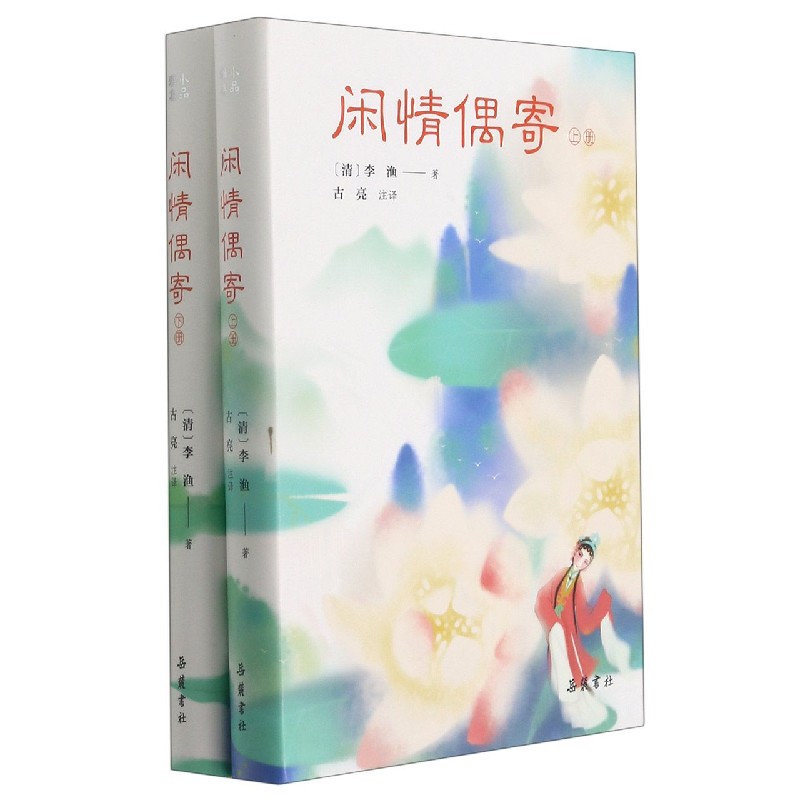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金华兰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他自幼聪颖,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曾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他一生著述丰富,著有启蒙读物《笠翁对韵》。
卷一词曲部上 结构第一 填词一事,向来被文人们看作末技。然而若能放下身段去做这件事,还是胜过跑马比剑,酗酒赌博。孔子曾经说过:“不是有掷彩博弈的游戏吗?玩玩这个也比闲着好。”博弈虽然是游戏,但也好过整天吃饱了饭,什么事都不用心;填词虽然是小道,可还是比博弈好吧?我觉得技艺不论大小,贵在能够精湛;才能不论高低,利在善于运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既能精湛又善运用,就可以扬长避短,成名成家。不然的话,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作文只会堆砌典故,著书空发无用之论,写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填词这件事,不仅文人干好了足以成名,即使是前朝帝王,也有因为擅长本朝词曲而使国事彪炳千古的。请让我一一道来:高则诚和王实甫都是元代名士,除了填词,没有其他成就;假如这两人没有创作《琵琶记》和《西厢记》,那么今天谁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所以,高则诚和王实甫是因为《琵琶记》和《西厢记》才得以名垂青史。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所作诗歌、文章和书札都值得一读,而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并不是诗歌、文章和书札,而是戏剧《牡丹亭》。假如没有创作《牡丹亭》,那么汤显祖在当时就已经是有其人而无其名,更不用说以后的影响了。所以,汤显祖是因为《牡丹亭》才得以名垂青史。这是文人因填词而成名的实例。 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汉史”“唐诗”“宋文”“元曲”,人人都能脱口而出。《汉书》《史记》千古流传,不可磨灭,很久远了。唐代诗人辈出,宋代文士众多,在文坛,汉唐宋三代称得上鼎足而立,是夏商周这“三代”之后的又一个“三代”。元代统治的天下,不仅是政刑礼乐没什么值得效法的,就连语言文学,图书文章这些微末小事,也未见有什么成就;倘若不是元人崇尚词曲,有《琵琶记》《西厢记》以及《元人百种》这些书流传后世,那么当时的元代,也就会像五代、金、辽一样湮没在历史中,哪里还沾得上汉唐宋三代的光,被学士文人挂在嘴上呢?这是帝王国事因填词而成名的实例。由此看来,填词并不是末技,而是与史传诗文同源的另一支脉。近来倾慕填词,努力想要追步元人,比肩汤显祖的人很多,然而实际上作者还是寥寥无几,没听说什么绝世佳作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词曲创作只能通过阅读前世书籍来学习,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遵循。在没有灯光的暗室里,明眼人和盲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找不到路径,所以没有人指点迷津不足为怪。而且半途而废的人居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人也为数不少。 我曾经奇怪:天地之间每一种文字都可以在书本上找到与之相应的法脉准绳,这和耳提面命没什么区别;只有词曲创作一事,不仅仅是简略至极,甚至搁置一边,只字不提。揣摩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点: 第一,填词的道理艰涩深奥,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词曲作者,每当思绪奔涌,冲入云霄之际,就会魂魄飞越,如入梦境,不到篇章创作的终结,他的精神不会恢复常态。讲述真实的东西很容易,描绘梦幻般的东西则很难,所以不是不想传授,而是无法传授。果真如此,那可确实是真奇怪真困难,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了。我认为这种最精深的道理,讲的都是最上乘的学问,填词的学问并不都是这样,难道因为精深的道理难以形诸语言,而粗浅的道理也搁置不论吗? 第二,填词的道理变幻无常,说它应该是这样的,又有不应该是这样的。比如为生旦填词,贵在端庄文雅;为净丑作曲,定要幽默诙谐,这是常理。可是如果遇到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生旦,端庄文雅反而不合适;对于性情迂腐、不知变通的净丑,幽默诙谐则是忌讳。像这样的事情,不能死板地局限于陈规。因为怕以陈规旧习误导拘泥于古训的作者,所以宁肯付之阙如,也不画蛇添足,言无益之事。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变幻之理,不但适用于填词制曲,连科举帖括,赋诗作文也都适用,难道还有以一成不变的章法写文章,却会得到人们的赏识,世代流传吗? 第三,历来名士十有八九都以诗赋得人垂青,以词曲传名后世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千百人中也只有一个吧。而凡是能以词曲传名的人,都将其中的法门像宝贝似的珍藏着,秘不示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法门不是其他任何人传授给我的,为什么单单要我传授给其他人。假如家家户户都填词制曲,那么无论世间有多少《阳春》《白雪》一样的高雅作品,深谙鉴赏之道的人未必不会从晚出的作品中挑选出佳作,使才能平庸的前辈相形见绌;而且如果像周瑜那样精通音律鉴赏的人越来越多,频频指出词曲中的瑕疵,使前人的缺点和不足暴露无遗,这就好比一个善射的后羿调教出无数个善射的逢蒙,最终使自己吃亏受害一样,不如还是仿效前人,三缄其口,默不作声为好。 虽然词曲创作之道不传于世,上述三个原因是并列的,但据我个人揣摩,最后这个原因应该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文章乃是天下公器,不是我个人所能私有的;其中的是非,古来自有定评,难道是我个人可以颠倒的吗?不如倾尽我个人之所有,将它们公之于众,把天下后世所有名士贤人全部视为同道,胜过我的我把他当作老师,但同时也不妨碍他成为给予我启示的得意门生;与我相近的我把他当作朋友,这也是一条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途径。怀有这样的心态,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平生所知所学和盘托出,对于前人流传至今的书籍,也会自然而然地取其优长,弃其缺陷,辨其精华,识其糟粕,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以免在读书时被误导。理解我,怪罪我,怜悯我,甚至杀害我,全由世人,我不会顾及以后的事情。唯一担心的是,上面我所说的,自认为正确而不一定正确;世人所赞同的,我认为错误而不一定错误。我所说的完全是出于公心,如若不公,甘愿接受千秋万代的惩罚。哎,元代的先贤们如果复生,一定会原谅我的。 通常填词最重要的是音律,而只有我以结构为先,这是因为音律有书籍可以参考,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自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问世以来,阴阳平仄之间的界限已经清晰可见,就像水里划船,岸上推车一样,稍微懂得一点遵循章法的人,想要犯错误也不太可能了。程明善《啸余谱》和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问世之后,填词者更是可以依葫芦画瓢,创作有了明确的样本。前人把制曲叫作“填词”,填是“分布”的意思,就像在棋盘上按规定画着格子,见一格子,布一棋子,只有黑白之分,从来不会把棋子下到格外。需要用韵,我就押韵,不需要用韵,我就随意发挥。至于音律的和谐,音质的优美,虽然神妙而难以言喻,也可以由勉强为之发展到挥洒自如,由墨守成规而渐趋化境。至于结构,则应当在捻笔挥毫,创制音律之前就加以谋划。这就好像自然界为人体塑形,应当在精血刚刚凝结,胚胎尚未发育完善之际,就制定出完备的形态,让微小的精血具备五官和骨骼的雏形。如果事先没有完备的形态,而是从头顶到脚跟,一段一段地生长,那么人的躯体恐怕会有无数断断续续的痕迹,血气也会因此而阻滞其中。 工匠建造房屋也是这样。在地基刚刚平整,房屋间架尚未确立之际,应当先筹划好哪里建厅堂,哪里开窗户,造房梁需要什么木材,一定要等布局成熟,才能开工建造。如果建成一部分再去筹划一部分,顾前不顾后,必然会导致改建一部分以适应另一部分,房子还没建好就已经毁了。就像古人说“筑舍道傍,三年不成”,本来能够用来建造几座房子的资金,还不够建造一厅一堂了。所以创作戏曲的人,不能急于动笔,只有成熟的前期筹划,才换得来之后的奋笔疾书。有奇妙的素材,才写得出奇妙的文章,失败的命题是不可能使作者文思泉涌文采飞扬的。我曾经阅读过一些时下流行的戏曲作品,为作者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作品却无法配乐演出感到惋惜。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审音配乐非常困难,而是因为整部作品的结构缺乏妥善的安排。 词曲的文采似乎不必急于讨论,而我讨论文采也在音律之前,因为才华和技能是有区别的。稍有文采的人就可以称作才人,深通音律的人终究只是艺士。师旷只会鉴赏音乐而不会作曲,李龟年只会评判词的好坏而不会填词;假如让他们与词曲作家同处一堂,我肯定他们会坐在末席。有些事情虽然细微,却必须严格对待,这就是一个例子。 1.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生活艺术指南!玩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机趣新颖,言词浅明隽永,堪称中国古代生活美学之典范。 2.全文精心翻译,注释详尽,生僻字注音、释义,无需古文基础,全书阅读无障碍。 3.32开精装,轻便易携带,装帧时尚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