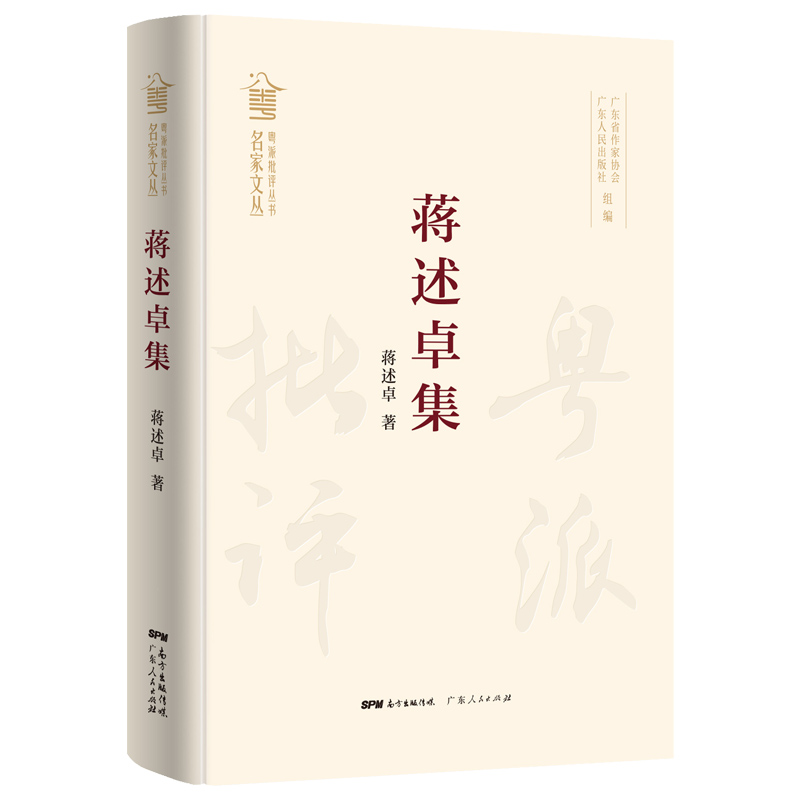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1.92
折扣购买: 蒋述卓集(粤派批评丛书?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144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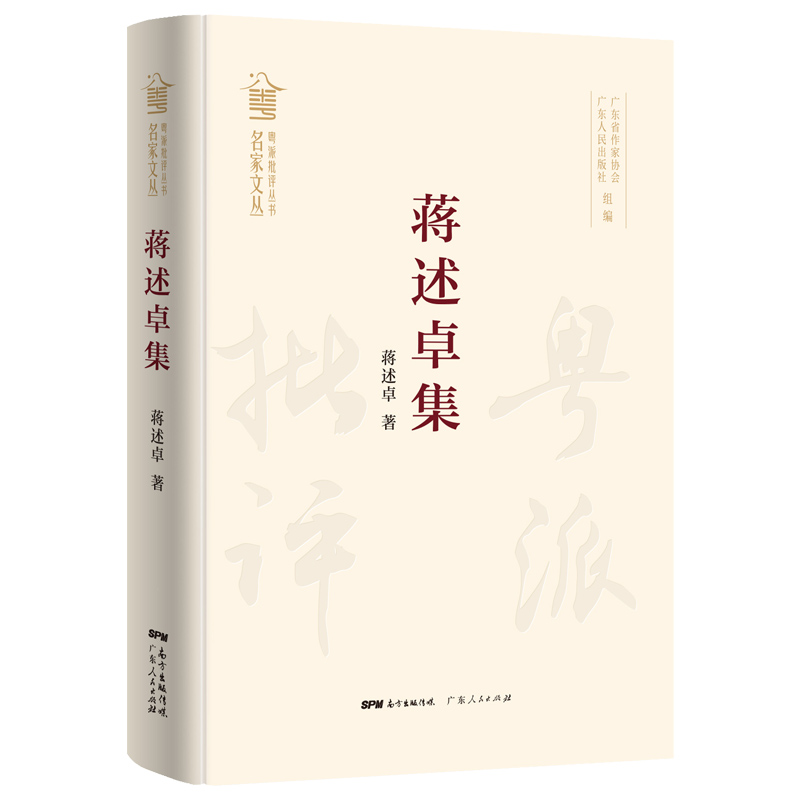
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 文学批评走到了世纪的门槛边了,理应不再犹豫与彷徨,然而,1978年以来,批评在经过拨乱反正、反思、引进与探索新方法等阶段以后,现在仍然对“如何行”的问题感到迷惑。批评何为?批评价值取向何在?运用什么话语进行批评的操作?诸多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批评以什么形态迈过这个“世纪之槛”,就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 时下文坛多在讨论批评的失语问题。这种失语,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批评家面对多元化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意识形态”“反映生活”“生活真实”“风骨”等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派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看似有语实则无语。因为:第一,他们完全套用西方的语言,让西方的语言淹没了他们的思想见解,也淹没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第二,由于他们把“技巧抬高于素材之上,把分析抬高于叙述之上,把批评家抬高于作家之上”,故不仅得不到大众的承认,也得不到作家们的承认。有的作家就宣称先锋派批评花样翻新,却并未深入作家之“心”与作品之“心”。先锋派批评语言与概念的“狂欢”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当剥去它们那些词藻、术语以及袭用西方的分析套路以后,却发现那些语言与概念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失语的产生绝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在逃避,都在退隐。它们逃避现实,逃避崇高,逃避理想,也逃避文化(有的虽写文化却只是猎奇)。先锋派批评之所以在1990年以后操持起西方的一套语言而驰骋文坛,只是因为当时文坛与思想界都处于价值真空的时期。面对汹涌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和文化探索锋芒的暂时受挫,作家与批评家都陷入了困惑之中。由于缺乏理性光芒的照射、理想的指引和价值基点的支撑,只好“跟着感觉走”。丧失了思想与理性,丧失了价值选择,把西方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也就成了唯一也是合理的选择。 失语的产生,又是一个文化机制与批评系统不成熟的表现,先锋派批评家大量使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并没有加以严格的限定以及文化的过滤与转换,很多情况下是在不确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且把一些明显并不现代的作家也硬拉入后现代的圈子来评论,从而造成了批评的零散、分裂与自相矛盾。在那一系列的批评文章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阐释系统,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语词、模仿的文体与叙述套路。先锋派批评家亦如先锋派作家,模仿西方的套路和方法,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通货”。 我并不反对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事实上,在如今的世界,没有哪一种文化是能够独立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文化的交流不可阻挡,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也是必然之事。然而,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不能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输入它们必须得到本土文化的认同、融合,并且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如果引进与移植仅仅停留在理论独白的角色,而不进入本土文化的语境,这种引进与移植就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尽管喧闹一时却难以扎下根来并长成茂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来术语与理论的目的必须明确,它不应该是临时的应对工具,也不是仅仅为了否定传统而做大面积的术语换代,而是为了重建自己的文化与阐释系统,包括批评系统。这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思想。 二 于是,建立一种新的阐释系统就刻不容缓地成为我们当下重要的任务。这种新的阐释系统就是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戏仿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处在什么时候,文化必然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心态、精神和品格。文化又是综合的,从综合的角度去批评文学则可避免偏执一端的弊病,如只以文本为中心的语义学批评、只从社会学角度的社会学批评,总会存在某些缺陷。文化诗学能带来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也会更为深刻地剖析文学。从文学批评史上看,立足于文化,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总会比单一的阐述角度显得深刻很多,分量也厚重得多。如中国古代的刘勰,近代的王国维、鲁迅,西方的马克思、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歌德、葛兰西、巴赫金、罗兰?巴特等。文学批评家应该兼文化哲学家。在目前的中国,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一身二任的人物。我们希望多一些文化哲学式的文学批评家,或许能使中国文学批评真正形成系统,具备大家气派,出几位批评巨人。 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其内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个层次: 1.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 2.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批评家要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反映历史、思考历史,观照当下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趋势。 3.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人文关怀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格建设上。作品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文学作品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培养人、塑造人。江泽民提出“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也就是要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批评家要帮助作品实现这一重要任务。 在第一层次上,主要是解决一个叙述者文化立场与文化背景问题。因为我们分析作品,不仅仅是分析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背后的文化背景,即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站在什么文化立场上这么说”。作者描绘一种社会生活,必然表示着他对这种社会生活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作者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根基,决定着他“说话”的深度和厚重度。 在第二层次上,主要是解决文学作品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即要看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是否能够复现文化或呈现文化的当下状况,并且符合当时社会状态存在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批评家往往要把作品当做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将其放置在文化的大环境内去考察。斯蒂芬?葛林伯雷说过:“伟大的艺术是文化的复杂的斗争与和谐的超常灵敏的记录。”从文化角度去批评文学,自然会涉及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模式。 在第三层次上,主要是解决一个批评的时代性问题。批评与创作一样,都要紧跟时代。批评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对文化进行消解,只破不立。批评作用于读者,绝不仅仅是介绍与推销、沟通与传达,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陶冶情操、宣扬理想、塑造人格。这也是批评体现文化关怀的重要方面。 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主要在一种文化对话中来建立,这种对话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现在和未来的对话、作者与大众对话、作品与社会的对话。这种阐释系统的立足点还是文化,运用的概念、术语应该是中西方相融合的产物。这是因为,近百年来的批评理论已经很西方化了,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中国文化传统,要体现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如果仅从翻译西方文学批评而言,要尽量做到如钱钟书先生提到的“化境”,使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真正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并不是指词语字面上的中国化,而是指词语表面上能真正体现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对接与融合。文化上的对话是一种处于平等地位上的对话,而不是一种侵袭和强权。词语上完全照搬不是对话,并不能建立起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由于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异质,照搬的词语往往游离于本土文化之外,难有生命力。先锋批评大量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词语而进入不了大众的层面,就是因为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如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这种阐释系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必须做到中西融合,使其具有更强更广大的可接受性,同时这也是使中国文学批评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最佳选择。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必须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使文学作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的最佳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