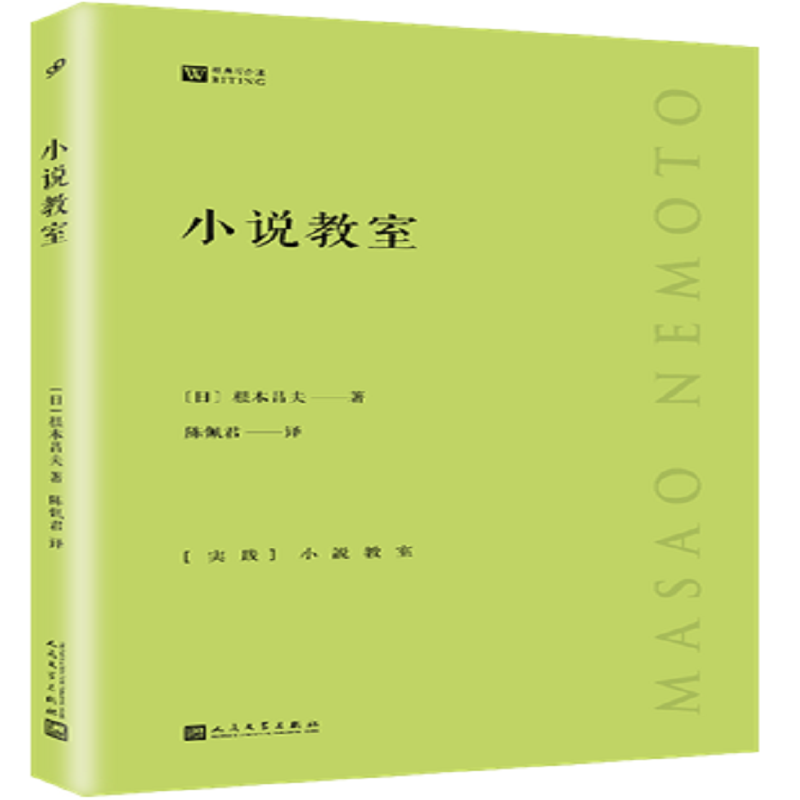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3.10
折扣购买: 小说教室(经典写作课)
ISBN: 9787020145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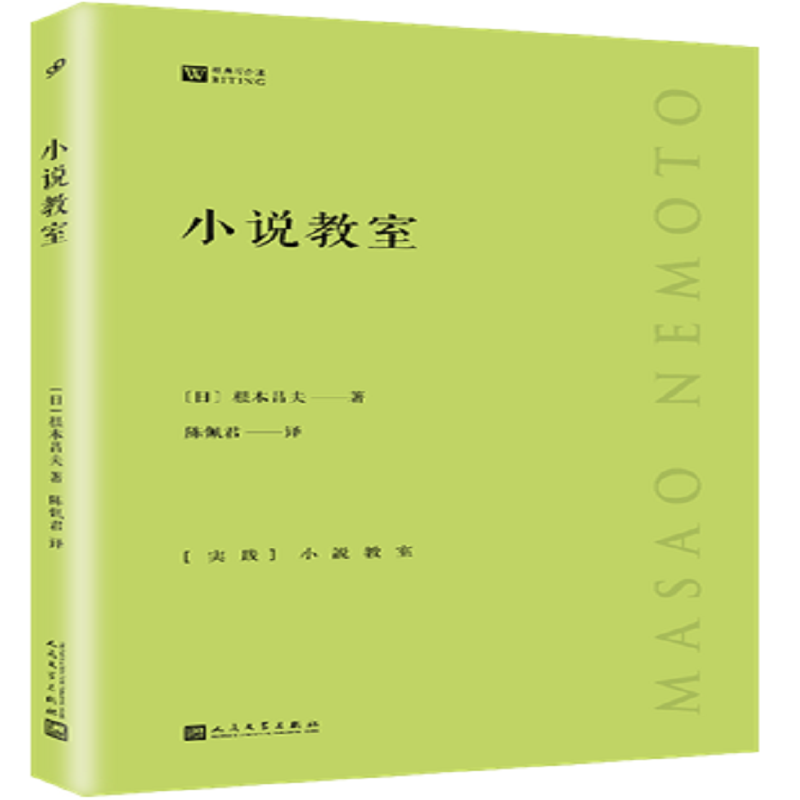
根本昌夫 Masao Nemoto 文艺丛书编辑,日本法政大学、帝京大学、明治学院大学讲师。他出生于1953年,从参与早稻田文学编辑室工作开始展开职业生涯。任文学杂志《海燕》《野性时代》总编辑期间,发掘、培育新作家,曾协助吉本芭娜娜、角田光代、岛田雅彦等多位日本作家登上文坛。从出版社退休后,根本昌夫仍旧活跃于编辑圈。他长期在朝日文化中心开设小说写作班,催生数名获得重要文学奖项的新人作家,被称为“日本文坛伯乐”。
第一章 何谓小说? 一、小说不是“叙事” 散文和传闻也是小说 “‘小说’是什 么?” 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呢? 即使热爱小说胜过三餐,立志成为小说家,对小说的一切了如指掌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也觉得难以作答。就算是平常会看小说的人,或许也从来没想过小说的定义。 “不过,简而言之,小说就是‘叙事’吧?” “小说就是指虚构的故事 吧?” 真的是这样吗? 且让我们查查词典吧。 翻开日语词典,关于小说的释义有“透过作者的构思,描写人物、事件或人间社会,具有故事情节发展的散文体作品”(《岩波国语词典》)等说 法。 汉和词典(《角川新字源》)上记载,小说是“不足道也的议论”。也就是说,相对于君子以国家、政治为职志写下的文集称为“大说”,关于日常之事、传闻、幻想等的文章,定义为“小 说”。 第二种释义是,“民间故事、寓言、怪谈、随笔等的总 称”。 然后,第三种释义终于接近大家一般对“小说”抱持的印象——“根据作者的想象力构成散文的文学作品”。附带一提,“构思”的意思是思考如何组合主题与形式等各个要 素。 简而言之,看来把小说理解为“什么都可以”也无妨。包含散文(随笔)在内,发挥想象力的虚构故事也行,甚至连传闻好像也可以算在内。 就这层意思而言,写小说绝对不难。 小说,很自由。 所谓写小说,就是从内心的感受、想法、思绪、回忆之中,选出重要的事来表现。把重要的事写下来,传达给别人。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感受、诠释事物的方式都不一样。要把自己内在的事,传达给和自己感受、诠释方式不同的他人,是需要下功夫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呢?接下来请跟着本书一起进入探讨。 小说是内在的“非虚构” 山田咏美曾在和佐伯一麦对谈时,说“小说是内在的非虚构”。虽然采用虚构的形式,但是小说里一定含有“真实”的成分。关于这份真实的含义,小说可说是“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这个“真实”也可以置换成“哲学”或“科学”。虽说是哲学,其实并非艰深难懂的事,像“自己是谁”“人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类的疑问,相信不论是谁都曾经思考过。此外,或说科学也并不是指会出现什么公式。除了物理学、化学、数学这些自然科学之外,还有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及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这类具有逻辑性的学问也应把它视为一种科学。 小说既是哲学,也是科学。 小说容易被认为与哲学、科学无缘。不过,只要追溯小说的起源,就会了解小说其实原本是哲学,也是科学的事实。 大体而言,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欧洲讲求“遵从神的律法而活”,是个由基督教主导的社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转变成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然后在16世纪的时候,蒙田写下《随笔集》,问“我知道什么呢”,也就是“我知道何事(其实我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尝试“自我探求”。以伦理社会的说法而言,是一场从“观念论”转向“经验论”的巨大思潮。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超俗回到理性的变 革。 在17至19世纪间,理性的戏剧和小说诞生了。哲学开始和故事融合。故事从神话、传说或劝世文等这些和作者没什么关系的内容,演变成出自作者经验的“内在的非虚构”,也就是具备某一种“真实”的小说开始出现 了。 早在西洋的哲学和思想传来的明治时代以前,江户时代的小说作为一种科学,肩负着启蒙的功能。例如,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内容就含有启蒙经商之道的“社会科学”,还有曲亭马琴以八项道德名目塑造人物角色的《八犬传》,也可以说是包含了道德方面的“人文科 学”。 追本溯源来看,就能够了解小说不只是虚构的叙事,也是融合了故事和哲学的文体。 那么,为什么小说的作者要刻意把“我是谁”“人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人该如何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融入故事里 呢? 那是因为比起用直截了当的话语来回答,融入故事更能传进读者心 里。 好比说,与其直接听闻“人类需要爱”这句话,大家也都是读了小说后感到“啊,人果然需要爱啊,爱真的很重要”这样更能深植内心 吧。 另一种情形是,选择小说这种表现形式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虽然无法用语言完整地描述出来,但如果你想描写的“真实”是难以用笔墨形容、无意间的冲动、没有符合字眼的微妙感觉、漠然的视觉映像等情况,那就只能融入作品的字里行间或整体故事所营造出来的感觉 上。 我常听说有作家亲自出马挑战以自己的作品为考题的测验。“这个作者想说的是下列A至E中的何者?请选出最接近的答案”,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往往自认为“我想说的不在A至E当中”而无法作答,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这些作家大多表示:“如果我想说的事能归结在六十字或这样简短的话里,那打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小说’的形式了。” “故事”扮演了糖衣的角色,让人更愉悦、印象更深刻地服下名为“哲学”的药方,又或是“故事”本身已经加入了“哲学”的药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