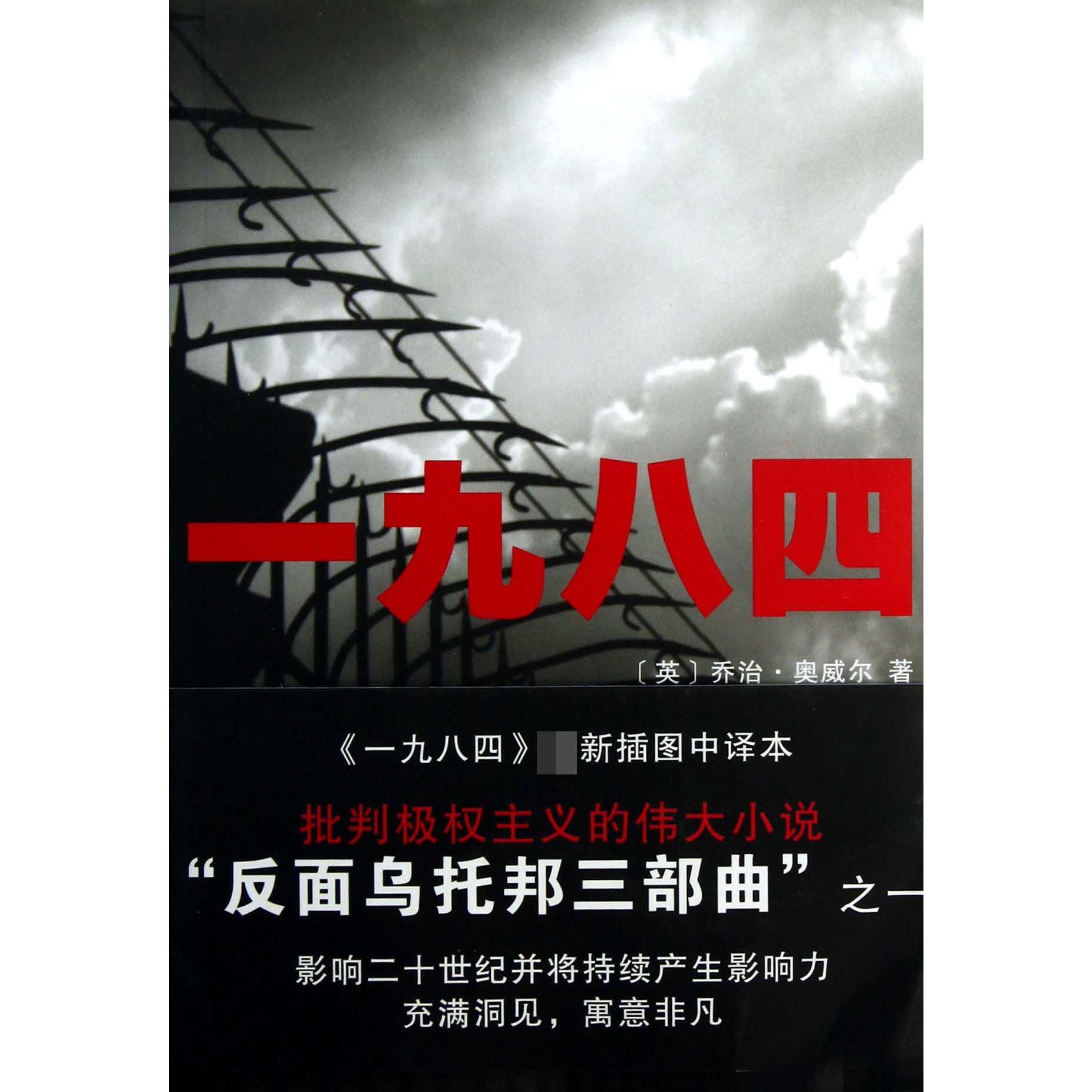
出版社: 花城
原售价: 26.00
折扣价: 19.50
折扣购买: 一九八四
ISBN: 9787536054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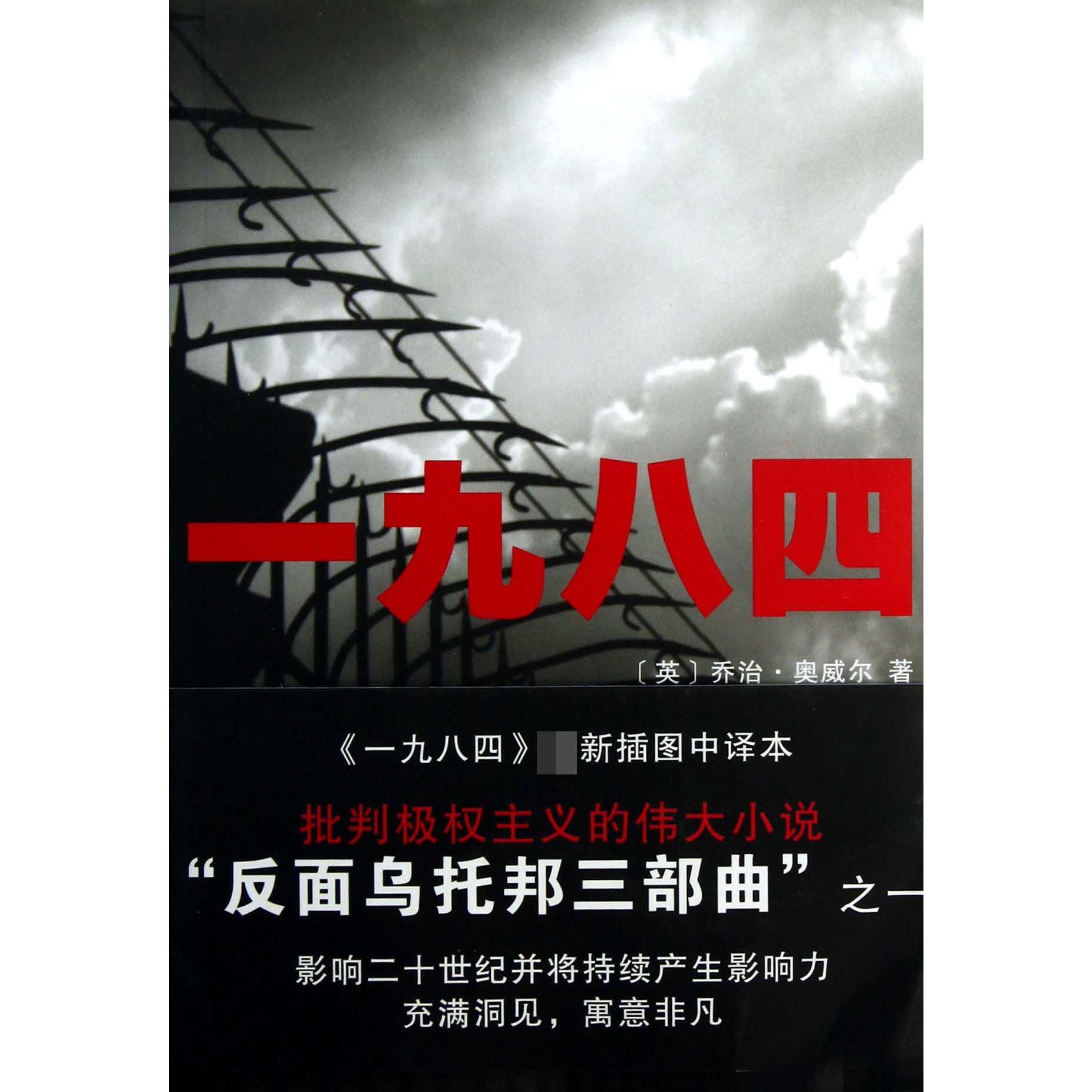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作家。1903年出生于英属印度,1907年举家迁回英国,进入著名的伊顿公学学习。后因经济原因无力深造,被迫远走缅甸,参加帝国警察部队。终因厌倦殖民行径、痴迷写作而辞去公职,辗转回到欧洲,流亡伦敦、巴黎等地。一边深刻体验下层民众生活,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并有多部作品出版。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为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而参战,不幸负伤。1939年,二战爆发,他积极参加反纳粹的活动。西班牙内战与二战的苦痛经历,让他对战争与和平、极权与民主、社会关怀与人类理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1945年,乔治·奥威尔出版了著名的小说《动物农场》。1949年,他的代表作《1984》问世,在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入选多国中学生必读书目,被翻译成62种文字,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1950年,乔治·奥威尔因肺病去世,年仅47岁。
如果那样模模糊糊的一件事也说得上是发生过,那么,它 就发生在今天上午,在部里。 快十一点的时候,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把椅子从自 己的办公位子拖到大厅中央,对着大电屏,准备参加两分钟仇 恨会。温斯顿刚在中间一排椅子上落座,有两个看着眼熟却从 未说过话的人意想不到地走了进来。其中那位姑娘常在走廊遇 见,他叫不出名字,只知道是小说司的。温斯顿有时见她双手 沾满机油,拿着扳手,没准是负责维修哪部小说写作机的机械 工。她大约二十七岁,样子很大胆,头发浓黑,脸上有雀斑, 动作矫捷,像运动员似的。一条猩红色丝质腰带——青少年反 性同盟的标志——在她的制服外缠了几圈,不松不紧,恰到好 处地突显了那苗条的曲线。温斯顿第一次见她就感觉不好,他 知道那是为什么:她竭力在周身营造出一种——与曲棍球场、 冷水浴、集体远足等相联系的——总之是思想纯正的气氛。几 乎所有的女人他都讨厌,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特别是年 轻女人,往往是党的最忠实的信徒,盲目相信宣传口号,甘心 充当包打听,到处刺探异端思想。这个女孩让他更加觉得危险。 一次,在走廊上,她忽地从侧面瞟了他一眼,那目光似乎穿透 了他的心,一时间让他充满了黑色恐怖。他甚至怀疑她是思想 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不太可能。但只要有她在跟前, 他就忐忑不安,既有敌意,也有恐惧。 另一位是男的,叫奥布赖恩,内党成员,担任要职,属于 高级领导层。他的职位如此之高,以至于温斯顿连他的工作性 质都弄不清。内党成员的一身黑色制服一出现,椅子周围立时 肃静下来。奥布赖恩高大魁梧,脖子很短,面容粗犷,显得诙 谐而严酷,虽然令人望而生畏,却有一种特别的风度。他轻轻 扶正鼻梁上的眼镜那个习惯动作,不知为什么总给人一种亲切 的感觉,似乎是文质彬彬的。这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如 果现在还有人这么想的话——那种十八世纪的贵族绅士掏出鼻 烟壶来待客时的做派。以往十来年,温斯顿见到奥布赖恩也不 过十多次。他深受奥布赖恩的吸引,不仅那拳击手般的体型和 斯文举止之间的反差使他颇为好奇,更因为他暗暗觉得——也 许不是觉得而是希望——奥布赖恩在政治上并不尽然是正统的。 那张脸上的某种神情仿佛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或许那神情并 不是一种非正统的征象,只是一种智慧的流露而已。不管怎样, 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能躲开电屏和他单独在一起,他是个 可以谈谈心的人。温斯顿从未作过哪怕些许努力去验证这种猜 测,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此刻,奥布赖恩瞧了下 手表,马上十一点了,看来他决定就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 恨会结束。他在温斯顿这一排坐了下来,与温斯顿相隔一两个 位子。中间坐着一位淡棕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 的办公位子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就坐在他们后排。 这时,大厅那头的大电屏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像一台大机 器运转起来缺少润滑油似的。这种响声让人不由得怒火中烧, 义愤填膺。仇恨会开始了。 按惯例,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德斯坦因的脸孔呈现在电 屏上。观众的嘘声此伏彼起。那个淡棕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发出 一声尖叫,含着恐惧和厌恶。戈德斯坦因是叛徒、变节者。他 很久以前曾是党的领导人(到底是多久以前,没人说得清),几 乎和老大哥地位相当,因参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又神 秘地潜逃,至今下落不明。两分钟仇恨会每天不同,但主要对 象总是戈德斯坦因。他是头号叛徒,最早玷污了党的纯洁的人。 之后发生的一切罪行——反党、叛国、颠覆活动、异端邪说、 离经叛道——无不源于他的教唆和煽动。如今,不知在什么地 方,他还活在人世并策划着阴谋;或许混迹海外,在其外国主 子的庇护之下;或许甚至就藏在大洋国内某个阴暗的角落—— 时不时地可以听到这类传言。 温斯顿一阵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德斯坦因的面孔,他都 有一种百感交集的痛苦。那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浓 密的白发,下巴上一撮山羊胡。这张脸显得很聪明,但不知为 什么又有一种天生的可鄙。鼻子细长,快到鼻尖处架着一副眼 镜,有点老态。他的面庞和嗓音都很像绵羊。此刻,电屏里的 戈德斯坦因又在恶毒攻击党的教导,那么夸大其词,那么蛮不 讲理,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却又似乎有点道理,让你警惕着, 觉得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很容易受骗上当。他辱骂老大哥,攻 击党的专政,主张马上和欧亚国讲和,鼓吹言论自由、新闻出 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说革命已经被 出卖了——这些话都讲得极快,用的全是大字眼,模仿着党的 演说家惯有的风范,甚至还用了不少新话词汇——说实在的, 比任何党员日常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为了防备有人对戈德斯 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产生怀疑,在他讲话的时候,电 屏里他脑袋后面是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在行进,一排又一排 强壮的兵士,亚细亚式的脸上毫无表情,那军靴踏地的响声构 成了戈德斯坦因嘶叫的背景。 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