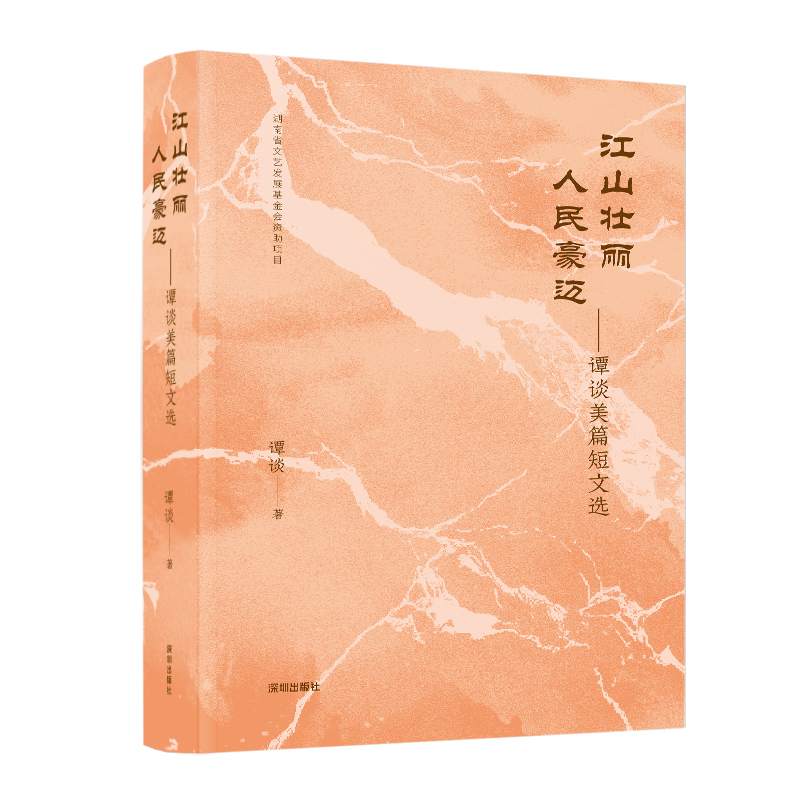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55.00
折扣价: 34.10
折扣购买: 江山壮丽 人民豪迈:谭谈美篇短文选
ISBN: 9787550739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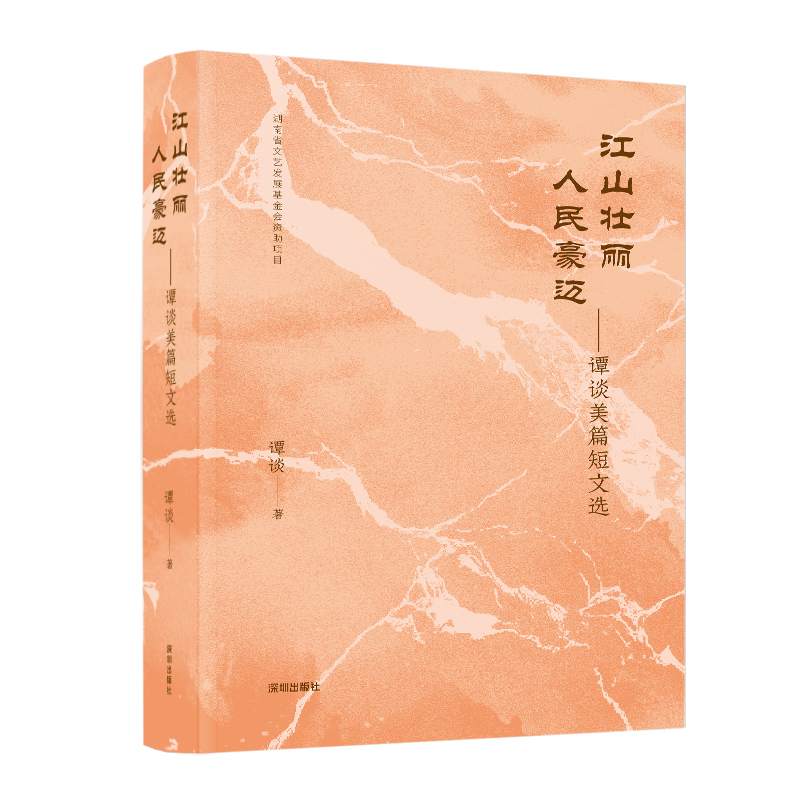
谭谈,1944年生,湖南涟源人。有600万字、数十种著作行世。包括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在内,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曾主持修建毛泽东文学院,创建作家爱心书屋,主编大型丛书“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先后当选中共第十三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五届、第六届候补委员、委员,中共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我的外婆路 年岁一年一年大了,童年离自己越来越远。然而,远 去的童年,在自己的心里却越来越清晰……许多童年的记 忆,时不时地浮现在自己眼前…… 我的童年,是在花山岭脚下那个小山村度过的。儿时, 我常常跟着妈妈,从屋子前面的石板路出发去外婆家。爬 上石岭尖,就看到岭下小溪边高耸着一座宝塔,那是七宝 冲的七宝塔。下了山,沿着山脚下一条小溪边的青石板路 往前走,就可以到达外婆家。青石板路面上的一块块青石, 被一代一代山里人的脚板踩踏得光滑光滑的。过了益寿亭, 过了花桥,就见到小溪进入了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一座古 朴的石桥。石桥两端,还有一对威武的石狮子呢!妈妈说, 这个地方叫温江。这是你爸爸的外婆家,你奶奶的娘家。 这条河呢,也叫温江。 水面到这里变宽了,水也更清了。更为奇妙的是,河 里的水,冬天是暖暖的,而夏天是冰凉的。那时候,我老 是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次,我又跟着妈妈到外婆家里去。快走到这里的 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离开了那条青石板大路,往一座小山上走去。 “妈妈,这是去哪里呀?不到外婆家里去了?” “你不是老问,这河里的水,为什么冬天滚热,夏天冰 冷吗?今天妈妈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你就晓得了。” 不大一会儿,我跟着妈妈,来到了一座长了好多竹子 的小山上。只见山上有一口不起眼的塘。塘里的水,清亮 清亮。一蓬一蓬的水草,在水中摆动。塘中心,有一处水 直往上翻滚,只见一层一层的水花,从这里四散开去。塘 岸边,有一个口子,清清的水往下流去,流出了一条溪。 塘里的水太深了,也太清了。深得、清得让我害怕。我紧 紧地抓着妈妈的手,不敢放松。 接着,妈妈又领着我来到离这口塘不远的一个山墈 边,我看到墈边有一个洞。洞里流出来一股好大好大的 水,也是那样清,那样净。妈妈要我伸手去摸摸那水。我 的手一触到水,冰浸冰浸。当时正是夏天,这水竟是这样 的凉…… 这时,妈妈告诉我:“这两股大泉,就是东温和西温。 这里的水,都流入山下面的河里。它们是这条河的主要源 头。现在,你晓得这条河里的水为什么冬天热、夏天冷了 吗?因为这是一条泉水河!” 过了温江桥,往前走一段,河岸边一架大筒车,在河 水的推动下,正不慌不忙地旋转。只见挂在筒车上的一个 一个竹筒筒,一到高处,就把筒里的水倒到了安在上面的一个木槽里。木槽里的水,又通过一节一节的竹管,流到 高处的水田里去了。眼下正是水稻扬花的时候,正需要水 去为谷粒灌浆壮籽啊…… 这是老天的恩赐啊!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大旱,禾苗枯死,饮水艰 难。天上的水星见了,忍不住掉下了两滴眼泪,变成了东 温和西温。两眼大泉流了出来,汇成了这条河。人们给了 它一个很贴切的名字:温江。 温江,这条泉水河,是别有一番情趣的。不宽的河床 里,终日河水饱满。盛夏,水清凉清凉的,跳下去洗个澡, 让你透身地舒服。严冬,河面上却是水汽腾腾,洗衣洗菜, 河水还微微热乎呢! 我站在筒车边,出神地看着它转动,看着上到高处的 一节节竹筒里泻出水来,看着竹筒里泻出的河水,通过 一根根竹管,流到高处的田里……每回,都是妈妈强拉 着我,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令我迷恋的地方,往前 走去。 儿时的外婆路啊,有太多的温暖记忆了。过了温江石 孔桥不远,小河就流进了涟水。它在这里消失了自己,壮 大了别人。 就在温江与涟水相汇的地方,有一座风雨桥。我们那 里的人,都叫这种桥为屋桥、花桥。称它为屋桥,是因为 桥上盖有瓦,是有屋顶的。说它是花桥,是因为桥上的廊柱屋檐,都是雕有花(画)的。这些乡间大路上的亭也罢, 桥也罢,都是民间爱心人士做的善事,为那些终日在外奔 波的路人提供一个歇歇脚的地方。这两江相汇的地方,就 有一座饱经历史风雨的屋桥,名叫新车桥。 走过新车桥,沿着一座青山往前走。紧靠着山脚,有 一个小水沟。清清的山泉水,在沟里流动。有一次,我看 到一只螃蟹在沟里缓缓地爬动,便弓下身子,伸出手去, 一把将螃蟹捉住。正要胜利地向妈妈报告,猛一下感到手 指钻心地痛,手指被螃蟹的大夹子似的钳子夹住了,不由 得“哇”的一声哭泣起来…… 妈妈赶忙帮我把夹住我手指的螃蟹取下来。“蠢宝!看 你以后还这样去乱逮螃蟹吗?逮螃蟹,要避开它前面那两个大夹子似的钳子,抓住它的背壳,这样,它的钳子才夹 不到你。” ………… 外婆家离我们家有三十里路。过了新车桥,就是乌鸡 坝。那也是一个令儿时的我迷恋的地方。后来长大了,住 到了都市,与省武警总队的一位司令员相识相交。一听这 位司令说,他是乌鸡坝的,顿觉十分亲切。我对他说:“那 你是我外婆路上的啊!” 常走外婆路的那个时候,我才五六岁。如今,已是近 八旬的老翁了。外婆路上的那些桥、那些亭,多半已消失 在历史的风尘里了。只有天地不老、山河不衰,东温、西 温的水长流,温江的水长流。近些年,当地政府在温江建 起了自来水厂,让这甜美的山泉水,进入了千家万户。几 年前,我老家的乡亲,就喝上了这八九里路外的东温、西 温的泉水……前年,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毁坏倒塌的七 宝塔,经村民们集资,重修复建,以崭新的姿容耸立在山 岭下、小溪边了。近日,又闻有关部门正在筹划整修我外 婆路上幸存的一座风雨桥—新车桥;而已消失在历史烟 尘里的洞冲花桥,也在筹划复建。前两天,主事者找我, 要我书写“洞冲花桥”四个字,我欣然应允……真是喜讯 连连啊! 前人留给我们的那些乡间大道上的亭也罢,桥也罢, 尽管它们今天没有了实用价值,可是,它们是一个个历史符号。它们的另一种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厚重,值 得今天的我们珍重啊! (2023年4月5日发布美篇,载2023年6月2日《娄底日报》) 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谭谈先生作品的一贯风格,本书也不例外,那些活蹦乱跳的文字,是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脉搏的跳动。杖朝之年的老者,仍不倦地行走在祖国大地上,他用最朴素的方法,最直白的表达,写下了鲜活的纪实短篇,从各个小侧面、小角度展现当下的大时代,记录人民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