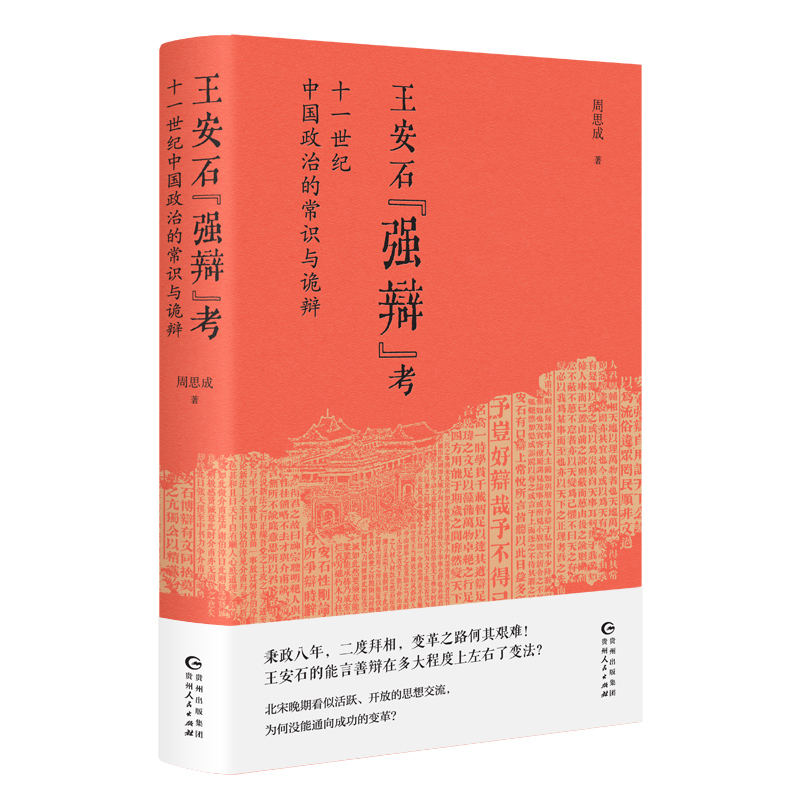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人民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王安石“强辩”考 : 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
ISBN: 9787221182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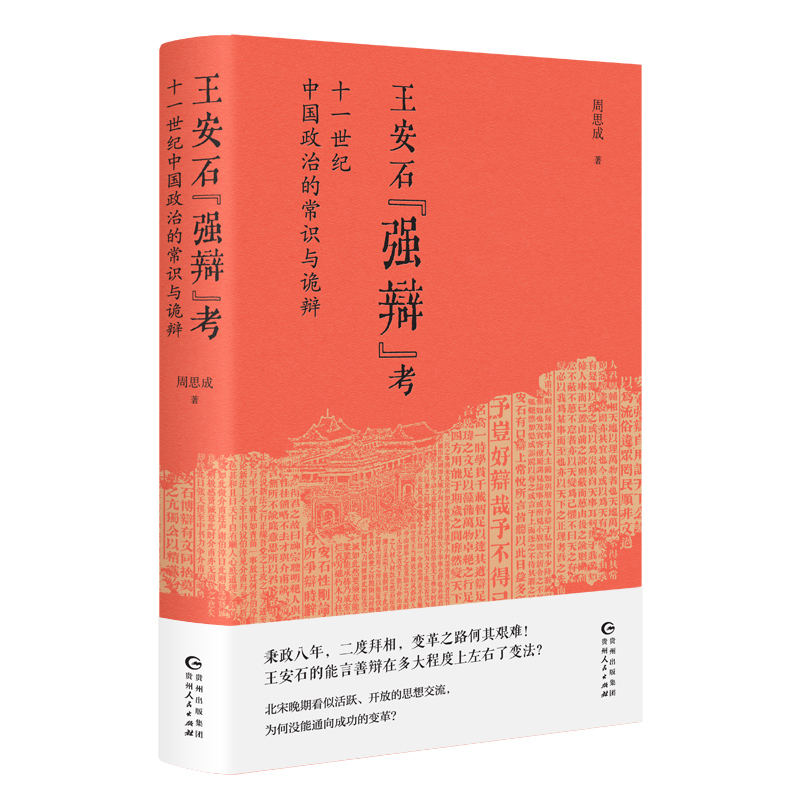
周思成,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 已出版作品《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另有译著多部。
序?言 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八年(1075),这7年,是两宋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喧嚣时代。 这个时代,以宋神宗从江宁府(今南京)召王安石入京,迅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推行“新法”而拉开帷幕,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退归江宁而奏响终止符。从熙宁二年开始,短短6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推出了均输、市易、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保马、将兵等十余项“新法”,期待以近似大规模政治动员和国家运动的方式,一举解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重压下的北宋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痼疾。 尽管变法派打出了“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的大旗,这一揽子新法仍在朝野引发了轩然大波:在风气日趋保守的朝堂之上,围绕每一项新法的酝酿制定出台,新法派和反对派都要吵得面红耳赤,势不两立,后人形容当时情景: 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邀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 的确,这种政治辩论,常常升级为恶语相向,直至闹到御前,皇帝只好亲自出面圆场:“相与论是非,何至是?”不止一人觉得,这类举动有失大臣和读书人的体面,有人抱怨:“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不论是贤名甚著的元老重臣,如富弼、欧阳修、范镇、文彦博、吕公著,还是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如苏辙、程颢、范纯仁、陈襄、刘挚,一旦与新法派议论不合,便以各种方式被摈斥出中央决策层,或投置闲散,或离京外任;同时,一些比较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就是日后被斥为“新进小人”的官员,很快出现在官僚体系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受到“新法”的牢笼和驱策,从京师到各路的官民,甚至隐隐感受到震动的“北虏”和“西贼”,纷纷或被动或主动,甚至是不计成本地调整各自的利益、行为和预期:一些新的机构和组织成立了,一些新的诱惑出现了,一些新的强制也降临了。过不了多久,从各地流出的钱帛、米粮,一袋袋,一车车,被来回调运或者干脆封桩入库,好应对那人人预感必将发生的更大事件,或者说,军事灾难…… 总之,在许多变法的亲历者看来,“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正是新法最直截、最迅速,也是为数不多的“见效”。随之而来的,是百年来祖宗以“仁恩厚德”培育成的理想世界的全面崩塌,所有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个盛世崩塌留下的可怖黑洞中: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然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二 在这一片喧嚣和纷乱之中,总有一些声音似乎格外响亮,还格外刺耳。 熙宁二年(1069)的某一天,众宰相和执政官员到政事堂聚议新法。传说,新提拔的参知政事王安石风头正盛,“下视庙堂如无人”。会议才开始不久,王安石和同列某官就一言不合,起了争执,旁人连忙打圆场。新参政从椅子上噌的一下站起来,怒视周遭诸人,最后,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狠话”: 君辈,坐不读书耳!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大哲学家张载之弟),也是为了反对新法,专程找上政事堂,与王安石理论。二人辩论良久,张戬援引儒经中的典故立论,王安石哂笑一声,语带讥讽地说: 安石却不会读书,贤(指张戬)却会读书!? 这句反话噎得张戬半天没有吭声。在王安石眼中,他的“良法美意”不受反对派待见,根本乃是由于这帮人不学无术,泥古不化。为此,他专门告诫神宗,“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无法理解新法带来的利益,所以“好为异论”,完全没必要理睬。 新法派中另一著名人物——章惇,在后变法时代成为宰相,力主“绍述”,大肆迫害元祐党人,在熙宁年间却不大受王安石看重。不过,此人的作风和王安石倒有几分神似。元祐初年,旧党得势,欲尽废新法,章惇操着一口带点福建口音的官话,竭力为新法辩护: 与同列议事,一不合意,则连声骂曰:“无见识!无见识!” 台谏官员就据此攻击他“纵肆猖狂”“无大臣体”,认为“此语,虽市井小人,有不轻发也,而惇以为常谈”。 “不读书”“无见识”“没学问”,类似的人身攻讦,在科举社会,在无不自诩博学鸿儒的官僚士大夫听来,大概要算最伤自尊的侮辱,在北宋政治中却也常见,台谏的弹章、贬降的制词,往往有之。至于气急败坏,在情绪失控的应激反应中,将政治的分歧,首先归结为竞争对手的智识、学问上的缺陷,而不是先论出身、阶级、信仰、种族、阴谋等,尤见得北宋的书生政治家有质朴可爱的一面,往坏了说就是迂腐、书呆子气。但是,这总归是努力让政治超越狭隘的情境、利益和权力关系,显示政治是可以(至少在一个相对平等、均质的文化精英圈子内部)通过公开、理性的论证或说服来推进的。这还涉及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政治哲学问题:智识的差别(intellectual distinction)能否转变为政治优势?或者说,最有“学问”、最会“读书”的人,最有资格治理国家吗? 尽管宋代政治制度缺少可供官僚士大夫内部进行政治辩论以弥合分歧、达成共识的理想机制,毕竟要承认,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示了政治行为者与制度环境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主义”。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熙宁四年(1071)的另一天,御史中丞杨绘(反新法派)提醒宋神宗,得多关心一下不愿附和新法而纷纷出走的元老重臣:“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杨绘还提议,及时选拔人才出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清要职务,以备顾问,储人才,因为“堂、陛相承,不可少”。在场一些官员纷纷表示赞同。 用房屋建筑来譬喻朝廷的人事结构,是一种惯常的做法。宋太宗就自夸对“内外官吏,皆量才任职,喻如匠者架屋,栋、梁、榱、桷,咸不可阙也”。王安石给一代大儒胡瑗写诗,期待他能得到重用:“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构架桷与榱。群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至此,一切都很正常。孰料就在此时,王安石站出来,以一种莫可名状的揶揄语气发表了一番议论: 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乃成室。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 这番驳斥,不仅堵住了杨绘之口,又顺势借“基”“础”“柱”“梁”这一连串譬喻,将旧党上上下下的元老、中坚和新锐通通嘲讽了一遍,可谓巧妙而极尽刻薄。这里,用的是类比,却不是在说理,而是一种人身攻击,诉诸情绪而非诉诸理性,效果不错——史书十分简略地记下了神宗皇帝的反应:“上笑。” 其实,王安石讥为粪壤、烂石、朽木之辈,许多原是他的故交和诤友。比如欧阳修,作为前辈,提携青年王安石不遗余力,既赠诗勉励:“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又上奏宋仁宗夸他“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后来,王安石也深情悼念欧阳修,以为“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到了庙堂的政治辩论中,逞一时口舌,老前辈就划入了烂石朽木。无怪乎后世传言,王安石曾对宋神宗污蔑欧阳修:“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也无怪乎后来杨时笑他“说多而屡变”,陈瓘骂他“取快而,乍强乍弱,况随其喜怒而论君子、小人哉”。王安石自己说过,“君子之所不至者三”,其一是“不失口于人”,这条箴诫,不妨原物奉还给荆公。 梁任公读罢宋史,不禁感慨:“政见自政见,人格自人格,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乃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出乎贤士大夫也。”从高度情绪化和道德化的攻讦,包括后来的“君子—小人”“朋党”等议论,又见得“泛道德主义”(pan moralism)在宋代仍有挥之不去的浓重暗影。它就像一个散发恶臭的巨大泥沼,任你如何爱惜羽毛,都无法全身而退。 三 本书的聚焦点,正是熙宁这个喧嚣时代的唇枪舌剑:理智的、诡辩的、冷静的、狂热的、善意的、险恶的……不为贪看热闹,而是有以下三点用意: 在两宋迄今的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众多史料中,对王安石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评价,就是说他性喜“强辩”:“强辩自用”(赵抃),“强辩背理”(《宋史》本传),“率以强辩胜同列”(邵博),“直是强辩,邈视一世”(朱熹)……“强辩”,这一北宋晚期以来王安石的恶谥,既是一种行为描述,又是一种负面评价,与真实世界中他本人的鲜明个性脱不了干系,又是元祐、绍兴等时期,新法反对者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对王安石和王安石集团的历史形象进行建构的一个关键元素。王安石等人的“强辩”,先在传统史学中被脸谱化、污名化,后在聚焦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史学中被边缘化,其实还有值得重新审视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一部面目稍显特殊的王安石传记。 广泛而激烈的政治辩论,在北宋历史上不止一二次,有日本学者喻为现代的“议会论战”。不过,熙宁时代尤其独特。朱熹说,比起汉唐,本朝胜在“议论”,“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无许多闲言语也”。所谓“熙丰”,主要指熙宁。到元丰年间,王安石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国是既定,诏狱屡兴,喧嚣不再,议论反而显得沉闷,甚至有些压抑,到了元祐初年,之前被压抑的议论又得到了一轮释放,可视为熙宁的延续。所以,叶适说得更准确:“本朝议论行事为三节:庆历也,熙宁也,元祐也。”此外,熙宁时代这些文字和口头的竞争,哪怕有时不过是争意气,犹如“村妪相谇”,也绝非清谈,而是对现实的政治进程有直接影响,乃至最终左右了新法的成败。比如,推行青苗法时,尽管阻力巨大,王安石独立朝堂: 在廷(指宰相曾公亮、陈升之,以及范镇、李常、吕公著等)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 所以,历史书写中的王安石形象,往往是一个靠着巧舌如簧取悦神宗,趁机窃取权力的奸佞: 安石有口辩,上常悦,所言皆听,以此日益多所变更。 当然,除了王安石的辩论性格和才能,皇帝的个性和施政作风,宋代政治决策中颇受研究者重视的“对”和“议”,皆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机会和场域,后文都会一一触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以“言语”或者说“辩”为核心的一个熙丰政治侧影。 最后,新世纪学者倾向于从政治而非社会经济角度来解读“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所谓政治,涵盖了人物、事件、制度等。本书更关注政治思想。当然,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具有多层次性。准确地说,本书关注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底色的政治观念,探索行动者习染的政治思想结构(某种意义上可称“常识”)如何影响了制度、政策及其他政治活动,也就是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互动。 据说,在新儒学的刺激下,宋代是先秦诸子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天命、人性、王权、君臣、正统、华夷、礼法,等等,历数千载之演进,至宋代已发展得十分成熟。在现实政治中,这些思想元素以或潜或显、或强或弱的方式影响着宋人的倾向和选择。不过,在熙宁时代的政治辩论中,这些形而上的“大观念”,本身还不算是主角。政治辩论带有明显的情境性、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如何从这类“表话语”中解析出“里话语”,即书生政治家对理想或现实的政治本质、政治关系以及统治技术的一般认知、预设、思维结构,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挑战。梁任公指出,研究政治思想史有三种路径:专题(如天下、国家、民本),年代(通贯、先秦、唐宋),宗派(如儒家—法家,道学—功利)。这里是截取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为横切面,观其汇聚,观其沉淀,观其激荡,观其向后变化之端倪,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北宋晚期看似思想活跃,交流频繁,却没有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 以上就是本书的蓝图,至于究竟实现了几分,就留待读者来批评吧。 正文选摘: 三、王安石:民意表达的悖论(节选自第七章) 根据王安石自己得到的信息反馈,“民”或者说百姓,是积极拥护青苗、免役、保甲这些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新法的。熙宁五年(1072)推行保甲养马法,让开封府界诸县的保甲组织自愿申请饲养官马(一年限额三千匹),承担马匹的维护和赔偿责任,换取一定的赋税减免。关于府界民众是否心甘情愿参与这项国家战备事业,神宗和王安石等宰执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安石曰:“此法已令诸县晓谕,百姓多以为便,有千五百户投状。” (吴)充曰:“大抵言情愿者,皆官吏驱迫。” 安石曰:“若官吏驱迫,即是诸县等第均敷。今但有千五百户投状,必非驱迫。” (文)彦博曰:“如体量和买草,河东和买亦名为和买,俱不免驱迫。” 上曰:“此即是均敷。均敷即自来驱迫,若非均敷,则非驱迫可知。” 彦博曰:“缘官吏或冀望升擢差遣,故上下相蒙,以强抑为情愿,不可不察也!” 安石曰:“必无此事!……” 王安石解释,府界民众中有一千五百户自愿申请,这个数字不多不少,既足以说明“百姓多以为便”,又显示官吏并没有为了完成指标而全面摊派。吴充、文彦博疑心底下的官吏为了绩效而隐瞒实情,强迫至少一部分民众“自愿”申请养马。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真有此事,那一套保证下情上达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发挥作用,受官吏欺压的民众可以自由去登闻鼓院、登闻检院或待漏院,直接投书伸冤: 若抑勒百姓,即百姓何缘不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经待漏出头,即陛下理无不知。打鼓进状,即陛下理无不见。陛下既知见,理无宽贷。官吏不知何苦须要抑勒百姓,为蒙蔽之事? 所以,经过这一串逆向的“滑坡论证”,并不存在什么“官吏驱迫”“上下相蒙”,民意的传达和反馈是直截、通畅、准确的,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屏蔽。面对别人质疑新法造成的种种弊病,王安石的态度一贯是,“民”完全清楚切身权益并能够通过合法渠道加以保护,他们的意见表达也是客观、真实的;只有反新法派怀有私心,妄图用谎言、造谣来破坏朝廷的善政: 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如此易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 有一些民意反馈,对新法特别有利,王安石更不会忽略。神宗指责农田水利法没有实效,王安石当即举出证据反驳:朝廷派程昉负责漳河淤田,拓宽了原武县(今河南原阳)等濒河地区的耕地面积,“百姓群至京师,经待漏院出头,谢朝廷差到程昉开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灾害!”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这群赞颂新法的民众,本是因为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集体上京告状。新法官员将他们拦截回来,处以杖责。民众只得谎称他们是去京城谢恩,新法官员顺势代写了一封《百姓谢淤田表》,加上两百多人的联名签字,派小吏直接送入登闻鼓院,“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可是,如果真的有小民击登闻鼓鸣冤,或去待漏院告状,反馈的是新法的负面消息,王安石如何回应呢?他脸色一变,开始断言愚民总是分不清哪些是局部的利益,哪些是整体的利益,哪些是短期的利益,哪些又是长远的利益,而政治就要算一笔功利主义的账: 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若欲人人皆悦,但有利无害,虽圣人不能如此;非特圣人,天地亦不能如此! 他仍旧诉诸“祁寒暑雨,民犹怨咨”那一套的辩解:好比“时雨之于民”,实际不可或缺,但必然妨碍“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更不可能保证“墙屋无浸漏之患”。这些无非是达成更高的“善”必须付出的代价,为政岂能“待人人情愿然后使之”? 王安石以为,愚民不仅搞不清真正的“大利”所在,他们的意见表达还会被居心不良之人操纵和利用,针对新法。若他们真的成功“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那也属于遭人误导挑唆。比如,府界周边有人反对保甲法,“以十数万愚民,而欲煽惑之者,非特一人而已”,不可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带头挑事的那一小撮头目的责任: 昨日闻,已捕获扇惑纠集人头首根勘,然至京者亦止有二十余人而已。以十七县十数万家,而被扇惑惊疑者才二十许人,不可谓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势驱率众人,而能令上下如一者。 本章开头讲的东明县百姓因为编排役法不公,集体上京告状,在王安石看来,也是同样的性质。不论此事是否真的是反新法派的阴谋,王安石不仅派人追究知县贾蕃的责任,还一再提醒神宗,要“以道(相当于前面说的理义)揆事”,不要动辄被舆论带偏: 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幸,则亦非所以为政。 民众只要感到新法损害一点自身利益,就敢于“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此风决不可长。皇帝必须“明示好恶赏罚,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则奸言浮说自不敢起,诡妄之计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当帖息”。说到这儿,王安石已经不在乎自己还把“经待漏出头、打鼓进状”说成新法之下民意的表达器和测量器。不仅如此,就在熙宁五年(1072),神宗和王安石还“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又设置京城“八厢探事人”逻察市井,很可能就是专门应对民意的集体性表达(如东明县事件)。 最终,民意的表达由正到反,在荆公的政治辩论中形成了一个矛盾的闭环,成了某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东西:任何明确感受自身利益受损的人都可以打鼓进状,任何实际上这样做了的人都不清楚真正的利益,是被煽惑的愚民……反对派固然无言以对,反馈和纠错的机制也成了空话。 ◎贡献一部面貌特殊的王安石传记:秉政八年,二度拜相,却落得一个“强辩”的恶谥。本书重新审视在现代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王安石政治个性的议题。 ◎聚焦北宋熙丰年代的政治氛围:变法派与反对派之间如何唇枪舌剑?当时的制度环境为政治辩论的展开提供了哪些机会和场域? ◎从思想观念的底色出发,观察北宋的改革及其结局:这些书生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跳出了传统思想的约束?看似活跃、开放的争鸣时代,为何没能实现成功的社会变革? ◎第二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豆瓣2021年度图书、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得主周思成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