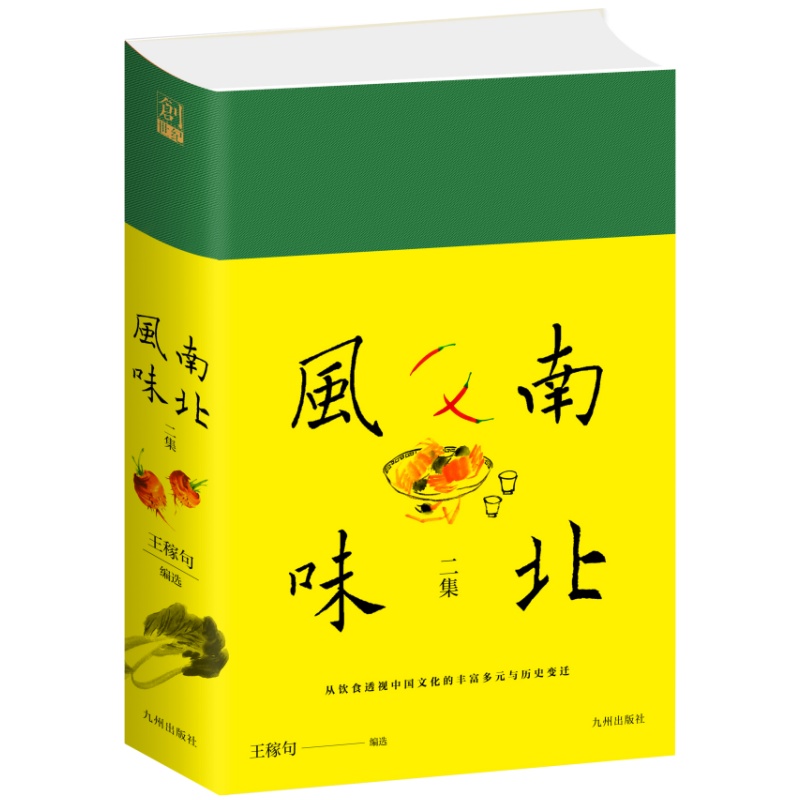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148.00
折扣价: 94.80
折扣购买: 南北风味二集
ISBN: 9787522530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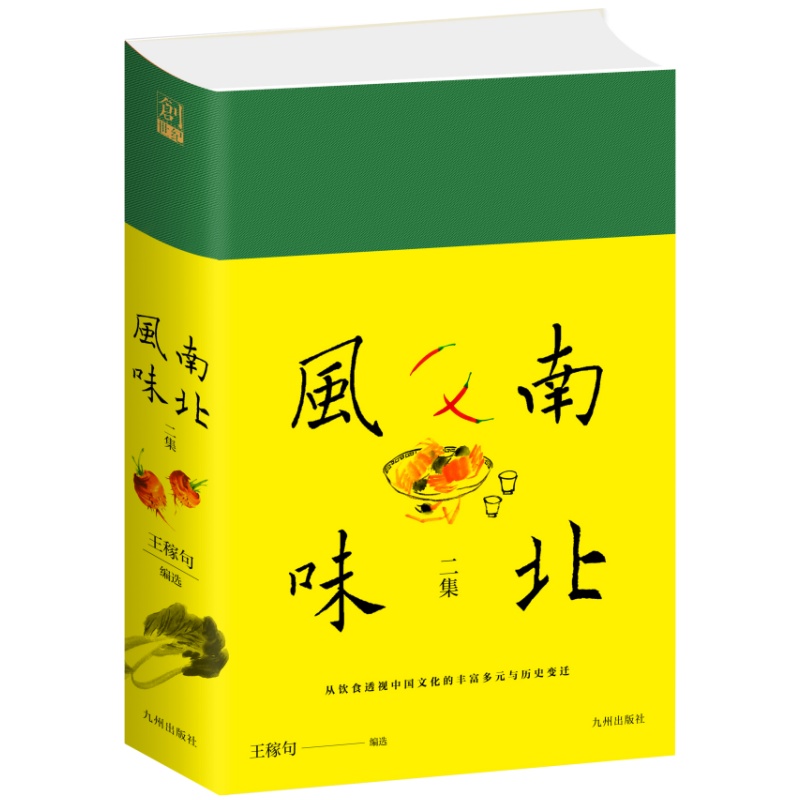
王稼句,苏州人,作家,学者,藏书家。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并在乡邦文献和文化整理中用功颇深。著述百余种,以文化随笔为多,有《谈书小笺》《秋水夜读》《看书琐记》《看书琐记二集》《看云小集》《听橹小集》《苏州山水》《姑苏食话》《吴门四家》《吴门烟花》等。
北平的“味儿” 纪果庵 若想以一个单词形容北平的话,那只有“味儿”一字。朋友们一提到北平,总是说:“北平有味儿。”或是说:“够味儿。”什么是“味儿”?我倒先要问你,我们吃砂锅鱼翅或是烤涮羊肉,大家抢着说:“有点味儿,不错!”这里味儿当什么讲?你明白了吃饭的所谓味儿,则生活的所谓味儿,亦复如是——不,北平的味儿,并非专像砂锅鱼翅,或是烤涮羊肉,倒有些像嚼橄榄,颇有回甘,又有些像吃惯了的香烟,无论何时都离不了。要把菜来比附,还是北平自己出产而天下人人爱吃的“黄芽菜”有点近似吧。因为它是真正人人可以享受的妙品。 闲园鞠农《一岁货声》把北平一年到头卖东西的叫卖声都记出来了,冬晚灯下阅读,好像又回到“胡同儿”里,围着火炉谈笑一般。我想,“货声”也要算北平的“味儿”代表之一,其特点是悠然而不忙,隽永而顿挫,绝不让人想到他家里有七八口人等他卖了钱吃饭等等,这就给人一种舒适。有时还要排成韵律,于幽默之中,寓广告之用,有时加上许多有声无义的字,大有一唱三叹的风致,例如早晨刚起床,就有卖杏仁茶的,其声曰:“杏仁——哎——茶哟。”那是很好的早点,在别处很少吃得到。卖粥的铺子都带卖油条,北平叫“油炸烩”,《一岁货声》记其叫卖声云:“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好大的个儿来,油炸的果咧。”(果,即烩之谐音)又云:“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里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一个大,即一文钱,亦即后来之一个铜板,而可抵今日之法币五角者也。北平之油条,要炸得脆松,故云云。但亦别有一种,是较软的,内城多不卖,而前门及宣武门一带有之,常与豆腐浆、杏仁茶合组一摊,应早市者也。区区一粥一油条,而有如许花样,这就是北平的“味儿”。照此例极多,再说两个,以为参考,卖冰激凌云:“你要喝,我就盛,解暑代凉冰振凌。”卖桃云:“玛瑙红的蜜桃来噎哎……块儿大,瓤儿就多,错认的蜜蜂儿去搭窝。”卖枣云:“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来哎,一个光板来。”又衬字多的如卖酪:“咿喓嗷……酪……喂。”卖砂锅:“咿?咦喓呕?砂锅哟?。”后者真是喷薄以出之,有点儿像言菊朋的戏词了。 观察北平的特点,总是在细微地方着眼才有发现。如吃饭,北平人是不愁没米没面的,有小米面、棒子面(即包芦)、黄米面,等等。小米面可以蒸“丝糕”,名字满好听,吃起来也不难,道地的北平人,可以在里面放了枣、赤糖,格外甜美;还有一种街头摊子,专用小米面作成厚约半寸的饼,放在锅边烘熟,上面是软的,下面有一层焦黄皮,很好吃。棒子面可以煮成粥,蒸为“窝头”,又可以切成小块,煮熟加一点青菜,好像我们吃汤面似的,北京叫“嘎嘎儿”。老实说,在北方,只有这些才是“人间味”,大米白面只有付之“天上”了。不过是像这些琐屑的食品,北平人也要弄出一个“谱儿”,使它格外适口些,好看些,从先我常看见贫苦的老太太到油盐店买调料及青菜(北平每胡同口皆有油盐店、肉店,而油盐店都带卖青菜,或带米面,不像南京之买小菜动辄奔走数里以外也),一个铜板,要香菜(即芫荽),要虾米皮,要油,要醋,要酱油都全了,回家用开水一冲,就是一碗极好的清汤,普通常叫这种汤为“神仙汤”,一个铜板而包罗万象,真是“神仙”!吃韭菜饺子必须佐以芥末,吃烤羊肉必有糖蒜,吃打卤面必须有羊肉卤,吃炸酱面之酱,必须是“天源”或“六必居”,抽烟要“豫壹”,买布则八大“祥”,烧酒须东路或涞水,老酒要绍陈,甚至死了人,杠房要哪一家,饭庄要哪一家,执事要全份半份,都要细细考虑,不然总会给人讪笑,这就是所谓“谱儿”,而我们在旁边的人看了,便觉得有味儿。 请放弃功利的观点,有闲的人在茶馆以一局围棋或象棋消磨五十岁以后的光阴,大约不算十分罪过吧。我觉得至少比年青有为而姘了七八个歌女什么的对人类有益处。若然,则北平是老年人好的颐养所在了。好唱的,可以入票房,或是带玩票的茶馆,从前像什刹一溜河沿的戏茶馆,坐半日才六至十个铜板,远处有水有山,有古刹,近处有垂杨有荷香有市声,饿了吃一套烧饼油条不过四大枚,老旗人给你说谭鑫培的佚史,说刘赶三的滑稽,说什刹海摆冰山的掌故。伙计有礼貌,不酸不大,说话可以叫人回味,“三爷,你早,沏壶香片吧?你再来段,我真爱听你那几口反调!”亲切,而不包含虚伪。养鸟或养虫鱼,北平也有不少行家,大清早一起先带鸟笼子到城根去遛遛,有未成名的伶人在喊嗓子,有空阔的野地,有高朗的晴空,鸽子成群的飞来,脆而悠长的哨子声划破了空气的沉寂,然后到茶馆吃杯茶,用热手巾揩把脸,假定世界不是非有航空母舰和轰炸机活不下去的话,像这样的生活还不是顶理想的境界吗? (《人间味》1943年第1卷第1期,署名果厂) 吃喝玩乐在南京 赵启民 南京是西沿长江,南障雨花台,东帡锺山,北倚幕府山,四临靠山傍水,所以南京城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曲折的。城既曲折,以致城内的街道也尽是歪七扭八。在这里雇车或指路,向来都是拿左右以替方向,莫说别处人乍来南京,就是南京人在没太阳的时候,也常会摸不清东西南北。可是你不要怕转向就不肯到南京来,南京不仅在沿革上是历当首都,而且在人生的享受上,这里也极吃喝玩乐的能事。 南京人的食物,向来以大米为主,普通人家购面的很少。面的用途,大约可以说仅限于做点心,如早点的烧饼油条,午点的包子,晚点的馄饨蛋糕,以及筵席上的饺子蒸卷等等。主食之外,此地喂养鸡鸭的很多,油鸡和板鸭虽很出名,但此地人吃它的时候却很少见,不过因为鸡鸭多,而且价格也和别的肉类相差无几,所以拿鸡鸭佐餐,并不像北方那样费难。尤其是鱼类,因为地靠长江,当然吃鱼也是非常方便。这里所缺的只是没有“炮”、“烤”、“涮”那样好吃的羊肉。羊在这里吃不着很多的草,长的个既不大,肉也总有股呕人的膻气。倒是猪肉,虽已卖到七块多钱一斤,但人们还是照样抢着买。除肉类以外,南京的豆腐确实比北京的豆腐好吃,嫩而不懈,细润得好像江南女子的皮肤。还有豆腐干切丝,此地叫做“干丝”,用肉或猪肝炒,佐以姜醋,这是在北方不易吃到的极好的下酒菜。更有一种黑灰色的豆腐干,叫臭豆腐干,街巷里常有小贩担着挑子,一头摆着碗箸,一头有个大锅在煮着满锅的臭豆腐干,许多人围在锅旁,人手一碗,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在没有吃过它的人,不要说吃,只那股气味,早已会使你闻香就马上加鞭了。水果在南京可以说是缺产,一切都是既劣且贵,惟独水产物,菱藕和荸荠等,既鲜嫩又硕大,花钱不多可以供你吃个饱。 茶在南京好像不若北京那么讲究,这里没有熏茶,只是整叶放在盖碗里生泡,按说龙井应当好,可是实际上它比不过北京,而南京人之讲究吃茶的精神,却比各地人都不在以下。这里的茶馆普称茶社,茶社差不多都带楼房,不但多而且地方也极宽广,由早至晚,那里面总是挤挤的,有闲的人,常会把整天的光阴抛掷在茶社里。等到红日已没,再由茶社转入浴堂,所以在南京有句俗语:“早起皮包水,晚间水包皮。”吃茶的精神,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茶而外,酒也是喝的一种。南京的酒,烧酒少黄酒多,黄酒也就是通称的花雕,每个大饭馆差不多都有自备的瓶酒,瓶上印着“老雕”、“二十年太雕”、“远年花雕”等字样,可是真正的老雕,怕早已被前喝者喝得精光了。好在如今的醉翁们其意多不在酒,而在借酒酬酢,互相为欢。就好像茶社里面坐的人,有些个确不为吃茶,他们的目的是在讲和彼此的误会,南京人名之曰“讲茶”,讲茶如果讲不和,常会以全武行来做结束。最近更有人利用茶社,作为操纵暗市秘密交易的场所,以致喝之一途,在南京已显然地起了一种畸形的变态。 南京好玩的地处很多,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燕子矶等都是名闻全国的。每当夏末,荷花盛开,划只小船荡在玄武湖碧绿镜平的水面上,那种天然的风味,确非燕城内海、昆明可比,置身于此,却也可使你忘尽了战乱一切。不过,普通人们除非因为天热无法,不得不来此一讨清凉,一般的兴趣却多集中在秦淮两岸。那里有迷魂醉性的场地,歌舞女以及野鸡们的住家,找不到一颗灵魂,然而却也能把你的灵魂销沉在她们的怀里。若说南京的玩,当要以此为最盛。 据说王玉蓉就是秦淮歌女出身,现在在上海演剧的曹懋麟,也是从前秦淮河畔的名歌女。的确,这地方盛产着歌舞名姝,而且名姝们也会圈拢着肯去成千动万花钱的大爷们。 一条小小的街衢,开设着女子服装店有八九家之多,那就在秦淮的沿岸。 可是你千万不要参观秦淮河,那不但是两岸垃圾,满河的秽水,而且相离几步远,彼处有个妇人在倒马桶,此处便有位老太婆在淘米,对岸还有个女孩在那里洗衣服。她们都是破落户,不是故意来做什么点缀,而那几只“更将炮艇作兰舟”故的破画舫,都已破得比破粮船还要难看些。不过,那里也不并非完全无趣,如果你不怕臭水熏你。…… 写南京的吃喝玩乐,我只能写到吃喝玩,乐,并不是没有,夫子曰:“乐在其中矣。”可惜我还不曾进到内里。 (《国民杂志》1942年第2卷第7期) 镇江干丝 敏 仲 朋友!你如果足迹多到些地方走走,在开眼界增阅历之外,还可以尝到不少各地方的隽妙食品。虽说现在上海等处已有许多土产公司开设,把各地著名土产食品,介绍给都市里的人,但终不及你自己到那地方吃到的来得真、善、美。 这期本刊上,我且来谈谈我路过镇江时,吃着的镇江干丝,事情是已在六年以前了,到如今六年以后,我还不曾忘却呢。 镇江干丝,为脍炙人口的镇江名产,仅仅这价值不贵的简单东西,能驰誉全国,可见自有它的真价值在了,这好比川菜的豆腐一味,妙绝人寰,一样的异曲同工,无独有偶。 那年我于役扬子,渡大江而北,每次必经过镇江。有一次,和老表何君从扬子回里,过江后并无耽搁,径乘人力车赴镇江车站,待车回常州。 那站,时候尚早,距车到时刻,还有一两小时之久,我们便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馆子里泡了壶茶,买了些小吃局和纸烟,消磨时光。表兄忽然想到吃干丝,他说:“镇江人常常吃茶佐以干丝,风味别具,我们不妨一试。”我自然赞同,当下叫堂倌弄一碗干丝来,不多一刻,热腾腾地拿上来了,用开洋、酱麻油同拌,干丝切得细而且长,细得真和一根丝一般,当然入味透极啦,在上海的镇江馆子里,哪里吃得到这般细的。 我们一会儿便吃完了,再来一碗,越吃越够味,接连吃了四碗,方才罢休。这种吃法,有人或者以为要说是饕餮之徒。其实那碗并不大,何况我们是路过镇江,难得吃着的东西,如何可以不吃一个畅,此番吃后,何时再到镇江一快朵颐,不能预定啊! 果然六年多了,还没有机会再到镇江去。今年我想到南京去一趟,回来的时节,假使能到镇江,勾留若干辰光,那末干丝妙味,决计不肯轻轻放过呢。 在上海到过镇扬帮馆子里去吃过这东西的朋友,你们要是有便到省里去时,千万再一试他们本地的,比较比较看,到底我是不是夸张地宣传! (《食品界》1934年第9期) 食在广州 秋 有一天,鲩鱼从佛山带了十二只弯弯曲曲的鸭脚来,同来六人,每人恰巧分到二只。我拿着鸭脚,仔细欣赏它底颜色及构造,很觉得诧异,因为我不曾看见过这么奇怪的鸭脚,我家乡的鸭脚也不是这个样子。我问鲩鱼:“叫什么名?”“鸭脚包!太乡里!”鲩鱼气恼恼地说。 我不作声了。我嚼着,细细斟酌它的滋味。我吃到一半,咬到一块肥猪肉,一股油膏便从牙缝里迸了出来。我赶忙从嘴巴里拿出来看,一团猪肉正端端地放在鸭脚包的中间,我忍不住又问了:“怎样做的?”“拿生鸭脚,中间塞些猪肉、鸭肝、鸭肾,再用鸭肠在外面捆起来,在火上煨到熟了为止。”当时我的脑中立刻浮现着“食在广州”。我不觉怔了一会儿,便笑了起来。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灵些,就是上海学生,还要屈在到上海求学的广州小子之下呢。广州人还肯用精细灵敏心思,对食物研究。广州人连什么都可以弄来吃,就是连狗、猫、老鼠都食。广州河南的贩卖狗市场,随时可以见到广州人蹲在棚前,撩起衣袖,放出豪爽的态度在大嚼呢!更奇怪,广州人还要捉些红红绿绿的仿佛蚯蚓加了毛脚的禾虫来磨烂,加下猪肉、鸡蛋、豆腐蒸了便食,像“油虫”般的龙虱,更是当做上味,平常的食物,给广州人一弄,便成咸、甜、酸、辣几十色菜。看起来,似乎肮脏得很,但那味儿却是好得无从形容的。天然出产的水果类,也令人一看到便流涎三尺,苏轼还要“日啖荔枝三百颗”呢! 广州的街道,哪有一条是没有“食”的铺子,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见到餐馆。广州满处都有茶楼、餐楼,我所以认为给广州人请食一餐饭是无上光荣的事。 广州人不但会弄食,而且会食。广州人的牙齿、舌头真利害,一嚼便是咸、甜、酸、辣几十味都可以来的,肚子更是像橡皮制的,“肚子饱,口不饱”,不知要吃到哪时才止呢! 广州人吃东西的姿势,更是好看,尤其是女人,指儿尖尖,嘴唇儿薄薄,拿起一只“鸡翅”,撕撕嚼嚼,不上几分钟,便只剩下几条骨头的了——更有些牙齿尖的连骨头也嚼了去。 有幸我走到“食的天堂”——广州来,虽然我多得了胃痛病,向腰包掏多几块钱叫佣人煲“凉茶”,但我觉得因为“食”而死,也是“诚心所愿”的事情了。 (《培道学生》1935年第3期) 麻婆豆腐 潜 鱼 住在京沪的人们,到川菜馆去吃川菜,总免不了要叫一份麻婆豆腐。大家都知道麻婆豆腐好,我想除了成都人和成都亲临过麻婆饭店的人外,都只顺口说着罢了,其实并不晓得麻婆豆腐好在哪里。成都的麻婆豆腐究竟怎样呢,现在我特地来介绍一下,以便研究食谱的参考。 在前清的时候,成都北门外有个很平常的小饭铺,专卖街上过客的餐饭,也没有某饭店的招牌。因为它那里的豆腐比别处特别弄得好,那时老板正是一个姓陈的老太婆,生得一脸麻子,所以客人就叫她做陈麻子婆,豆腐也就叫做麻婆豆腐。这就是麻婆豆腐的来源。 这个麻婆饭店,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招牌而且平常的饭店,一个陌生人到成都,恐怕还找不着,可见它的得名,完全是实际上的努力得来的,不像现在做生意的人,专凭宣传。铺子是一个二大间旧式平房,很古老的,没有油漆,家具也是新式的,有方桌四五张,长板凳二十多条,房子的右手一角,就是这个饭店的大厨房了。 至于它这里做生意,也和别处不同,它只卖一样菜——豆腐,另外就是饭了,这也表示它的专长所在。但是到此地来吃豆腐的人,都是特意来的,一些菜当然不满足,这时候它又有的通融办法,它也可以代做,不过仅仅要贴柴火作料费。 说麻婆豆腐的好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就是调味得好,弄得很烫。但是这两件事也容易,调味固然是成都酱油和辣子比京沪等处好,我想制法确大有关系,成都有两句俗话,说“千煮豆腐万煮鱼”,“豆腐只要吃得烫”,大致陈麻婆在这两句话上早已用了功夫,生意才这样红,不特京沪不及它,就是成都其他的饭店也不及它。庄子说,解牛的人,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神乎其技,不知道陈麻婆弄豆腐废了多少年的心血啊。 (《小日报》1937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