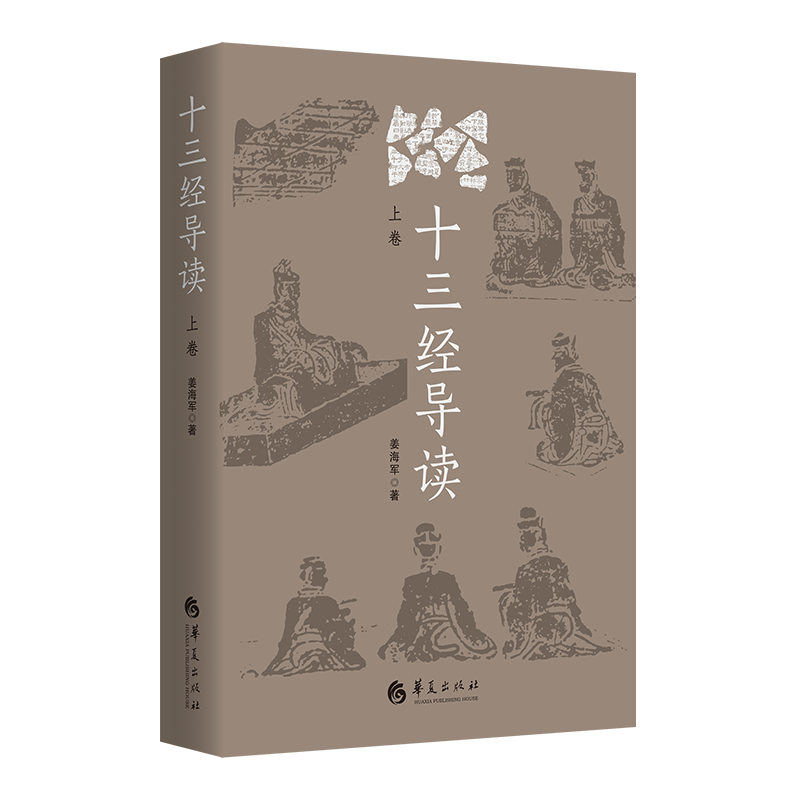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80.00
折扣价: 49.60
折扣购买: 十三经导读 下卷
ISBN: 9787522202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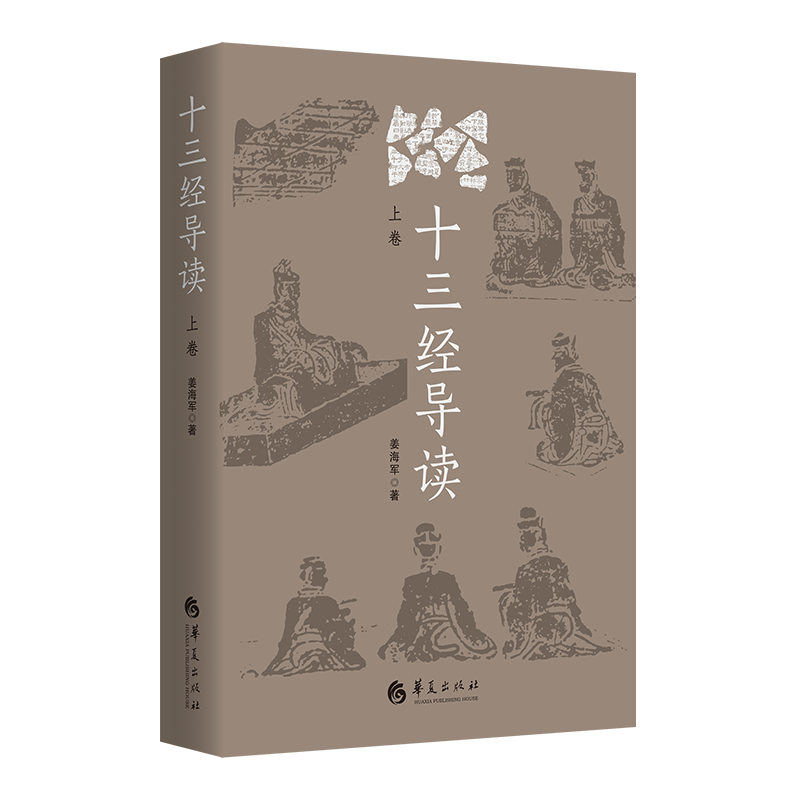
《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770),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
《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770),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的时候都用“弑”,这无疑有了强烈的情感色彩与礼教内涵。在今天流传的《春秋》文本中,记载臣子杀死君主的情况一共是二十六次①,这二十六次都无一例外地用“弑”而不用“杀”。孔子这样做无非想要表明,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以下犯上,是违背等级礼制与人伦道德的卑鄙行为。尽管《春秋》叙事非常简洁,但是它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外交、战争、会盟、祭祀、仪礼、灾异、王权争夺等等都有记载,所记载的史实经过后人研究认为基本可信。所以,它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经典依据。 二、《左传》的成书及其对《春秋》的解释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洁,所以从孔子时代开始,便有很多学者为它作传,其中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春秋》三传作为注解孔子《春秋》的著作,它们虽然都是传承孔子《春秋》大义,但是彼此侧重点有所不同。《左传》侧重《春秋》中的史实,其方法就是后人常说的“以事(史)解经”;而《公羊传》《穀梁传》侧重《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其方法就是后人常说的“以义解经”。 (一)《左传》的编撰成书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在中国古代一般都被认为是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是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最早记载左丘明作《左传》的是司马迁《史记》: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司马迁《史记》认为,孔子作完《春秋》之后,由于这部书对孔子时代以及之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多有褒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端,于是这部书一直没有书写在简帛上,而是由孔子弟子们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左丘明担心孔子弟子们每个人的观点、见解不同,从而造成对孔子《春秋》大义的误解,于是作《左传》① 关于左丘明的身世问题,学者一直都有争论。根据西汉孔安国注《论语》、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和孔子是同时代人,但他不是孔子弟子,因为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没有提到他。左丘明是一位博学多识、性格耿直、品德高尚的鲁国宫廷史官,孔子对他的人品很欣赏,曾经表扬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左丘明鄙视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徒,我孔丘也非常鄙视这样的人。 正因为如此,孔子将他引为同道中人,两个人应当是经常论学切磋,互有启发。根据汉宣 帝时期的博士严彭祖在其《严氏春秋》中引用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的说法:“孔子 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此 古本《孔子家语》是先秦书籍,并非王肃伪造的今本《孔子家语》)意思是说,孔子打算 作《春秋》,左丘明就曾与他一起坐车到了东周宫廷藏书处看书,回来后孔子作《春秋》、 左丘明为之作传,即《左传》。后来,孔子先作完了《春秋》,并且去世。左丘明继续为 《春秋》作传,作完《左传》之后,他在晚年将这部书传给了孔子弟子曾子的次子曾申。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明晚年双眼失明, 成了一名瞽史,但依旧撰写了《国语》一书,传于后世。 为《春秋》作注解,以免孔子《春秋》“微言大义”被人错解。之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也继承了《史记》的说法: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徴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 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班固在《史记》的基础上,对左丘明编纂《左传》做了更加系统的说明,并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并一起观看周代史书,孔子作了《春秋》,左丘明则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编纂了《左传》,以此来解释《春秋》。另外,像贾逵、郑玄、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大儒也都认为左丘明作《左传》,这在中国古代是最基本的观点。当然,从古代开始也有很多学者怀疑这个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说法,比如中唐啖助就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氏,是战国时人,而不是春秋的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钱穆则认为,《左传》 是吴起所作,等等。 关于《左传》的成书过程,以前一般都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一次成书说”,即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的。但后来学者研究发现,《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很多学者多次传播、多次修订、完善后,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清代姚鼐就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 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在姚鼐看来,《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左丘明只是完成了《左传》最初的原本,之后便将此书传给了曾子的儿子曾申,曾申又传给了吴起,吴起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了铎椒,铎椒传给了虞卿,虞卿传给了荀子。后来,秦博士张苍又从荀子那里继续传承了《左传》,并成为汉代《左传》学的宗师。姚鼐认为,在《左传》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它不断地被修订、完善(其中增删、修订以吴起为最多),经过多人、多次的增删、修补,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左传》文本。 不只是姚鼐否定司马迁“一次成书说”,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也持类似的观点,即“二次成书说”。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认为,《左传》成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左丘明根据春秋时期各国流传的史书编撰而成了《左氏春秋》,这部书还不是完全用来解释孔子《春秋》的;第二阶段,刘歆根据《春秋》的编年体例和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对《左传》进行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得《左传》内容与《春秋》经文彼此对应,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文本。这种观点对后来很多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康有为、胡念贻①、顾颉刚②、赵光贤③等人,他们都认为《左传》本是与《春秋》无关的史书,经过刘歆等人的增删、改造,最终成为解释《春秋》的著作。 以上几家的说法,都表明今本《左传》不是一次性成书,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刘逢禄、康有为等人认为刘歆伪造、篡改《左传》,有些言过其实,这可能与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有直接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姚鼐的说法比较公允,也更符合《左传》传承、成书的实情。其实,不只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有增删、修订,其他很多经典比如《周易》《老子》《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也都被不断地编辑、整理过,我们今天将出土的简帛古文与今本相对比,就会发现的确有增删、修改的部分。比如,先秦《周易》卦爻辞的内容与今本就有很大差别。老子《道德经》以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顺序正好相反,这就表明它经过了后代的修订。今天《左传》文本,也的确是经过增 删、修订后成书的。姚鼐之所以认为吴起增删最多,这和《左传》记载的历史史实以晋国为最多有直接的关系(《左传》全书共十九万多字,其中晋国最多,占四万多字)。我们即使从《左传》文本本身出发,也能找到一些增删、修订的例子。比如《左传》中鲁哀公十五年、十六年的历史,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就应当是后人所增加。 还有,《左传》与《春秋》经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有很多无传之经与无经之传。另外,还有一些“以义解经”的部分,如“君子曰”“五十凡”之类内容,并不是传文的有机的构成,更像是后人加入。所以,就今本《左传》而言,姚鼐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左传》最初的原本应是一次性成书,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纵观全文,全书在写作风格、用词规范、叙述内容等方面基本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后人篡改而成(即使有一些增删,但并不影响全书的整体性),这就说明《左传》原本肯定是左丘明最初一次性完成的,司马迁的说法没错。何况,作为史官的司马迁,能够接触到比后人更丰富的、更原始的史料,而且他离左丘明的时代更近,所以他对史实的把握应该比姚鼐、刘逢禄、康有为等人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史记》作为一部信史,它的记载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它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总之,就原本而言,《左传》是一次性成书,司马迁的说法可靠无误。但就最终的定本即今本而言,《左传》的确是多次修订、完善后成书,这种传承、完善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与创造。当然,《左传》在传承中所出现的增删、修订、丰富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是很常见的,况且这种修订并没有对《左传》所要表达的本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以事(史)解《春秋》 《左传》主要是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对《春秋》经文作最为详细的分析,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历史最重要的经典。这部书基本以《春秋》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内容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战争胜败、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之所以记载这么丰富,和左丘明是鲁国史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作为太史,他掌握着比别人更丰富、更珍贵的资料。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详细地编撰《左传》?这和他的创作目的有直接的关系,即他担心孔子弟子误解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所以为《春秋》这部书撰写更加丰富、翔实的历史事实来为孔子思想作佐证。比如《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只有九个字,但是《左传》却花了将近一千字进行解释: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元年》)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从郑庄公的出生说起,交代了母亲厌恶郑庄公,而偏爱他的弟弟公叔段,然后又分析了郑庄公如何听从母亲的要求分封了公叔段,而母亲却与公叔段合伙叛乱,想篡夺君位,另外又记载了郑庄公如何解决这次危机,以及他如何听取颍考叔的建议,最终实现母子和好如初,等等。 又如《春秋》宣公二年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对此《左传》作了详细的解释。春秋时期,晋灵公很小就做了国君,不仅荒于政事,而且非常任性、残忍。他经常在朝廷上拿弹弓打行人、大臣,以此取乐。有一次,因为他的厨子做的熊掌不合他的口味,一怒之下他就把厨子给杀了。面对晋灵公的荒唐行为,宰相赵盾曾多次劝谏,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掉赵盾。没有办法,赵盾只好选择逃避,到处躲避晋灵公的追杀。有一次晋灵公派一个叫麑的 大力士去暗杀赵盾。麑发现赵盾天还没亮,就已经穿好了朝服准备上朝,他被赵盾勤于政事、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动,认为杀了赵盾属于不义。但是他又认为,自己若不执行君主的刺杀命令,就是对君主不忠。麑认为这是两难选择,于是就选择了自杀,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晋灵公多次追杀赵盾,以至于赵盾同族的赵穿终于看不下去了,就派兵杀死了晋灵公,同时把赵盾召回到了朝廷,让他继续担任宰相,主持国家政务。对于这件事,晋国的史官董狐认为, 杀死晋灵公的真正凶手不是赵穿,而是赵盾,于是在史书上写下“赵盾弑其君”。赵盾看了以后,非常吃惊,说自己并没有杀害晋灵公,这样写是错误的。但董狐解释说:“你身为宰相,逃避晋灵公的追杀,但没有离开晋国,赵穿杀晋灵公的时候,你却袖手旁观。现在晋灵公被杀,你继续当宰相,却也没有惩办凶手赵穿,这弑君的罪名,不归于你归于谁呢?”赵盾听了,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任董狐记载。孔子听到这个事后,极力称赞董狐,说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即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史官,能够秉笔直书,不畏强权。不仅如此,孔子作《春秋》也继承了董狐的做法,他也写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且他直书晋灵公之名“夷皋”,这表明晋灵公该杀,这样就比董狐更加公正、客观了。由此可见,孔子“春秋笔法”可以说是对“董狐之笔”的继承和发展。 又如关于晋文公重耳的事迹,《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只有经文“晋侯夷吾卒”五个字,但《左传》中就对晋文公重耳出逃、周游列国、与各国君臣周旋、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晋国、登上君位等等,写得非常详细。 当然,《左传》并非对每一条经文都作非常细致的解释,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简洁的介绍,比如对《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解释为:“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又如《春秋》僖公十九年,记载有“梁亡”两个字,《左传》对此作了简明的解释: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左传》这段话翻译过来便是说,梁国灭亡了,《春秋》没有记载是谁灭了它,说明它是自取灭亡。起初,梁伯喜欢大兴土木工程,到处建筑城池,但是却不去居住,老百姓被折腾得非常疲惫,以至于难以承受,就谣传说:“某国就要入侵梁国了。”于是就有人乘机在国君的宫殿外面挖沟,说:“秦国将要攻打我们了。”老百姓都非常害怕,就逃跑了。秦国由此乘机占领了梁国。《左传》对“梁亡”的解释很简洁,但却非常形象,把老百姓的怨恨与统治者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左传》对《春秋》简洁的经文作了细致的解释,使得很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样一来,我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认识就会更加完整、全面,对它们的评价也会更加客观、公正。否则,根据《春秋》经文的片言只语,我们很难了解历史的真相,更难以下结论,甚至会做出错误的评判。比如《春秋》宣公二年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如果单凭这句话我们就会断定赵盾是乱臣贼子,杀了自己的国君。但借助《左传》详细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赵盾不是凶手,晋灵公也是该杀。 总之,《左传》对《春秋》中的军政大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做了细致的解说,成为我们了解《春秋》的经典之作。《左传》虽然只记载了上起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前后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历史文化,所以《左传》也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经典。对此如明人黄洪宪所言:“(《左传》)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国讣告策书,与夫公卿大夫氏族谱传;大而天文地理,微而梦卜谣谶。凡史狐、史克、史苏、史黯之所识,《梼杌》《纪年》《郑书》《晋乘》之所载,靡不网罗摭拾,总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① 就是说,《左传》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人文、社会、经济、礼仪习俗等各方面都做了记载,成为我们了解上古三代尤其是春秋时期最重的经典依据。清人崔述也说道:“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后,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后一大功臣也。”② 离开了《左传》,我们对先秦很多历史史实都无从了解。不能不说,《左传》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起源、先秦历史最重要的经典依据。 《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这部书与流传于世的《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一样,都是解释孔子《春秋》的,合称为《春秋》三传。 一、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笔法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宫廷史书,后来经过孔子的删改、修订,同时也吸收春秋各国历史,编成了新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融入了孔子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编纂思想,所以后世把《春秋》看成是儒家经典之一,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依据。 《春秋》这部书非常有特色,那就是“简而有法”,即非常简洁,但是有自己的叙事规则,史称“《春秋》笔法”,或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对中国古代的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作《春秋》 孔子为什么要编撰《春秋》呢?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捕捉到了一只独角兽,不知道是什么,就把它给杀了。孔子知道后,就去看,认出了这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麒麟。麒麟在上古时期一直被视为祥瑞(吉祥之物),只有在盛世才出现。而麒麟出现在春秋乱世,这并不说明当时就是盛世,反而表明盛世很难出现了。 孔子由此非常感慨,认为自己所向往的周代礼乐文明很难实现了。于是他就以鲁国的宫廷史书为基础,吸收各国历史,编撰了《春秋》这部书,融入了自己所信仰的周代仁义礼乐之精神。所以这部书后来也被称为“麟经”,或“麟史”。 《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为止”,一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使用的是鲁国的纪年,主要记载了鲁国的历史,同时也有当时春秋各国的历史,所以《春秋》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中国通史。由于孔子《春秋》所记载的时间跨度与当时社会政治发展基本吻合,所以历史学家用“春秋”来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名称。后来为了历史叙事方便,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开始于周平王东迁那一年(前770),截止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 孔子编撰《春秋》的目的,就是以周代礼乐制度为价值判断依据,通过历史叙述的形式(即采用蕴含“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褒贬的形式,对春秋人物与事件进行评价,看人物的言语、行为是否合乎周礼,如果是合礼的,就是对的、善的;不合礼的,就是错的、恶的),让人们从《春秋》记载中,看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此来规范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君臣的行为规范,从而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春秋》笔法 孔子《春秋》一书,虽然记载了与鲁国十二位国君相关的、长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全文最初只有一万八千多个字(现在的版本是一万六千多个字),行文非常简洁。如《春秋》记载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子益师卒”,等等。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如《春秋》隐公八年载“螟”,以至于我们都无法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螟虫灾害,更不知道螟虫灾害的规模有多大,朝廷是怎么处理的,最后结果怎么样,等等。 其实,孔子《春秋》正是通过这些简洁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即我们常说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它是指孔子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孔子首创,而是孔子对以往历史叙事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字定褒贬。比如描述一个人去世,其等级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称死。又比如周代统治阶层一般分为四个等级:公、侯、伯、子男(子男为一个等级)。在孔子时代,这些称谓开始变得比较混乱。但孔子在《春秋》一书中却对它们作了明确的区分,即宋一定称为公,齐一定称为侯,郑一定称为伯,楚称为子,许称为男,等等。又比如春秋时别的史书,一般不分上下等级,只要是杀人都用“杀”,《国语·周语上》“鲁人杀懿公”,《国语·晋语》“武公伐翼,杀哀侯”,“晋人杀怀公”;《竹书纪年》“(周)携王为晋文公所杀”,“郑杀其君某”,“(越王)不寿立十年见杀”;《左传》“自其厩射而杀之”,“郑人杀立髡顽”,等等。以上这几个例子都是臣子杀掉君主,在用词上都用的是“杀”。在孔子看来,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这是违背礼制、伦理的事情,非常大逆不道,于是他在《春秋》一书中,记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