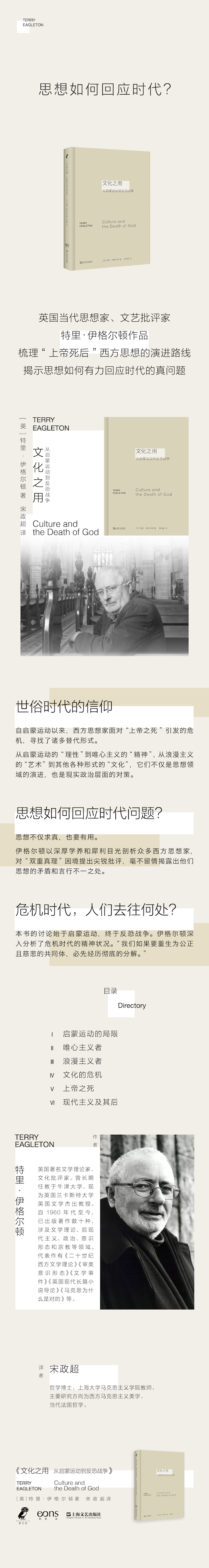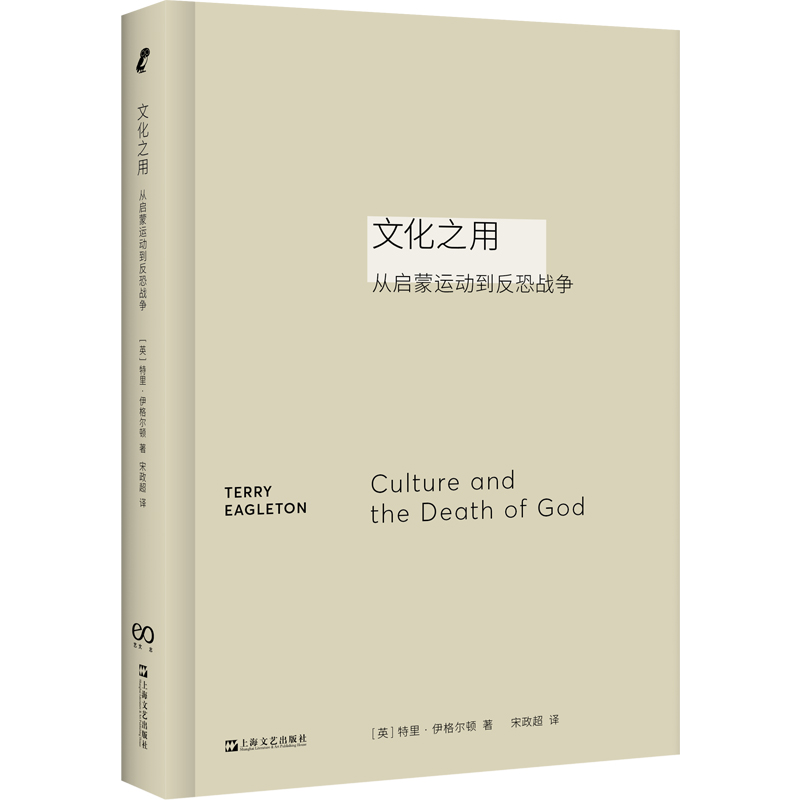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62.00
折扣价: 39.70
折扣购买: 文化之用:从启蒙运动到反恐战争
ISBN: 9787532186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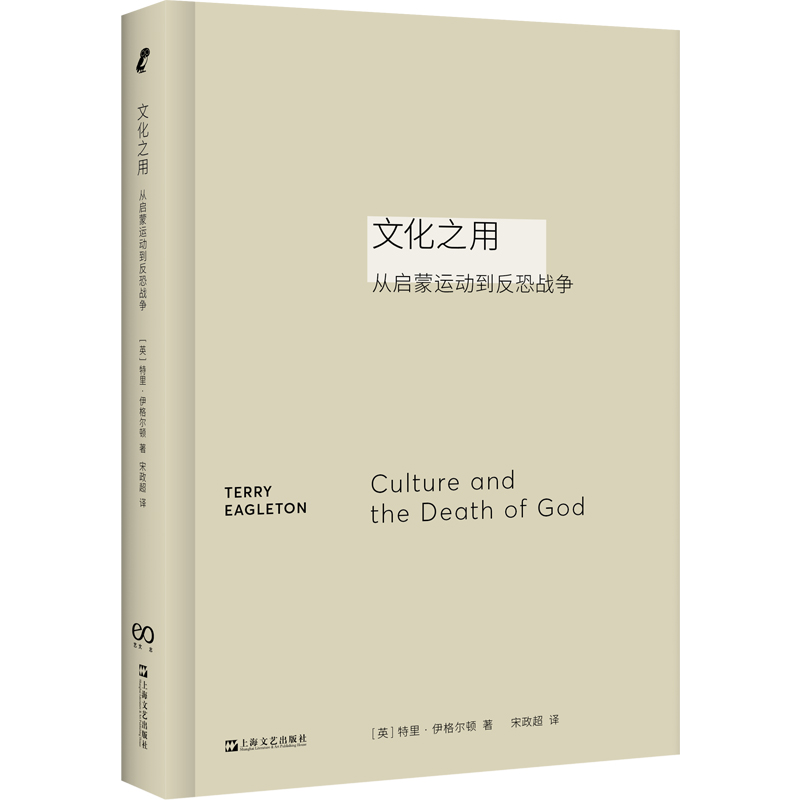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自1960年代至今,已出版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领域。代表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事件》《英国现代长篇小说导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 译者 宋政超,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法国哲学。
启蒙运动或许被困于信仰问题之中,但却并非是特别反宗教的。恩斯特?卡西尔写道:“我们很难讲启蒙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无宗教的或者抵触宗教的时代……它的根本目的(特 别是德国启蒙运动)并非瓦解宗教而是瓦解它‘超验的’正当性及其基础。”我们应该还记得“无神论”一词直到16世纪才出现在现代欧洲的语汇之中,并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质疑是否真正站得住脚。正如马尔科姆?布尔挖苦的那样:“无神论一边到处被人抨击,一边又被认定并不存在。” 普遍性的信仰缺失的确紧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但后者并非前者的主要原因。这种怀疑论的基础取决于社会条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无信仰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具体表现于每个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信仰坚定与否,而非大主教或者好战的世俗科学家们争辩的内容。 大多数理性(Reason)的狂热信徒依然保持着某种宗教信仰。牛顿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是基督徒,洛克、夏夫兹伯里、伏尔泰、廷德尔、托兰德、潘恩和杰弗逊是自然神论者(Deists)。苏格兰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既是反无神论的也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卢梭是有神论者。 知识无法触及信仰的对象,尤其在休谟看来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它是习惯和风俗的产物。同样的,道德也只是一套人类的发明,是没有形而上学基础的。 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攻击实质上是政治上的而非神学上的。总的来说,运动并非要用自然取代超自然,而是将一个残暴、愚昧的信仰替换成一个理智、文明的信仰。让这群作为新兴中产阶级代表的学者最为反感的是神权与王权卑鄙地结合在一起,借助教会的力量神化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政治制度。 约翰?洛克的学说认为心灵本身最初是一块白板,这一学说可以用来驱逐原罪的幽灵,因此反对人性先天的堕落而乐观地相信社会塑造的力量能够使人变得有德行。基督徒眼中的原罪在自然神论者看来只是过失罢了。 孔多塞宣扬普选、妇女平权、非暴力政治改革、所有人平等接受教育、言论自由、福利国家、殖民地解放、宗教宽容以及推翻专制独裁的益处,他也相信人类的无限完善。他一边描绘自己关于人类乌托邦的伟大构想一边从实际创建这个乌托邦的雅各宾党人那里逃亡,这称得上是思想史上难得的讽刺。 信奉牛顿学说的人在宫廷形成了一种贵族文化。明显讽刺的是,他们关于宇宙的力学理论竟然也能被用来树立精神上的权威。用牛顿的话来说,如果物质是“麻木不仁的”,只有神圣的意志才能使其开始运动。精神力量居高临下地规定着自然界正如国王和独裁者治理自己的国家。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牛顿都是他们国家旧有教会的拥护者,并且很大程度上也是支持君主统治的。 可问题在于,平民普遍被认为对理性是无动于衷的。像潘恩和戈德温这样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坚持大众启蒙的可能性,但他们那些更为保守的同事明显缺乏这个信念,相应地他们中的有些人接受被称作“双重真理(double truth)” 的论点。根据这个学说,那些受过教育的怀疑主义者必须学着不去动摇平民的迷信行为。由于对其可能引发政治动荡的 恐惧,它必须与平民大众相隔绝。 理性被假定为具有普适性,但甚至无法在一个单一国家内使自己普遍化。 我们或许敬畏其权威,但我们很难去爱它。理性无法让我们感觉到欣喜若狂的满足感,融入集体的感觉,无法拭去悲伤者的泪水。 你可以将宗教理性化,就像费希特的某些更为大胆的著作,或者将它完全从理性中驱除,就像各种信仰主义一样;但是前者无法满足大众,后者无法满足精英阶层。 对从赫尔德到荷尔德林这一系思想家来说,理性主义有漂白这个世界的内在价值的危险。问题就是如何恢复那个价值又不用过多借助于理性主义正起劲破坏的宗教概念。 权力,为了发挥效力,就必须将自身镌刻进感觉之中。 正如知识对启蒙运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的工具,那么神话也可以被如此看待。大体上,两种模式都排斥知识与作为批评条件的权力的割裂。于是启蒙运动“复归到它从未能成功摆脱的神话中去”。商品拜物教就是这样一种原始巫术。它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在理性时代的清醒头脑中能够存活下来的无数方式之一。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第一句话就宣称这本书不是为普通大众撰写的,这则警告对于哪怕读了一页的人来说都是多余的。这就是某些思想家的命运,他们的著作试图以内容吸引普通民众但是以形式吓退了这些人。 在一个既不习惯自由也不习惯平等的社会秩序中,美学构建了一块自由和平等的个体的飞地(enclave),一个微型的公共领域。它是居于顽固的现实的中心的,被遮蔽的乌托邦。这个幻象有多荒唐就有多鲁莽。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政治团结依赖于像审美判断一样率性而虚弱的能力之上,我们的处境的确是可悲的。 艺术已至之处,人类亦将到达。借助于政治改革,我们最终也能够以自身为目标而蓬勃发展,而不是为了任何确定的目标。审美的理性是反工具论的,将自我从交换价值和实用功能的范围内拉回来。审美的反实用性质因此成为它自身的政见。 众所周知马克思将宗教视作人民的精神鸦片,同时还是牧师洒向资产阶级腐败良心的圣水。而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则是他还将之视作这个失去了心脏的世界的心脏。 宗教懂得如何吸引大众,而德国哲学不懂。 民族主义是作为总体性的文化概念的主要来源——作为个人或者族群的完整生活模式。然而同时,它也促进了派系性的文化理念。这是种极为罕见的结合。对席勒而言,如我们所见,文化和派系偏见是世仇。对马修?阿诺德来说亦如是,他的观点在我们之后讨论的话题中会提到。民族主义,相比之下,表明了立场,但是以文化之名。民族生活方式可以构建一个共同体,但它也是残忍异见的起源。 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时下这个角色是被银行和跨国公司继承了。 浪漫主义对分析性思想的厌恶在这个运动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光明就在我心中,”雅可比辩称,“然而一旦我试图将其置于我的理智之下,它就消失无踪了。”曾努力拜读其作品的人将会非常明确地理解他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某些早期哲学家曾经梦想的大众神话最终以电影院、电视机、广告和大众出版的形式实现了。 阿诺德公开承认自己是个俗气的人或者中产阶级的成员;然而由于他也是那群唯利是图、心智粗俗的群体成员中那个持不同意见的,好像可以从外部对他所属的生活方式作出批判。对自身信念的玩味的疏离正是文化人的一个标志;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因为“雅各宾主义的两个突出标志——它的凶猛以及对抽象系统的沉迷,文化是这两者永恒的对手”。 现代主义将上帝之死体验为一种创伤,一个公开侮辱,既是痛苦的来源还是庆祝的理由,而后现代主义则完全没有这种体验。在其世界中心没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但在卡夫卡、贝克特或者甚至菲利普?拉金的中心都存在。 在某些后现代文化伪造的精神性中也有着超常的痕迹。这是人们在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社会期待的一种外刚内柔的折价的宗教信仰。一种含义混乱的神秘是那些头脑冷静的社会所能希冀的唯一信仰,恰如明显的诙谐是唯一能让没有幽默感的人感觉舒适的喜剧。 对现代主义来说,神的荣光让位给审美的灵光,而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艺术又将后者驱逐。唯一苟延残喘的灵光就是商品或者名流,这些现象并非总是轻易被辨别出来。 鉴于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其后工业化时代,是一种本质上无宗教信仰的社会秩序。对其运行而言,过多的信仰既无必要也不值得。信仰是潜在有争议的事务,既无益于贸易也无益于政治稳定。对商业而言它们也是多余的。创立制度时所需的这些热诚的意识形态修辞随着制度的展开而消退。只要其公民投入工作、承担赋税并且不去袭警,他们可以相信随便什么他们乐意相信的。就好像意识形态不再需要通过人类意识。 经济或许是讨厌的无神论者,但是为其保驾护航的国家却仍然感觉到需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信徒。当然,不必非得是宗教信徒,而是赞同某些无法仅仅从赤字规模或者失业统计中得到的不朽的道德或者政治真理。 西方资本主义成功出产的并非仅只世俗主义,还有原教旨主义,这是辩证法最为值得称道的壮举。 理性只有在植根于自身之外时才能真正合理。它必须在理性之外找寻到自己的归依,这不是说要在对其有敌意之处找寻。任何纯粹以理念的术语把握自身,其后在与感官世界相关的不那么空想的路径中摸索的理性形式,自开端就是虚弱的。 现在正是某些左派,而非右派,指望着对政治的宗教“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精神空虚的反应,但也是因为在宗教和信仰、希望、正义、社区、解放等等这些世俗概念之间确实有着重要的紧密关系。很多杰出的左派思想家,从巴迪欧、阿甘本以及德布雷到德里达、哈贝马斯以及齐泽克,因此转向了神学问题,使他们的某些追随者感到委屈或困惑。 如果宗教信仰从那个为了社会秩序的存而必须向其供应一系列基本原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它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目标是作为所有这些政治学说的批判者。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过剩或许证明了它的救赎。 如果特里?伊格尔顿不存在,就有必要创造一个他。 ——西蒙?克里切利(《哲学家死亡录》作者) 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变化的巡回调查。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这部丰富、复杂的作品中。伊格尔顿巧妙地探讨了理性、宗教、文化、神话、艺术、悲剧和现代荒诞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干练的机智和挑衅性的诙谐表达出来。现在,西方正与复兴的伊斯兰教发生碰撞,对其而言,上帝非常活跃,伊格尔顿的见解特别及时。 ——《科克思书评》(Kirkus Reviews)。 伊格尔顿对宗教的持续力量做出了丰富而令人信服的描述。随意翻开这本书,你会在一页纸上看到比一打冗长的哲学社会学论文中更多引人深思的论点。现代思想中的大多数关键转折点都得到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范围广泛,思想激昂。 ——《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摆脱上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格尔顿对过去三个世纪的哲学和文化趋势进行了简明扼要、引人入胜的概述。—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特里?伊格尔顿以他法医般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机智考察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批判性思想寻找上帝替代品的历程。……他的知识深度让人着迷。 ——《论坛报》(Tribune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