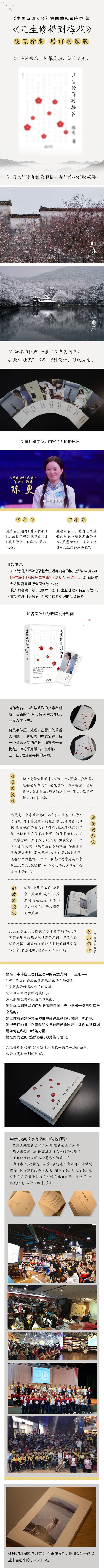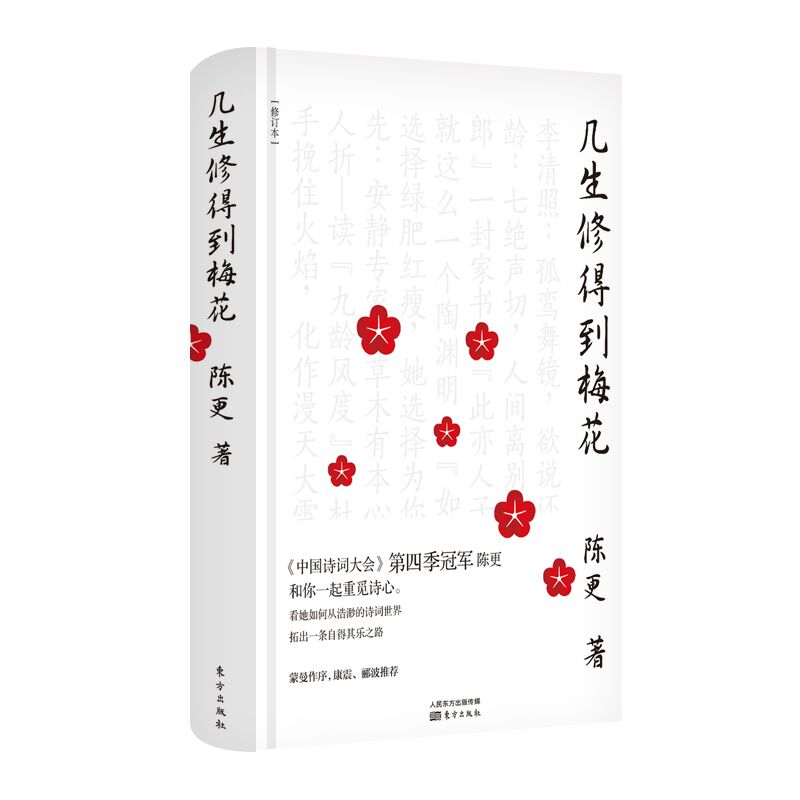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几生修得到梅花(修订本)(精)
ISBN: 9787520709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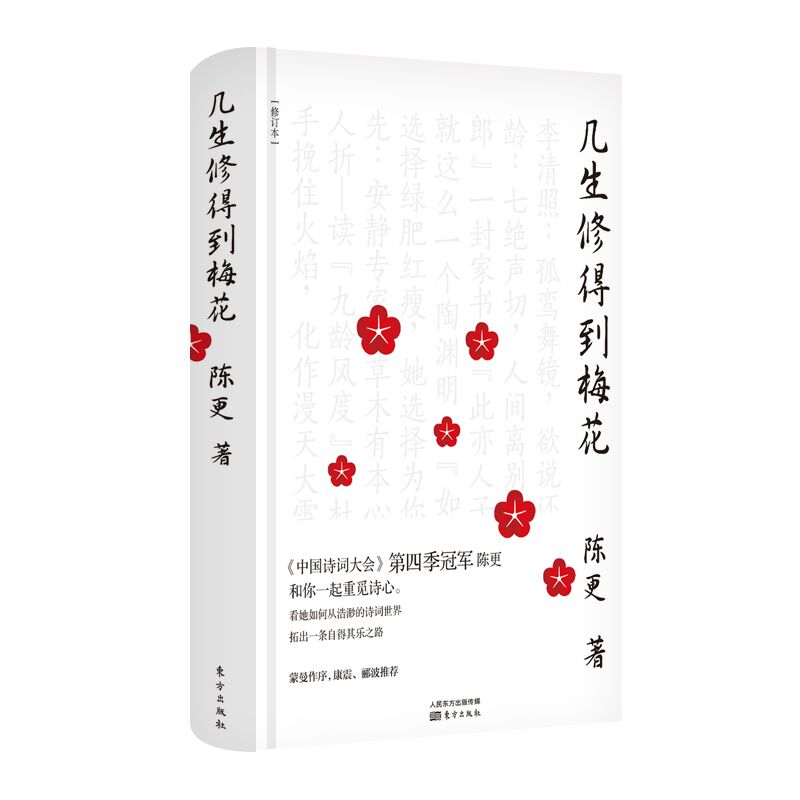
陈*,《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明星选手,北京大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在读博士生,被誉为“从函数定理的工科博士到风花雪月的诗词女神”。屡次获得“**奖学金”、“菲尼克斯奖学金”、北京大学“忠孝振兴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等荣誉。因连续四年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而*到关注,并因表现出色被选为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活动推广大使”。作品曾发表于《光明*报》等媒体。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韦应物在写诗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两地书 有的诗像鲜榨橙汁,“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甜蜜适口,鲜亮清新,但喝过也就喝过了,只那一霎的滋味;有的诗像提拉米苏,“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温厚馥郁,层次丰富,有旖旎的幸福幻觉,但吃多了,也会觉得腻;有的诗则是上好的明前碧螺春,譬如这首,乍一看平淡无奇,细品来深远悠长。不讨好,不用力,从容清冷,历久弥新。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静静地想念一个人,本身就足够美好。况且**恼人,夏夜燥热,只有秋夜可爱,天清风凉,是一年四季*温柔的时候,大自然*包容的时候。人处于自然之中,*容易忘却人世繁杂,把心放空。但在这样该“放空”的时候,心头却能浮现出故人,可见这友情的分量。 “山空松子落。”在寂静的天地之间,有成熟饱满的松果儿“噗嗒”一声落在厚厚的、积年的深林落叶上,这样的声响,能让人顿然感觉到生机,但背景是清秋的空山,又顿然感觉到凄凉,这是丘丹所在的地方。禅化的隐居境界该如何描摹?这一颗松子落,已然胜过万语千言。你也能隐隐感到,俗世政务缠身的韦应物,对这禅境的向往,都含蓄地表现在了此刻对它的想象里了。 “幽人应未眠。”我揣摩你所在的环境,是寂静空山,有松子时不时落下;我揣摩你在做的事情,你这样一个雅人,在这样的夜晚,一定也舍不得这美丽的夜色而不忍睡去吧。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是一封两地书。一来,这一书,一时间,却有两个空间,如“渭北春天树,江东*暮云”,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在秋夜漫步想念你,你在空山**亦未眠。二来,换个角度看它,它又像是两颗心,一人一句,穿越时空的对话。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秋夜适合散步,也适合想念你。 我这里万籁俱寂,与静穆山林相对而坐,时有松子下落,这“噗嗒”一声让我心里一动,想到你应该也没睡吧。 于是我不禁想到顾城的《门前》: *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恬淡其文,深情其人 《红楼梦》香菱学诗后,有这样一段笑话——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湘云听了,忙笑问道:“是哪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湘云香菱听了,都笑起来。 韦应物曾出任苏州刺史,所以世称韦苏州。这段话说的是两个姑娘学诗之痴,可宝钗何等学问,在卷帙浩繁的诗册中,她举了四个诗人,四种特色,其中便有韦应物的淡雅。可见他一支纤笔,竟开辟了一方天地,以一个淡字深入人心。但田园诗人那么多,个个都淡,他的特别,在于浅淡背后所藏的饱满的生命力与压抑的深情。好比一个挂在角落的竹斗笠,布满尘灰并不起眼,但它来自一竿听过山风、看过雷暴、浴过霞光、扎根于山石中的好竹,因此,手触其上,能感到它有细密的纹理、有不屈的生命、有仍在流淌的血液。又好似披着轻纱戴着幕篱的美人,只留给你一个缥缈的背影,看不分明那容颜是怎样的明眸皓齿国色天香,但却在猜测怀想中,比一览无余的美,多了一番特别的意趣。 正如他以松子落地的轻微,来隐喻人心里感情的细腻,我想,韦应物淡雅中的生命力与深情,来自他用一颗诗心,将人百种感官**精微的知觉与感触无限扩张,*常生活中难以捕捉的那些飞珠溅玉的回忆、起伏无边的感怀,都在这些描述中浮现出来了,于是我们深感共鸣,于是我们记住了他。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是体感温度。今朝是时间,晨起感到皮肤有凉意,山中是空间,在这一时间将冷这一知觉无限扩张,扩张到了深山里,由我的冷推及你的冷,于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的念头,像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俱全。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是听觉。故乡遥,何*去。南方萧瑟的秋雨之夜,有雁声北来,这归雁正从故乡来。于是听觉无限扩张,这雁声仿佛就是从故乡传来。或许这只雁曾经经过我家,替我看望过我的家人;它现在就要回到春天时离开的它的故乡了,而我归期渺茫。这从我的故乡来,又要回它的故乡去的雁声,牵出多少欲说还休的乡愁。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是视觉。海门是长江入海处,该是波涛奔流巨浪汹涌,可诗人的眼睛却从大江大海表面的大动静中,看出其水波深处的平静深邃。他的目光从江海交融的混浊无限扩张,扩张到深深深深的海底;江树在雨中静静伫立,但一派朦胧中他看到了水雾缭绕,于是树也有了翩跹袅娜的多情之姿。江海其深,离思其深,江树其渺,别愁其渺。之所以在这里细细地看这些景物,是因为想多留在送别之人身旁;或许看清楚这些送你时的场景,就能把你我的情谊留在心上。 “居闲始自遣,临感忽难收”,是送女儿出嫁的复杂心情。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早早地就开始在平*里劝自己女大当嫁,总会有这么**。可是礼乐响起,要起轿的一刻,依然悲伤难自抑,原来心理准备毫无用处。他将这大婚当*的不舍无限扩张,扩张到了开始为女儿出嫁做准备的那**。那种平*里自我安慰的伪装,那种关键时撑不住而号啕大哭的心情,我们都经历过。因此读到这里你会惊叹,你会想起那些如烟往事,并感激诗句给了你开启往昔感动的钥匙。而这份设身处地的温暖,来自诗人精微的感知,对生活的用心。 **细腻的感官总在平静和恬淡中来,因此*动人的感情似乎*是冷静时的感情。强烈的情绪反而容易模糊了环境,模糊了自己,所以韦应物下笔是淡雅的,甚至当他终于想要呐喊的时候,却还是像略带温柔的呼唤,还是要连声唤着“胡马”,还是有“雪”“路迷”“*暮”这样柔软朦胧的字眼,依然带有韦式色彩,是一种隐忍的深情。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无穷*暮。 细腻淡雅的他,像他的名字一样,有苏州的清韵,有万物的邃邈。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韦应物在写诗。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韦应物都知道,他把这些,都写进诗里了。 他又梦到了李白 ——“情圣”杜甫 梦李白(其二) 浮云终*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他又梦到了李白 有一次参加一个诗词论坛,开始前,在休息室里,我有幸见到了诗词研究专家周笃文老先生。他很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和我说起话来。 “那么,你*喜欢哪首古诗呢?” “杜甫的《梦李白(其二)》。” “哦……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老先生用长长的尾音念完了这句诗,就沉默了。我以为他会问我为什么,还在想该如何回答。但直到论坛开始,他也没有再问我。他似乎陷入了沉思,像是因为这首诗而想到了什么。 《梦李白(其一)》《梦李白(其二)》《天末怀李白》,讲的都是杜甫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李白,而他们竟然都被蘅塘退士收入了《唐诗三百首》。也就是说,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构成了蘅塘退士心里唐诗世界的一百分之一。 杜甫望着天空发呆的时候一定常常想起李白,反正起了凉风他也会想起李白,云飘来飘去他也会想起李白,所以他才会说“浮云终*行,游子久不至”。李白,像浮云一样不停地四处流浪,让人牵挂。“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这句诗总让我不禁莞尔。一看到它,杜甫那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忧郁侧脸,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满脸憨笑的撒娇模样,还有一点扭捏,还有一点亲昵。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诗里总有真性情。这句诗好笑之处还在于实在是十分自恋,明明是杜甫一连三夜梦到李白,还非要说是李白的一片真情实意,夜夜不辞劳苦到他梦里来。“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毕竟是梦,天亮前还要赶回去,所以他见到的李白总是行色匆匆,反复念叨:来一趟不容易啊。这里,虽是想象,虽是梦境,却也让人动容。你能想起那些团圆的不易,那些人生的艰难。“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是啊,听着李白说不易,杜甫也想到了来入梦之路万水千山,担心李白在入梦路上遇到危险。“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李白要走了,出门时他不经意间做了个小动作——挠头,那头上青丝不再,只剩下满头白发。这熟悉的动作和刺眼的白发,让凝望着他的背影的杜甫湿了眼眶。他不禁想起了这个头发都白了的才子,一生少有命达之时。 我们只有对一个人满怀深情,才会对他习惯性的小动作了如指掌,才会因为他一个背影就湿了眼眶,才会在所有人都关心他飞得高不高时,独独关心他飞得累不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真的心疼李白,满城锦衣华服,独李白寒酸潦倒;满城意气风发,独李白枯槁憔悴。而以他的盖世才华,明明不该如此。“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想到这里,杜甫悲问苍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友人;为什么他都已经韶华不再,还不能让他安稳地度过余生。“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想到李白余生所剩无几了。他默默地想:人死后有多么显赫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希望他活着的时候能平安喜乐。 《梦李白(其二)》很特别,堪称诗词中的后现代风格意识流。几个臆想中的画面,一段朦胧的心理活动,像电影中的《盗梦空间》一样任性大胆,又像《花样年华》一样沉闷平淡又莫名地刻骨铭心。 杜甫将李白思来想去啊。他将李白放入广阔而没有尽头的空间里,发现他亲爱的朋友在冠盖满京华里格格不入;他将李白放入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时间里,发现他亲爱的朋友因为身后千万年的盛名而**孤独。 这样的感情让他忘了一切,也忘了自己。哪里还有已入狱的李白,哪里还有被流放的李白,哪里还有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李白。在这里,我只看到了,杜甫的李白,杜甫心尖上的李白。 让人沉默的杜甫 知乎上曾有一个问题:“小时候背那么多诗有什么用?”网友菠萝马回答说:“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情深,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蛇灰线、伏脉千里。” 我相信,周笃文老先生的沉默,就是诗中的情深在伏脉千里后的迸发。而因为想到了杜甫的诗而沉默,也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他善于捕捉心底*细腻*柔软的情绪,唤起你*悠长*隐秘的生命记忆。 我曾经在与父亲久别重逢的一刻想到了这首诗中的一句,“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我的父亲,年轻时没能上大学。他一生善良而倔强、孤傲,也曾有过许多热血沸腾的梦想,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实现。他常有*挫的时候,但总沉默不说。童年时夏天的夜晚,父亲常带我去家附近的大桥上纳凉,大桥上车来车往,桥下是滔滔渭水。我在席子上玩耍,父亲在几米外的路边坐着。过大卡车的时候,桥面会微微震动,我就会下意识地抬起头看看父亲。他的背很瘦削,单衣下看得到突出的脊骨,他微眯着双眼,几小时一动不动地,沉默,像是在望着南来北往的汽车,又像是在望着这桥上光带之外的茫茫夜色。我那时候不太懂那个背影在想什么,后来常常想起,总会想到落寞这个词。 长大了,我在外求学,与父母聚少离多,常常大半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从火车站坐大巴车,车会经过家门口,父亲总在路边等我。家里是老式住宅楼没有电梯,他会帮我把行李箱从车上搬下来,然后扛在肩上,走楼梯上六楼。这是我早已习惯了的事。 但有一年,车快开到了,远远地我看到父亲站在路边,他穿着大伯留给他的棕色皮夹克。背景是冬*路边一排光秃秃的行道树。我看到父亲在已龟裂的并不合身的皮夹克里,显得单薄憔悴,他搓着双手,头向前探着,背弯了下来,站得一点也不挺拔。他的头发稀薄,显出老态来。这个画面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心里突然涌起了莫大的难过,父亲老了;我想起了“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带着壮志难酬的遗憾,父亲老了。 这就是伏脉千里。你总会在一个时刻,和你曾经读过的某一句也许与那个时刻看似并不相关的诗句,产生莫名其妙的共鸣。 初发心菩萨 如果你不了解杜甫,你或许会觉得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冷冰冰的抑郁症患者。但事实上,杜甫是一个深情的暖男。杜甫的深情,不仅是对李白,他对天地、对万物都满怀慈悲。 你看他在身陷囹圄时对妻儿设身处地的疼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你看他在自身难保时对路遇落难之人的嘱咐,“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你看他在颠沛流离的逃亡之途还要呐喊,“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你看他面对漫漫前路时对萍水相逢百姓的同情,“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你看他在何种境地之下怀想,“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看他在潦倒时对友人的情深,“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就像读这首《梦李白》,我们能感*到他对李白的挂念与同情,可合上诗卷,却恍然惊觉,杜甫自己,不也正遭*着“厚禄故人书断* ,恒饥稚子色凄凉”吗?若负平生志,若负平生志,而杜甫的平生志呢?当他蹒跚地迈出破旧的茅屋门,谁在凝望他搔白首的背影?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冻死亦足。”猛然间才想起,原来,他始终这样“无我”。 若问我*喜欢的诗人,我会说是杜甫,但若问为什么,我却总也说不好。 后来,在简媜的话里看到了答案。 *难的是,在困苦流离之中仍保有宽容平静的微笑;*珍惜的是,在披风带雨的行程中,还能以笠护人。若有这么干干净净的人,便是初发心菩萨。 燕园居二三事 “我还有这里” 每次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若是发生了一个从外界回到学校的过程,就会神奇地感觉好多了。心中安定之余,生发出一种“我还有这里”的庆幸与欣然。 从校园走进图书馆,这种感*又深了一层。 我*喜欢图书馆长长的走廊,一侧是很大的窗,一侧是列满书架的阅览室,阳光斜照,有用各种语言在轻轻读着什么的女孩子。我*常去的四楼,还有一个喜欢坐在走廊一角专注看一本旧书的保洁大叔,消瘦沉静的侧影,总让我想起那些曾在这里工作的民国先贤。他穿着陈旧暗淡的工作服,像是从那时穿越而来,或者时间从来都没有移动过。 记得一次在机场登机口旁的书店,随手翻起刘震云老师的新作,被女主人公风风火火的性子吸引。登机广播催了好几遍,我才意识到自己该登机了,赶忙放下书拖着行李箱跑过去,回到学校之后念念不忘,想立刻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便不怎么抱希望地在图书馆的主页上搜了搜—— 是刚刚才付梓的书,简直油墨未干——可竟然就有,骑车过去就能捧读起来,接续千里之外的缘分,还伴着图书馆大大的落地窗与温柔的落*余晖。所以,燕园在我心里近乎一个神祇的所在,可以满足我的每个愿望。 这几天一打开图书馆首页,就会看到一幅古画,荒寒色调的临水台榭,左下角题有几行小字:“勺園圖,又名《米氏勺園圖》,是明代**畫家吳彬應其好友勺園主人米萬鐘所邀,為其勺園所繪制的圖卷。該圖與北京大學舊藏米萬鐘的《勺園修禊圖》相映成趣,作為校園歷史研究和人文珍藏的一個亮點,照耀著古老而又年輕的北大校園。”让人看了不禁有点恍惚,有庄周梦蝶之感。勺园,现在是园子西南角一带建筑的名字:勺海,勺园食堂,勺园西餐厅,勺园宾馆,勺园一号楼,二号楼……原来园子*早即名为“勺园”,不知道主人米万钟当年命名此园时,有无“一勺水也作了海,我们看荷花”之意。 “食堂阿姨的言简意赅” 年岁渐长,食量愈减,以至于点一人食的麻辣烫或麻辣香锅,都会小心翼翼地问食堂阿姨,有*低消费吗?她们总善意地一笑说:“没有”。言简意赅。但为那几片平菇、青笋,就劳烦大厨师傅们颠勺,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可燕园就是这么暖,连食堂师傅都如此包容,吃着专为我炒出来的小灶,几欲潸然。 东坡肉窗口的那位大姐,抬起头来打量了我一眼,便低头抄起一把大勺在盛肉的盆里翻啊翻,拣出一块*瘦的舀起来,大勺一伸,问:“行吗?”还是言简意赅。她一定想我就是那种买一块肉吃要下好大决心的年轻女孩子,瘦骨伶仃的还**上七八次秤,可我其实爱吃肥的。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攒起勇气说一句:“大姐,其实我想要肥一点的。”只有像董小姐那样带着从没忘记的微笑,作出很感激的样子说:“可以可以!”然后端着一方皮下脂肪略薄的肉,失望地离开。 “那边风景好” 从东门外成府路的过街天桥正中眺望北大,会看到它对称的歇山顶建筑结构和背景的群山,*高的是图书馆的屋脊,再高处是山脊,同一色系,美得很有层次,能发现整个园子处在庇佑中。那山的线条与弧度恰到好处,在冷峻与温柔之间,工笔与水墨之间。 背景是一圈山,尤觉安心。每天早上去实验室的路上经过天桥,回过头能不能看清楚西山,是我了解那天有没有雾霾的方式。看不看得到柏树毛刺刺的感觉,看不看得到深绿底色里白色的山径,是我了解雾霾有多严重的方式。晴朗时是工笔画,雾霾天是水墨画。为了看那一圈山,跑了好几次宿管中心,打听楼里西侧的寝室有没有人要毕业,可不可以搬过去。被问起原因,如实答曰:“那边风景好”。结果总是被取笑,说你是来读书的还是来看风景的。 山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因此*眷恋这里。 燕园的夜晚不会特别明亮,小小的暖黄色路灯很温存,但多的是大片寂静的幽黑。勺园对面的长椅,夜里十点静静地去坐一会儿,在被蚊子发现之前离开。每一棵树的形状都恰到好处,*茵在脚下铺开,我感觉自己已经融入其中,被接纳了。 近几年未名湖去的少了,多因为那里总是游人如织。未名湖*好的观赏时间是中宵,这时候湖心岛的树影朦胧难辨,湖岸隐在暗处,你便可以想象它是你的玉鉴琼田三万顷。水面光滑如镜,月中山色镜中看。 去年初夏,未名湖里来了两只黑天鹅。常用镜头记录校园的一位同学在摄影*志里记道:“ 是五月十*左右来的,只有一只,徘徊在未名湖东北区域,不知道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反正突然就出现了。刚开始大家都特别兴奋,天天有许多人围观。不久后又来了一只,它们一起徙居到了翻尾石鱼附近的小岛上,并且很快融入了当地“土著”——绿头鸭和鸳鸯的生活圈,开始吃游客喂食的馒头等食物,并啄食岸边的芦苇和其他野*来改善生活。” *木里的地老天荒 路过春天会开满全校*美西府海棠的外国语学院门口,会想到吴兴华可是在这个地方,写下了“江南**的春雨,乌桕千万树,你的家是对着秦淮第几座长桥”。而钱钟书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他们又是不是在这里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音美意美形美”的翻译标准的呢?。 静园六院、图书馆南门外和松林附近有宗璞喜欢的紫藤,曾探进她窗里的丁香花枝,被她赞为“雪色映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年年春天香得汪洋恣意。朗润园季羡林先生种下的季荷,依旧亭亭,季先生称赞“纵浪大化中,无悲无喜”的二月兰也都还在。十月末,勺园外的白玉兰就已准备好如鼓胀小灯泡似的花苞了,而未名湖南畔的蜡梅还绿叶葱茏,这时,西门里两株几人合抱天庭饱满的老银杏已华灿得近乎奇迹,几乎占满整个天空,每次进门都不由得看呆了。园子里处处可见谦卑温和上了岁数的老侧柏,虽不高大,却坚定地守护着这里。 燕南园的房子,荒烟蔓*,缓踱的猫咪,脚步悠然而永恒。一入园,心底就起了地老天荒的念头。 夏时的黄昏,经常会下一场雷声滚滚的暴雨,天色暗得像世界末*,这时候,园子里几百年的老树翠**滴。暴雨匆匆,天空干净利落地迅速放晴,太阳带着无辜的表情出现,说:“呃,刚刚打了个盹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雨季的大树浓荫下总会立着一丛丛玉簪,鲜碧剑叶,白玉花瓣,*可贵的是花气幽香细净,沁人心脾。一次路过时实在没忍住,折了一枝回去插在瓶里。没想到玉簪的生命力极强,在我的花瓶里足足生活了两周,不仅正盛放如百合的簪子继续开着,已伸长了的玉簪后来还绽开它的花苞盛放,那些藏在绿萼中如珍珠般的小花苞竟然也在清水的供养下,探出头来,伸开如玉的簪子,让一枝枝玉簪奇迹般地长了,又长了,花苞大了,开花了。汪曾祺曾说一朵荷花开花时仿佛在说:“我开了。”而这些玉簪努力地生长开花,仿佛在对让她们离开故土的我说:“我们原谅你。” 长长久久的北京 北京这地方,总有人说它这不好那不好,我听过*让人发笑的理由,出自一位大概是南方来的朋友,说:“一个城市里怎么能没有江河呢,让人不能'舒服'!” 记得自己当时还弱弱地驳了一句:“有昆玉河呀…” 对方*生气了:“那也能算!” 可北京这地方,待久了真是让人眷恋,让人生出长长久久的想法。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 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儿香 夏天的炎热全部被遗忘 酌一杯佳酿漂远方 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拨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一片西瓜就能满足的北京人,吃到上好的沙瓤可是要高兴地唱一两句的,那可是“真正的”沙瓤啊!而在燕园的环境里,也有一点这样的小满足、小迟钝,处处敦厚,不张扬。这里没有高楼,没有外表华丽的现代化建筑。可正像图书馆首页所说的——这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北大校园。每**,各个角落里都有奇迹上演,人们奔跑着,汗水挥洒着,而燕园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