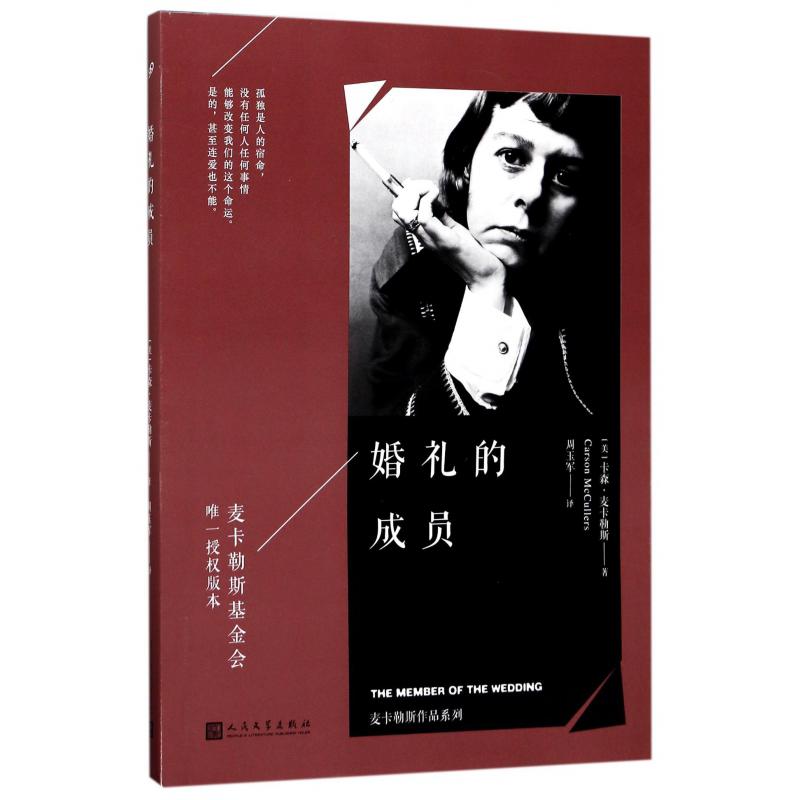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17.70
折扣购买: 婚礼的成员
ISBN: 9787020117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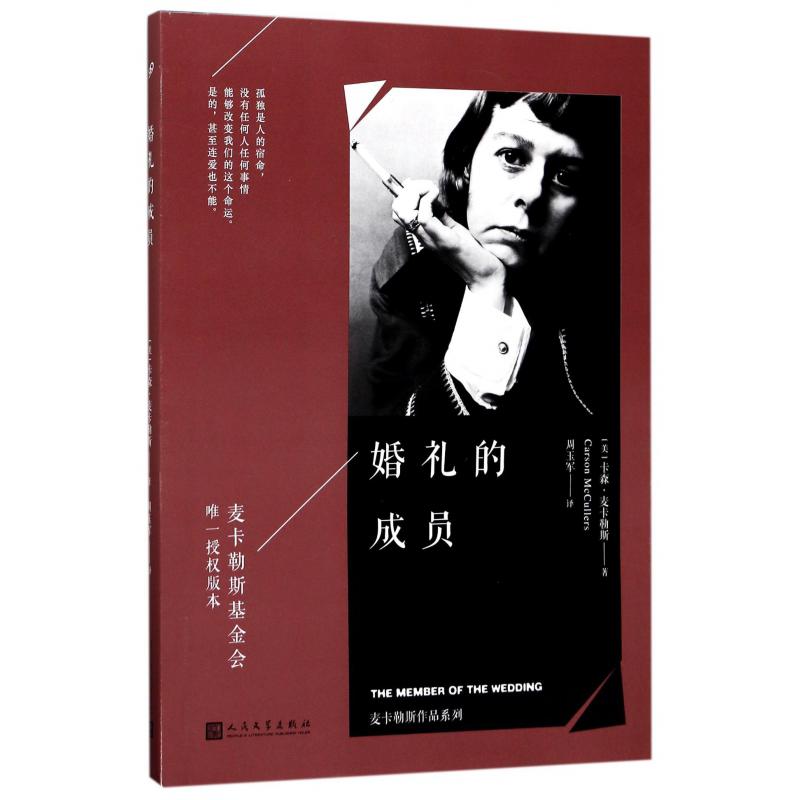
[美]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横扫欧美文坛的孤独小说家,生于美国南方小镇乔治亚州府哥伦布,是一个珠宝店主的女儿。15岁时从父亲处得到一台打字机开始了写作生涯。23岁时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34岁时出版经典代表作《伤心咖啡馆之歌》备受好评。她一生缠绵病榻,于29岁瘫痪并患抑郁症。又经历多次感情纠葛,爱而不得,心力交瘁。50岁时去世于纽约。她才情宽广,任性而孤傲,将一生痛苦浇铸为天才的文字,阐释人类永恒的爱与孤独。主要作品:《心是孤独的猎手》《金色眼睛的映像》《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没有指针的钟》等。
一切从弗兰淇十二岁时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开 始。这个夏天,弗兰淇已经离群很久。她不属于任何 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弗兰淇成了一个孤魂 野鬼,惶惶然在门与门之间游荡。六月的树有一种炫 目的亮绿色,但再晚些时候叶子就变得发暗,小镇也 黑下来,在太阳的烈焰下皱缩成一团。起初弗兰淇还 四处走动,干这干那。镇里的人行道在清早和晚上灰 扑扑的,中午的太阳为它们上了光,水泥路面仿佛在 燃烧,闪亮如玻璃。最终人行道烫得让弗兰淇难以下 脚。她老给自己惹麻烦,她私底下的麻烦是那么多, 觉得还是待在家里为好——家里只有贝丽尼斯。赛蒂 .布朗和约翰·亨利·韦斯特。他们三个坐在厨房的 餐桌边,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又一遍,于是到了八月 间,那些话变得有声有调,听起来怪里怪气的。每到 下午,世界就如同死去一般,一切停滞不动。到最后 ,这个夏季就像是一个绿色的讨厌的梦,或是玻璃下 一座死寂而荒谬的丛林。然后,在八月最后一个星期 五,一切都改变了,改变突如其来。下午一片空白, 弗兰淇一直在困惑,她还是想不明白。 “真古怪,”她说,“就这样发生了。” “发生了?发生了?”贝丽尼斯说。 约翰·亨利在一旁听,安静地看着她们。 “我从没这么迷惑过。” “可你迷惑什么?” “整件事。”弗兰淇说。 贝丽尼斯回应道:“我想你脑子准是被太阳烤糊 了。” “我看也是。”约翰·亨利轻声说。 弗兰淇自己几乎也要承认。当时是下午四点,厨 房四四方方,寂静而灰暗。弗兰淇两眼微合,坐在桌 边,心里想着一个婚礼。她看到一座静静的教堂,奇 怪的雪花沿着彩色的窗斜斜滑落。婚礼中的新郎是她 哥哥,他的面孔被一团光亮所取代。新娘也在那儿, 拖着长长的白色裙裾,这位新娘同样也没有面子L。有 些事情,关于这场婚礼的,给了弗兰淇一种无以名状 的感觉。 “看着我,”贝丽尼斯说,“你忌妒了?” “忌妒?” “忌妒你哥哥要结婚?” “没有,”弗兰淇说,“我只是从没见过像他们 俩那样的人。今天看着他们走进来,感觉很怪。” “你就是忌妒,”贝丽尼斯说,“去照照镜子。 看你眼睛的颜色就知道。” 水池上方有一块水汽蒙蒙的镜子。弗兰淇照了照 ,但她的双眼是一贯的灰色。这个夏天她长得这么高 ,简直成了一个大怪物。她的双肩很窄,两腿太长, 穿着一条蓝色运动短裤,一件BVD汗衫,赤着脚。她的 头发剪得像男孩子,剪了没多久,短得还未两边分开 。镜子里映像扭曲,但弗兰淇知道自己的模样。她耸 起左肩,头转向一边。 “哦,”她说,“他们俩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我只是搞不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有什么事情,你这傻瓜?”贝丽尼斯说,“你 哥哥带着他想娶的姑娘,今天回家来跟你和你爸爸吃 了顿饭。他们打算这个星期天到她在冬山的家举行婚 礼,你和你爸爸要去参加这个婚礼。事情不过如此。 你到底在烦什么?” “我不知道,”弗兰淇说,“我打赌他们每一分 钟都很快乐。” “那我们也找点乐子吧。”约翰·亨利说。 “我们找乐子?”弗兰淇问,“我们?” 他们重新在桌边坐下,贝丽尼斯为三人桥牌发牌 。从弗兰淇记事起,贝丽尼斯就是厨娘。她很黑,肩 膀很宽,个子很矮。她一直说自己是三十五岁,说了 至少三年了。她的头发分开,编成辫子,抹了油紧贴 着头皮,脸孔扁平安详。贝丽尼斯只有一个地方不妥 ——左眼是一颗浅蓝色的玻璃。它在她安静的黑脸上 向外恣意地直瞪着。她怎么会要一只蓝色眼珠,那不 是凡人能想明白的。她忧郁的右眼是黑色的。贝丽尼 斯牌发得很慢,遇到扑克被汗粘在一起就舔舔大拇指 。发牌时约翰·亨利每一张都看。他敞着胸,白色的 胸脯湿湿的,脖子上用细绳拴着一只小小的铅驴。他 是弗兰淇的近亲,她的亲表弟。这个夏天他要么和她 一起吃饭,打发白天的时间,要么就和她共进晚餐, 度过整个夜晚。她没法把他打发回家。他看上去不像 已经有六岁了,却长着弗兰淇所见过的最大的膝盖, 并且总有一边上面结着痂,或者贴着纱布,都是他自 己摔倒擦破的。约翰·亨利有一张眉头紧皱的白白的 小脸,架一副金丝边小眼镜,每一张牌都看得很仔细 ,因为他正输着,欠贝丽尼斯五百多万。 “我叫1红心。”贝丽尼斯说。 “1黑桃。”弗兰淇说。 “我要叫黑桃,”约翰·亨利说,“这是我要叫 的。” “嗯,那你不走运,我先叫了。” “啊,你这蠢货!”他说,“这不公平!” “别吵,”贝丽尼斯说,“老实说,我看你们都 是乱叫,根本没什么好牌。我叫2红心。” “我没吵,”弗兰淇说,“我无所谓。” 事实确实如此:那天下午她玩桥牌,就和约翰· 亨利一样,不过是碰到什么就出什么。他们坐在厨房 里,这丑怪的厨房让人意气消沉。墙壁上约翰·亨利 的胳膊够得着的地方,都被他涂满了稀奇古怪的儿童 画,这给厨房蒙上一种异样的色彩,就像疯人院里的 房间。现在这间旧厨房让弗兰淇浑身不舒服。她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弗兰淇不知道,但她能感觉到自己 的心挤成一团,正敲打着桌子边缘。 “世界真的很小。”她说。 “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说突然,”弗兰淇说,“这世界变得真快 。”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