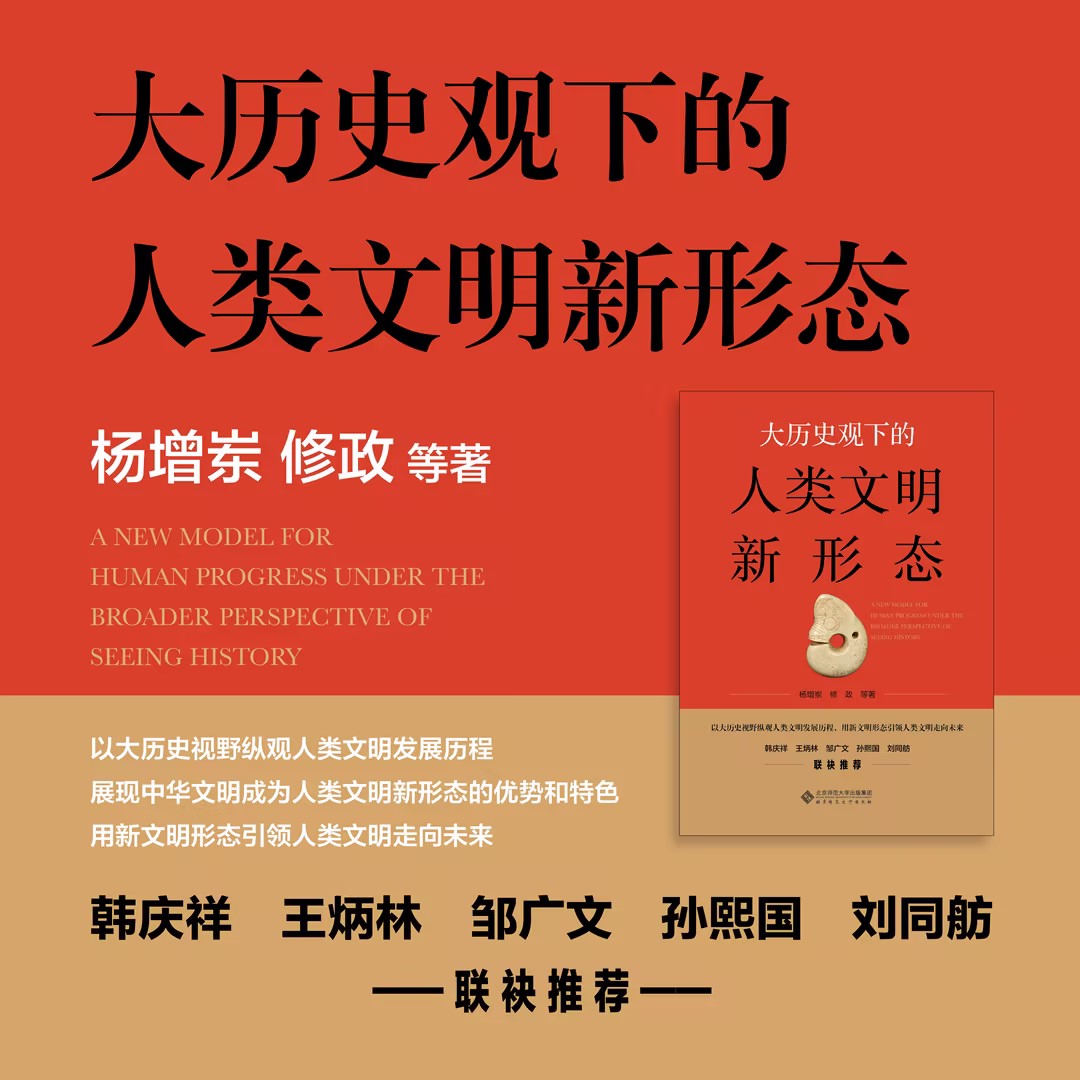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师大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4.60
折扣购买: 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精)
ISBN: 9787303299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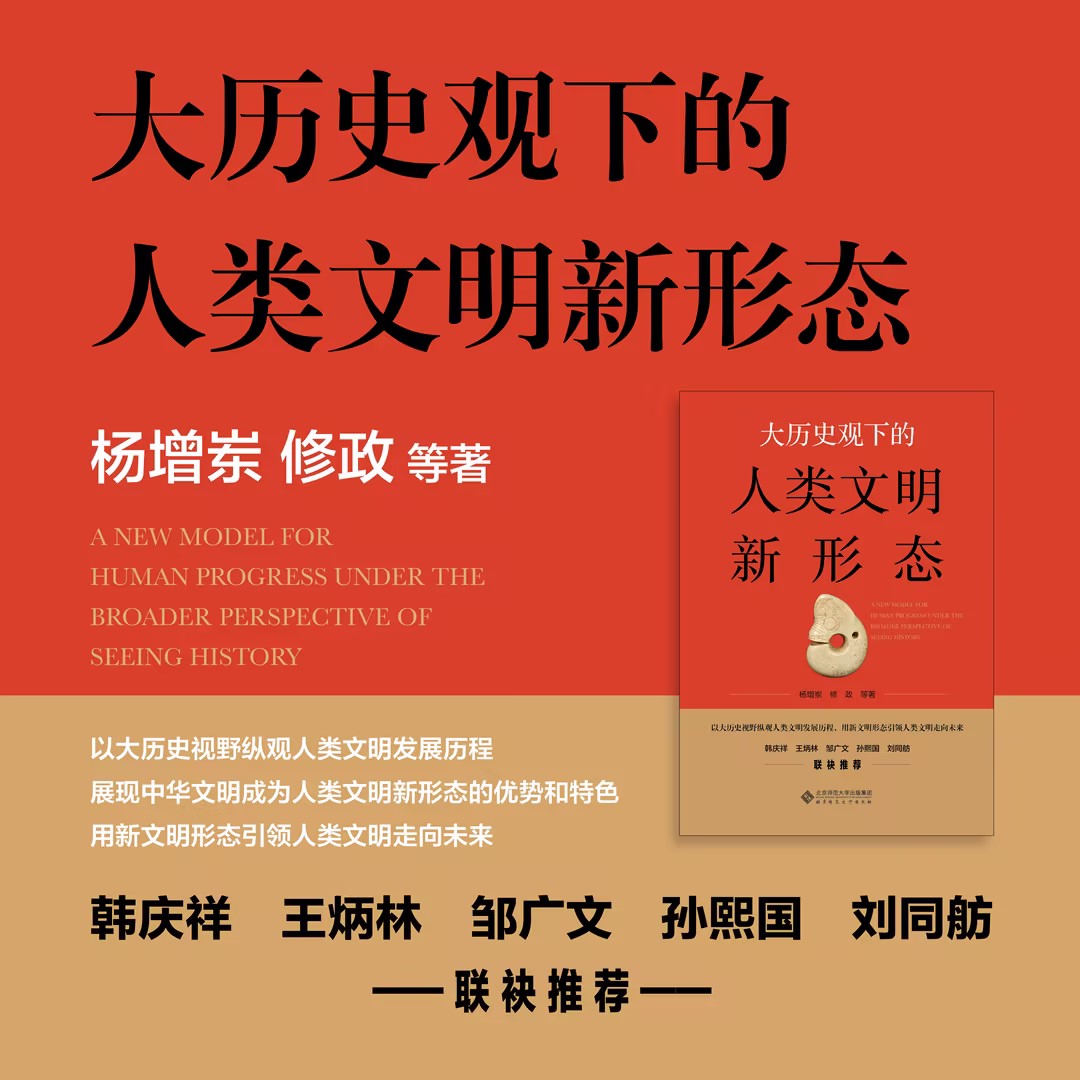
杨增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共青团中央青年理论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入选国家和北京市人才项目,北京市学校思政课青年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首批北京高校思政课特级教师。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等多项荣誉。 修政,美国杜兰大学金融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中国“变色龙”——有限交往下欧洲的中国文明观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的古代历史。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完成了对希腊、埃及和波斯的征服,他的军队越过兴都库什山直抵恒河,建立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一个以古希腊式海洋文明为代表的整体性西方文明初步形成。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同样用了十年时间,秦始皇嬴政东出函谷关扫清六合,书同文、车同轨,九州华夏归于一统,以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完成中央集权政体的建构。两个统一帝国的建立是中西方两种文明形态存续和发展的保障,也是我们得以从整体上讨论中西交往的前提。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外拓展,中国与西方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中碰面。然而,彼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被外兴安岭至喜马拉雅山脉无数高耸的雪峰和茂密的丛林组成的天然“长城”阻隔,仅有阿尔泰山脉与天山山脉之间险隘的关口维系着两个世界之间微弱的交通。 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300年这1500年间,是一个东亚“全盘中化”和西方“走向东方”的过程。这是一个罗马帝国自衰落后未能东山再起,西方逐步分化为“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对立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乌托邦”世界,以其包容、富足、先进的形象和其独有的神秘感,“不可遏制”地吸引身处中世纪的欧洲“中国热”的时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的主线是伴随着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进行器物和技术间的交流。 在东西方艰难地突破地理限制、进行有限交往的时期,大唐王朝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影响力跨越西北的天然屏障,远及波斯。唐王朝通过一系列征服与和亲建立起朝贡贸易体系明确了其在亚洲的政治中心地位,其制度、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令整个“中华文化圈”到唐代基本形成,这是西方人得以从整体视角定位“东方文化”的历史基础。 随后的宋朝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科技的传播伴随着海运的兴盛而发展,传统“四大发明”至宋朝时已基本传至西方。弗朗西斯·培根激动地说:“印刷术、火药和磁铁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至于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在唐宋时期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历程中,欧洲人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富庶、优越、神秘,这一判断符合当时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交往情况。 但即便是在唐宋时期,我们也只能从有限的意义上讨论中西交流,东方与西方在本质上还是两个孤立的系统,而这一切都将因为蒙古人的崛起、西征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而产生质变。蒙古帝国的诞生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是两面性的。首先,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跨越了从前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界线,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地理意义上的东西方首次被纳入同一个政治版图,由血腥的征服带来的“和平”与“繁荣”为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保证。这一时期,大量欧洲的冒险家、传教士随着商队涌向中国。不仅是商品和财富,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也将中国的风土文化带回欧洲。后来,一位从未踏足中国的神父胡安·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以马可·波罗的行记为蓝本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塑造出一个完美、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依据。但蒙古人无情的征伐和屠戮也给欧洲人带来了对东方面孔的无限恐惧,在西方对东方的印象中,“大汗的国土”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的特性,东方既是“天国”也是“地狱”。 讨论西方人的中国文明观,绝对无法绕开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本书为马可·波罗带来了显赫的名声,甚至日后使他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人,马可·波罗的名字就像恺撒大帝和哥伦布一样在西方家喻户晓。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本极富浪漫主义与传奇色彩的作品: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被东方的传说深深吸引,他与家族因为经商需要踏足蒙古统治区域的腹地,突发的战争将他们一行人回国之路阻断,机缘之下最终受邀觐见忽必烈大汗。波罗兄弟受忽必烈大汗的款待在汗八里(北京)滞留了数月,并带着大汗致罗马教皇的一封信回归威尼斯(却因教皇逝世而没能完成使命)。1271年马可·波罗再次启程,这次他游历了中国广袤的国土,甚至在大汗的授命下出任扬州总督三年,在离开故乡二十余年后忽必烈才允许马可·波罗返回祖国。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城市,从中国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使他成为巨富。但随后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让马可·波罗身陷囹圄,在狱中他向碰巧同为战俘的名叫比萨的路斯蒂切洛的传奇作家口述了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这一系列故事才得以保存下来。 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时酷爱使用“伟大”一词,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城市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极尽繁华的地方,马可·波罗讲述,“苏州共有6000座桥梁,桥拱非常高大,桥下甚至可以同时通行两艘大型船只”。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大汗被描述为一位威严、开明的皇帝,甚至在书中讲述了忽必烈大汗对基督教葆有很大兴趣,声称“如果教皇真的派来有能力向大汗宣讲我们信仰的人,他肯定会成为一位基督教徒”。 不得不说书中的这些内容很好地迎合了当时欧洲从贵族到平民的心理,一方面重商主义氛围和初兴资本主义萌芽令欧洲商人对东方的财富不可遏制地向往,马可·波罗将中国描绘成了遍地财富和发财机会的商人天堂。另一方面大汗奢华的宫殿和庞大的后宫、广袤的土地是欧洲许许多多蕞尔小国的王公贵族统治理想的放大版本。西征的蒙古大军让整个欧洲感受到了生死存亡迫在眉睫,但马可·波罗描述下的大汗不但文明开化、仁慈公允,甚至渴望皈依上帝。这一切都令中国成为当时的欧洲人一致向往的“彼岸乐土”。即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在当时便受到质疑,甚至后世的史学研究表明很可能马可·波罗并未到访过中国,但不可否认马可·波罗引发的东方热潮框定了欧洲人“中国文明观”的最初版本。 西方14至16世纪有关中国的作品几乎都与《马可·波罗游记》一样,对中国充满溢美之词,但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和明王朝的建立,东西方愈加频繁的接触使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葡萄牙人伽利奥特·佩雷拉因走私在福建海域被捕,于1549—1552年被明朝官府囚禁,在他的记述中如实写到,“虽然城市像我所述的那样庞大,但居民却很软弱,没有什么资材”。 如果说旅行家和冒险家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于表层,那么对中国人精神实质的理解则主要通过欧洲传教士向东方的一系列传教活动逐步揭开。耶稣会传教士奉教皇敕令向东方散播福音,其中以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传教士利玛窦最为著名。1583—1610年,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利玛窦拥有丰富的数学及天文学知识和精湛的绘图技艺,他为明朝神宗皇帝绘制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系统研习了儒家经典。耶稣会的其他传教士在利玛窦死后将他在中国记录的文字摘录整理成《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了孔子、佛道两家,伦理观念甚至是太监制度,尤其指出中国“整个帝国是由文人学者阶层即通常称作哲学家的人进行统治的”,仁慈的专制君主搭配哲学家治国,这注定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思索欧洲社会的改良方案提供了理想化的模板。 靠着这些耶稣会士的努力,“四书”“五经”等一系列传统文化经典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伴随着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思想层面的碰撞,至启蒙运动时代,欧洲思想家们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了两极分化,推崇者极尽赞美,贬低者则将中华文明形容得一无是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极为推崇中华文化,他认为在中国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认为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认为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还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剧中将儒家所推崇的忠诚奉献精神和成仁取义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剧1755年在巴黎上演,轰动法国剧坛,万人空巷,在启蒙时代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狄德罗对儒家哲学也十分赞赏,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文,对自《易经》至明末清初的中国哲学史详加梳理。他甚至还分析了《易经》与莱布尼茨二进制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抽象思维传统,中国哲学是借助符号、象数、形象来探讨宇宙的本原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高明体系。孟德斯鸠一生中也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留下了大量文字。他最著名的作品《论法的精神》共三十一章,其中二十一章涉及有关中国的讨论,其中“中国政体的特质”“中国的良俗”“中国人的礼仪”等章节干脆完全以中华文明为讨论对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甚至直接引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启蒙运动中对中国文化的反对和贬低声音同样不少,赞同中国“德治”的孟德斯鸠,曾撰长文论述中国专制主义与文化习俗的缺陷。声称“宁愿做野蛮人”的卢梭指出“中华文明的进步恰恰造成了社会的弊病”。主张“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孔多塞则称中国“被一群儒生的迷信所阻碍,故不能进步”。后来的康德对中华文明也多有批评,认为儒家学说“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和哲学只不过是一些每个人自己也知道的、令人不快的日常规则的混合物”,至于道家,则“宁可耽于幻想,而不是像一个感官世界的理智居民理所应当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感官世界的界限之内。因此,就出现老子关于至善的体系的那种怪诞”。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随着东西方联系的紧密,中华文明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愈发清晰也愈发复杂。欧洲的知识阶层对中国从幻想到学习,最终将中华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的历史,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在长达几百年的东西方有限交往的历史中,西方既有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幻想与迷恋,又有对东方堕落、软弱的蔑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近代史由欧洲开启,西方是掌握历史主动的一方,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有限交往下欧洲的中国文明观,而不讨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总的来看,随着东西方的地理壁垒被打破,随着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在近代欧洲人的眼中,中华文明的形象是神秘且复杂的,中国就像一条“变色龙”。欧洲人中国文明观长达几个世纪的嬗变背后是资本主义最终确立了其在全球的统治,世界也处在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主宰之下。本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理解资本主义文明。(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