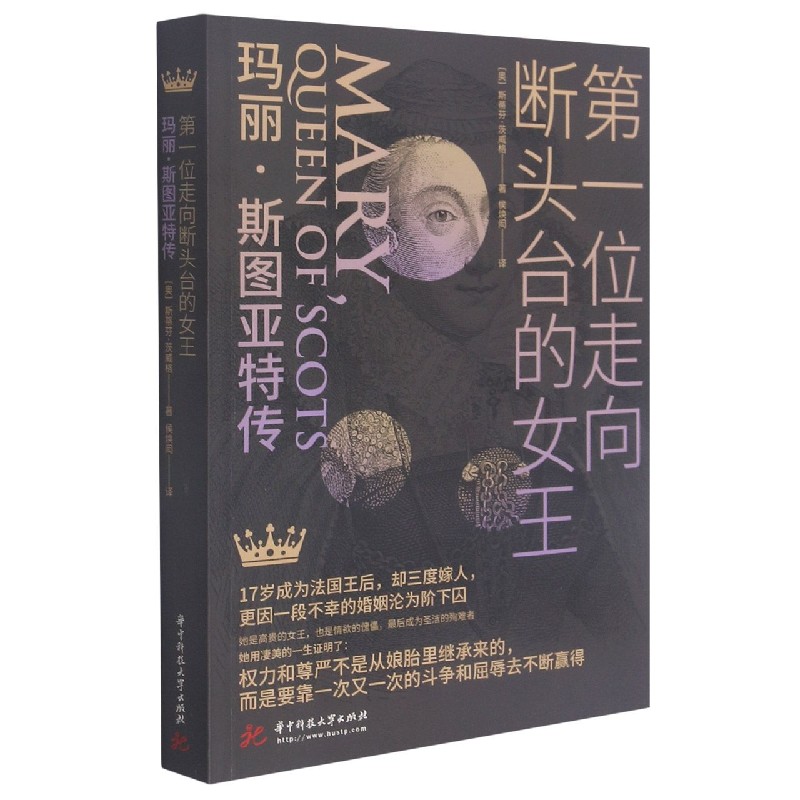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31.87
折扣购买: 第一位走向断头台的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传
ISBN: 9787568072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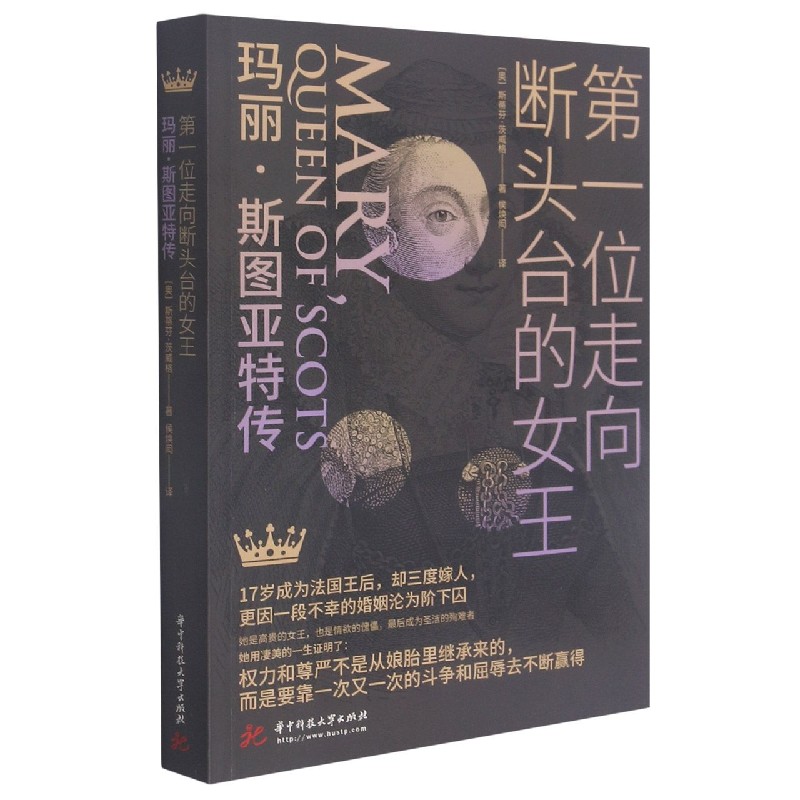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游历世界各地. 代表作《人生转折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危险的怜悯》等;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异端的权利》、《麦哲伦航海纪》、《断头王后》、《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等。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他的作品以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心理刻画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的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
两个年轻女子是全世界*理想的新娘:英国的伊丽莎白和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在整个欧洲,未必能找出一位尚未婚配的王公不派人去向她们求婚的——不管是姓哈布斯堡还是姓波旁,不管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还是他的儿子堂?卡洛斯,不管是奥地利的大公,瑞典和丹麦的国王,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是黄口孺子,年轻的小伙子和成熟的男人。政治新娘拍卖行很久没有这样热闹了。同一国之主的女子结婚,仍旧是扩张君权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在专制政体时代,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婚姻关系生发出广泛的继承权。统一的法国、西班牙的全球大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势都是这样形成的。如今,欧洲王冠上的*后两颗宝石又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伊丽莎白或玛丽?斯图亚特,英国或苏格兰;谁要是通过结婚获得了这个或那个国家,便算赢得了世界霸权。但是这不仅是民族间的竞争,并且是一场宗教战争,是一场征服人心的战争。因为不列颠群岛和它的一个女主一旦归属信奉天主教的并肩王,那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中天平的指针彻底倾向罗马的普世教会,它将重新在世界上占上风。因此,狂热地追逐新娘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事件,其中包含着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 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决定……对于这两个女子、这两位女王来说,这也决定了她们一生的纠纷。她们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牢不可分。倘若两个对手之中某一人通过婚姻进一步腾达,那么,另一人的宝座势必摇摇欲坠;倘若天平的一个秤盘上升,另一个秤盘必然下降。倘若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都不嫁人,一人只是英国女王,另一人只是苏格兰女王,那么,她们之间的虚情假意可能保持平衡。只要一个秤盘重了些,某一人就会强大些,就会胜利。然而,高傲毫无惧色地同高傲对峙,谁也不愿让步,也决不让步。除非拼个你死我活,才能解决这个僵持的争端。 历史挑选了两位大腕女演员来演出姊妹决斗这场辉煌的戏。这两个人,玛丽?斯图亚特也好,伊丽莎白也好,都是资质卓尔不群,旷世少有。同她们的多姿多彩的形象相比,并世的其他君主们——像禁欲主义者一般顽固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像孩子一样胡闹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无足轻重的奥地利的斐迪南,都仿佛成了二流戏子。他们任何人都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两个女子互相对抗的那种精神水平。这两个女子都很聪明,尽管如此,却仍控制不住她们的纯女性的激情和乖僻;两个人都很虚荣;两个人都是从小下功夫准备扮演崇高的角色。两个人都具有同她们的名分相当的威仪;两个人都精通为人文主义时代增添光辉的高雅文化。两个人除了本族语之外都能流利地使用拉丁文、法语和意大利语,伊丽莎白还懂希腊文;两个人的书信都以其生动准确的文体高出于她们宰相的平平淡淡的文牍——伊丽莎白的书信同她睿智的国务大臣塞西尔的签呈相比较,要鲜明生动得多;而玛丽?斯图亚特精雕细刻的、独特的文体,一点儿也不像梅特兰德和梅里的淡而无味的外交函件。这两个女子的非凡的才智,她们对艺术的理解,她们的帝王气度,能够使**挑剔的评论家满意。伊丽莎白敬重莎士比亚和本?琼森,而玛丽?斯图亚特钦佩龙萨和杜倍雷。但是这两个女子的共同点也仅止于个人的高雅文化造诣;她们的内在的对立却被共同点反衬得更加鲜明,而这样的内在的对立自古以来便被作家们理解成典型的戏剧性冲突而不断予以描绘。 她们的对立十分彻底,连她们的生活道路也仿佛图解似的、形象地表现了一点。基本区别如下:伊丽莎白在道路开始时艰难竭蹶,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在道路终结时困苦潦倒。玛丽?斯图亚特的幸福和权势来得容易,灿烂而短暂,好比晨星在天空中闪现。她生而为女王,少小时即已接受第二次涂油仪式。但她的坠落也是同样的迅猛而突然。她的命运仿佛浓缩为三四次灾难,因而像是一出戏——难怪剧作家们那么喜欢把玛丽?斯图亚特选作悲剧的主角。至于伊丽莎白,她的上升缓慢而牢靠(因此适宜于四平八稳的叙事文)。她什么都不是捡便宜得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从小被宣布是私生女,被她的亲姊姊关在伦敦塔里等待被处死,这个早熟的权术家起初不得不耍心眼以捍卫她的生存权利,靠恩典活下去。玛丽?斯图亚特作为国王们的嫡裔,她的不凡是命中注定的;而伊丽莎白则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本事才出人头地。 两条如此不同的生活道路自然是各奔东西。即使有时相遇而交错,也不可能结合。每一次拐弯,性格的每一个特点,都必然反映出本初的区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本初的区别便是一人生来就头戴王冠,好比有的孩子生来就头发浓密;而另一人则艰难地挣扎,靠耍心眼而取得自己的地位。一个人一开始便是合法的女王;而另一个人却是成问题的女王。这两个女子,谁都是因为本人的命运的特点而发展了她本人的、唯独她具有的品质。玛丽?斯图亚特无功而受禄,什么都轻轻巧巧地得到(唉,为时过早了呵!)由此生出了异乎寻常的轻松和自信,养成了她那*高的禀性——一往无前的勇猛,这既拔高了她,也毁了她。她的一切权力都得自神授,她也只向神负责。她只管发号施令,别人理应服从;即使全世界都怀疑称孤道寡是不是她的天职,她仍然在自己身上,在沸腾的热血中感受到自己的使命。她不大思考,很容易激动;她会在火头上仿佛拔剑一般匆促、轻率地做出决定。作为勇敢的骑手,她一拎缰绳,猛力一冲,便跳跃任何栏架任何树篱;她也希望在政治上指靠勇敢的翅膀飞越任何障碍险阻。如果说伊丽莎白把治国的艺术看成是下棋,需要殚精竭虑,那么,玛丽?斯图亚特则把它当作*够刺激的娱乐之一,是令人兴奋的人生乐趣,也是一种骑士的赛马。教皇有一次说过,她是“妇人身而丈夫心”,正是这轻率的勇敢,这强烈的利己主义,吸引了诗人骚客和悲剧作家,也促成了她的夭殇。 因为性格非常讲究实际、现实感达到完美程度的伊丽莎白,专门利用她的对手那种骑士般奋不顾身的失误和疯狂,从而赢得自己的胜利。锐利的、洞幽烛远的、鹰隼一般的目光(瞧瞧她的肖像吧),多疑地看着在她早年备尝艰辛的世界。她少小时就已经懂得命运女神的球会滴溜溜地转,忽前忽后:宝座离断头台只有一步之隔,而死神的前沿——伦敦塔离威斯敏斯特宫也是近在咫尺。所以她日后始终把权力视为某种变幻无常的东西,处处感受到威胁。伊丽莎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护持着王冠和权杖,仿佛它们是玻璃做的似的,而且随时会从手里滑出去。真的,她的一生充满了惊惶和波动。一帧帧肖像对她性格的刻画都令人信服地补充了我们看到过的文字描述:没有一帧肖像叫人感到她开朗、豪放和高傲,像个真正的君主。每幅画上,她的那种神经质的面容都显出戒备和怯生生的样子,仿佛在凝神倾听什么,仿佛在等待什么;她的嘴唇从来没有出现过自信的微笑。脸色苍白,身体笔直,神情间缺乏信心,同时又虚荣地昂起头;穿着富丽贵重、镶满宝石的长袍,好像被沉重的金光闪闪的衣服箍得身子僵硬。似乎只要她一人独处,只要从她那瘦骨嶙峋的肩上扒下那件富丽的衣服,只要从她那瘦削的脸颊上拭去胭脂,她的威仪便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苍白的、茫然失措的、老得过早的女人,一个孤单的灵魂,连自己的困难都对付不了,哪能说得上治理天下呢!女王身上的这种畏葸胆怯,自然离英雄气概相去甚远;而她一贯慢吞吞、迟疑犹豫的作风,无助于叫人领略她的帝王威势。然而,伊丽莎白作为君主的伟大,立足在不那么罗曼蒂克的其他方面。她的力量不表现在大胆的计划和决定上,而是表现在锲而不舍地惦记着积累和贮藏、储蓄和聚敛,换句话说,表现在纯市民的、纯粹是治家理财的美德。她的缺点——胆小、谨慎,恰恰在国务活动的土壤上获得丰收。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是为她自己活着,那么,伊丽莎白活着则是为了她的国家。作为责任心十分强烈的现实主义者,她把当权看成是天职;而玛丽?斯图亚特却把她的名位当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义务的头衔。两个人各有各的长处和缺点。如果说玛丽?斯图亚特轻率的勇猛成了她的致命伤,那么,伊丽莎白的迟缓犹豫*终却对她有利。在政治上,按部就班的坚韧不拔历来胜似奔腾澎湃的力量,认真制订的计划压倒一时的冲动,现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 1. 本书作者是因《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闻名于世的斯蒂芬·茨威格,其对女性深入且微妙的了解同样也反映在了这本书中。 2. 本书传主玛丽·斯图亚特是历史上第一位被 送上断头台的女王,她高开低走的一生充分显示了疯狂而不理智的选择将如何改变女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