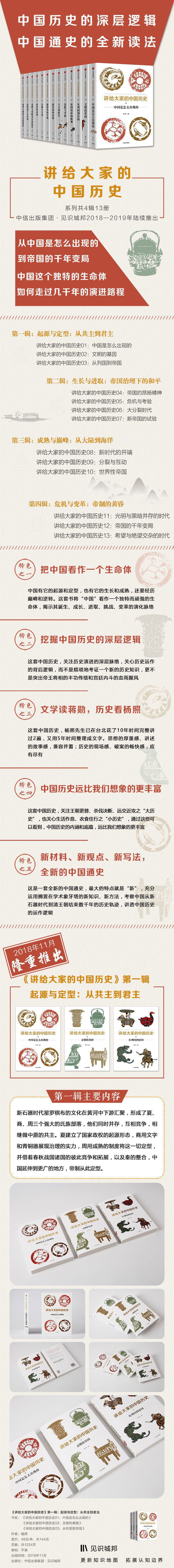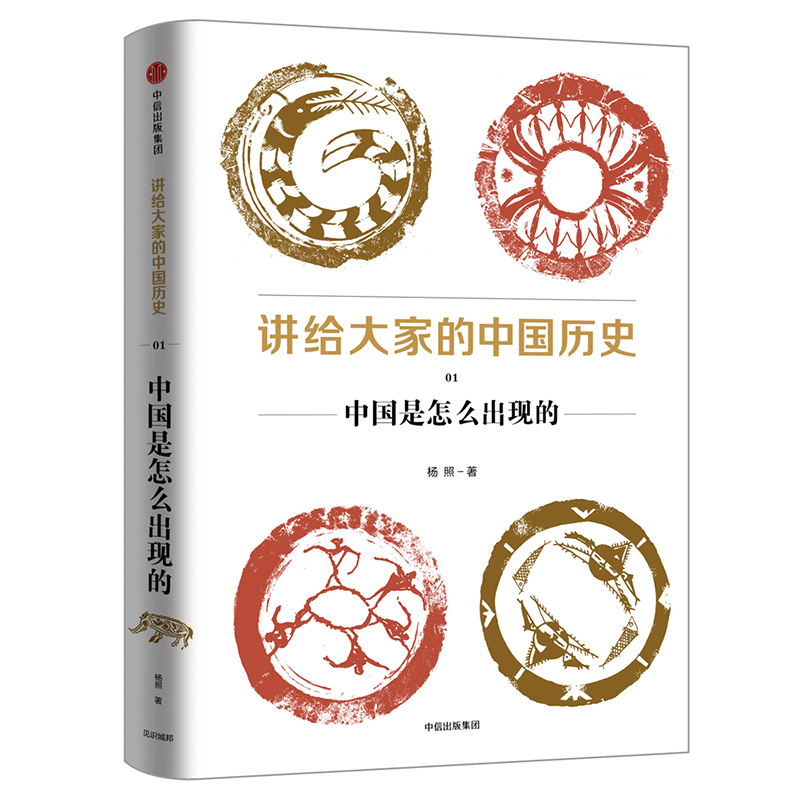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ISBN: 9787508685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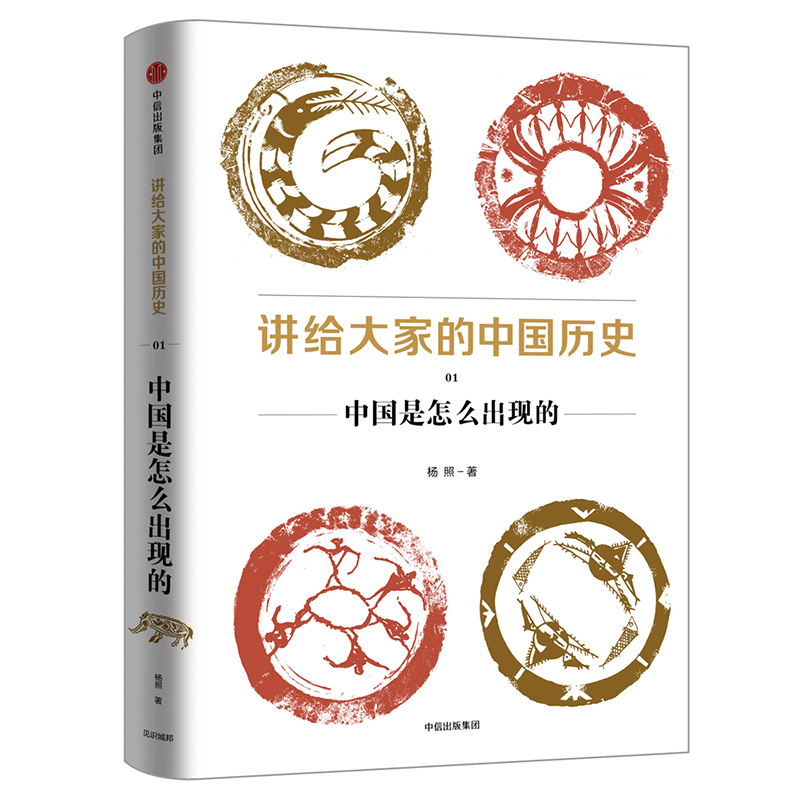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他的创作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迷路的诗》《想乐》《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呼吸》等。
第一讲 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了 0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在开始讲述中国历史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暂时假装从来没有学过中国历史,暂时假设中国历史对你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事物。 我当然知道,大家从前在学校学过中国历史。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大家可能拥有的丰富底子,反而希望大家暂时忘记曾经学过的中国历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过去在学校学的中国历史,其背后有个假设,我们今天必须认真予以检讨。这个假设就是—— 将中国历史当作一个具备高度同构性的民族文化历程。 过去读的中国历史建立在“同构性假设”基础之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从前课本里读到的尧、舜、禹、汤长什么样子?秦始皇、汉武帝长什么样子?唐太宗长什么样子?宋徽宗、明太祖长什么样子?这些皇帝或许各有各的长相,然而,我们从画像中看到的他们身上的衣服和装扮却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要问:“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一直用同构性假设去投射、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那么,许多事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甚至不会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若是以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皇帝,就很难去注意,更难去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如何产生。从皇帝制度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历史,我们才能真切明白秦始皇的重要性,以及秦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说白了,我们得先将皇帝的同构性从脑海中赶出去,才能了解,秦汉帝国的建立,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皇帝的出现与皇帝制度的诞生。 秦汉之前没有皇帝,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去除了同构性假设,我们才能回溯没有皇帝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王和侯,如何遂行有效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权力运作方式,与秦汉皇帝有何不同?再往上推,西周的天子和后来的皇帝又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中需要看到的是“异”,而不是“同”。 还有,如果我们所想象的秦始皇、汉武帝,一路下来,到唐太宗、明太祖,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皇帝,而每一位皇帝都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商朝,不可能理解各种史料明确反映出来的商朝文化,以及商朝的政治统治,也不可能读懂商朝的史料。我们现在赖以了解商朝,最重要的史料是甲骨文。以前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还是弄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的字形,而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记载的活动本质。 甲骨文和我们今天通用的文字有直接且密切的传承关系。一个懂中文的现代人只需一点儿训练,就可以快速认出约百分之六十的甲骨文。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拿到甲骨印记,很快就解读出了很多字。然而认出字以后,学者却要再花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真的清楚一连串文字讲的意思。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绝大部分人习惯用后来的中文及其指涉的内容去推想甲骨文要说的事,那就走上歧途,浪费了很多时间。 02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发生的,都是历史。可是,历史知识和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但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例如,1935 年在台湾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1935年2月13日,一个到圆山附近去游逛的少年,今天我们没法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圆山去的那件事,过去了,消逝了,再也无法还原。又例如,1946年8月10日,一位江西农民被拉壮丁到了部队,派到战场上打仗。我们也没法知道他那一天经历了些什么,那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学、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历史学一直不断努力,想要尽量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留下来,予以重建。但是,能 保留的,能重建的,永远只能是真实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与历史之间,必然是一种选择关系。 历史这么大,历史学只能从中选取部分,予以保留,予以重建重现,并表达出来。历史就像地图一样。每一张地图都有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要将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也就排除掉了一些东西。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有一篇文章讲1∶1的地图。那张地图是覆盖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一大张纸。1∶1的地图不会遗漏任何东西,然而这个地图没有办法用,也没有人要用。地图要有用,必然要缩小,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如此才方便。比例尺越小,地图涵盖的范围就越大,然而相对而言,它能保留的信息就越少。历史学也是如此。 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是1∶1的关系,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般,全都搬上来给我们。这种历史知识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不会有。现实的历史知识必定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将之转化为可传述、可理解的史学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幅地图,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要用一种怎样的比例尺?依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些是历史学极为关键的概念与原则。我希望读者暂时搁置过去的中国历史印象,因为我想带大家走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在重新看这块庞大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是如何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了要给谁用,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先跑到地图后面,检查其制作过程,然后再绕出来,换到另一个山头上往下看,或许最终会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进去的,只是全幅中国历史图景中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只这样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区域视而不见。 03 认识古代中国,从宋明理学开始说起 我们对中国古史多少有点儿印象。这些印象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回溯到明朝中期,从15世纪的一场争论开始讲起。当时士人圈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个争议,是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程朱”和“陆王”代表的是理学内部源于不同的推论而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态度。“程朱”是北宋的程颐(字正叔)、程颢(字伯淳)兄弟,加上南宋的朱熹(字元晦);“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字子静)和明朝的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简单来说,“程朱”认为建立从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程序是“格物致知”;而“陆王”却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明心见性”。 “程朱”强调人要变成合格的人,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功夫,要循序渐进,认识万事万物之理,进而从中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性”。为什么朱熹要强调四书,将《大学》《中庸》突显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因为《大学》《中庸》讲的都是程序,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对“程朱”而言,人要一步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通过格物致知积累学问。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成长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的人。 “陆王”却不是从这种角度看世界的。依照孟子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在于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在于有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心。既然良知——天生的道德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怎么要靠后天慢慢去学,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才培养起来呢?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找到并发挥你的良心。这里不牵涉外在知识。陆象山发挥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认为内在道德本心是“大”,其他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附加的。 这是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重要的士人文化。宋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士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两派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牵涉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政治。谁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标准阅卷?科举考试决定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他们一家子乃至整个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程朱”与“陆王”斗得厉害,因为不同派别对于考题和答案有不同看法,就会选择不同的人,淘汰不同的人。如此一来,宇宙论与人生论的信念,就和派别的壮大或消长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分别成了两个巨大的思想派别,一个是“程朱派”,另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 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 讲给普通大众的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1.这套中国历史,作者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套专注“讲透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也不只是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还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历史运作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2.这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中国通史。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50年来,有无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却被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永远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3.一套当代学者讲给今天普通读者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套从史前时代讲到清代结束的通史,它没有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的中国史那么学术,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那么戏说;这套中国史用既正儿八经、又简洁愉悦地方式,讲出了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就像《秦谜》《历史的温度》那样讲述有情感、有思想的历史。 4.这套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新”。 作者说,“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它吸收了专家学者的严肃认真,却没有学院的刻板僵硬;它采用了轻松幽默的讲解方法,却不是没有节操的搞笑和插科打诨;它主要不是讲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也不是繁琐考证一个新历史知识,而是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脉络,寻找历史运作的逻辑,启发我们新的认知。 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