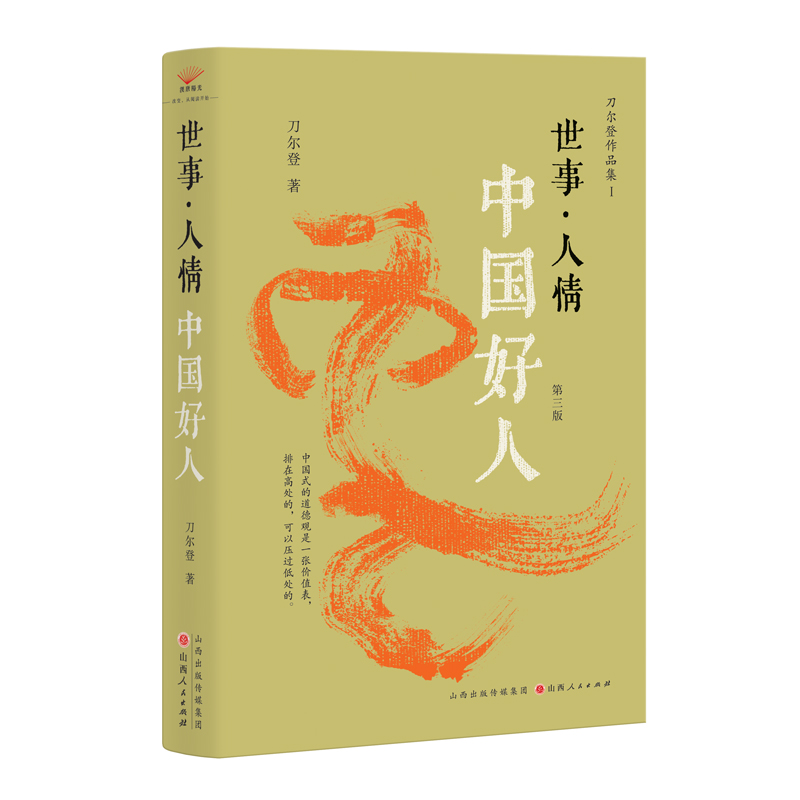
出版社: 山西人民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世事·人情:中国好人(第三版)
ISBN: 9787203134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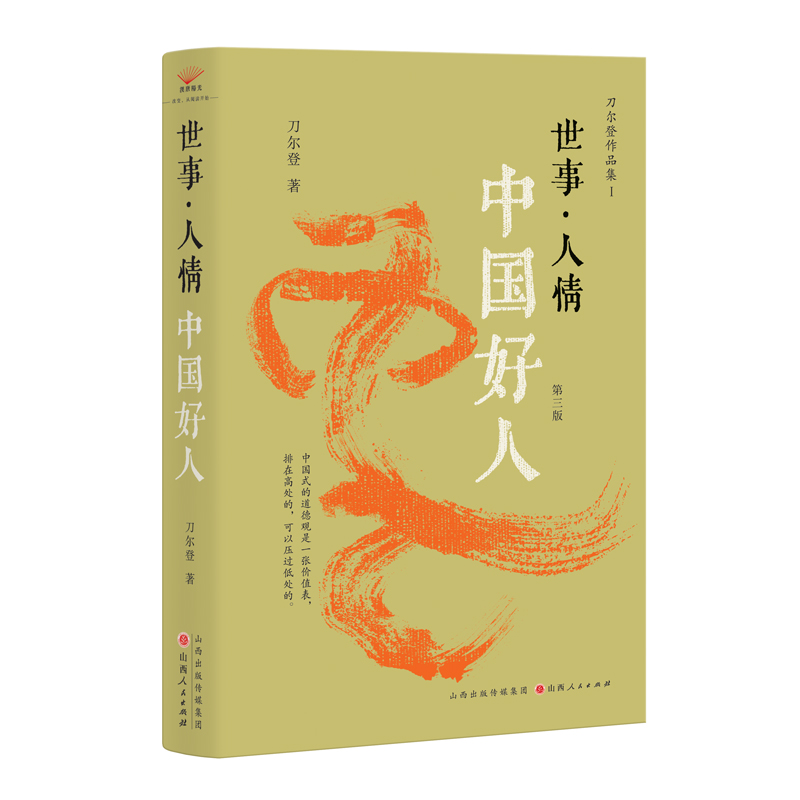
刀尔登 本名邱小刚,现定居石家庄。著有《不必读书目》《七日谈》《鸢回头》《背面》等作品。
海瑞:有女莫嫁海主事 古代名气最大的三个直臣中,汉代的汲黯可爱,宋代的包拯可畏,明代的海瑞可叹。 上回曾说到包公廉隅,令人凛凛,尚在人情之常;海瑞的性格,每有常情不能度者。当初海主事骂皇帝获罪,逮下锦衣卫狱,第一个上疏论救的,是户部司务何以尚。为这件事,何以尚挨了一百廷杖,也入诏狱,日夜拷问。若干年后,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是郎中,正是属下。二人相会,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说,若论官位,是该如此,但你我当年一场交情,就不能以客礼相待吗?海瑞坚持不肯。何以尚大怒,拂袖而去,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辈子是不要见你了。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说到这一点,保罗·约翰森的《知识分子》,虽嫌未掩悻悻之色,还是值得推荐的。 海瑞极端厌恶乡愿。乡愿知善而不能尽从,知恶而不能尽去,与俗浮沉。说起来,普通人都有这个弱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海瑞满眼都是缺少道德勇气的乡愿,“举朝之士皆妇人”。在他自己这一方面,交战于胸中的不是善恶——善恶对他已不是问题——而是“正道与乡愿”。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协的想法,对人对己不留情面,我们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实做到了。 他曾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见她拿块饼子在吃,问起来,是家中的仆人给她的。海瑞十分愤怒,说,你是女子,怎么可以从男仆手中拿东西吃?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哭啼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刚直激烈,终始一致。但每次有人对我说起他的好,我一边同意,一边难免要想:去对他的女儿说吧。 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执法,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原来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抚应天时的事迹流传最广,不多述,只说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颠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的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 在汉代,清官每入《酷吏传》。海瑞在任上没做过什么残酷的事,虽衙门前总有枷号的人,但并不算出格,虽建议恢复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也只是说说,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尽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亲对他的控制。这位母亲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同处一室,日夜督问。 按我们的常识,被人倾注以全部心血,是很不舒服的事。不过海瑞是孝子。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过门不到一个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与一妾先后自杀。时人非议海瑞的,一是矫激,二是迂阔,第三便是“薄于闺阁”。家事不好妄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像一个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象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还记得孔子不与暴虎冯河,并厌恶果敢而窒者吗? 我本来相当厌恶《大学》里修齐治平这一套,近年渐渐觉得它不是毫无道理。修身齐家为先,治国平天下为后。没有一种借口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抛亲弃友,尽管曾有许多强人取得过相反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亲密的人,不过是些可以在必要时牺牲而又不引起非议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议,还经常为人啧啧赞叹呢。 赵苞:谁令忠孝两难全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来。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遇上鲜卑人入塞抄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汉代,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 刀尔登经典作品。 ◎ “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书中,作者将一张张忠奸分明的历史脸谱还原成一个个具有多面向的人,通过对人性、政治、文化的多层面剖析,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人,以及历史的另一维度。 ◎ “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书中,作者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品评,反思了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杀人,以及以忠压倒孝、以忠压倒仁、以大节掩盖小节的评价标准。 ◎ 刀尔登识见敏锐,角度独特,其文章值得反复品味。 ◎刀尔登的文字精炼灵动,学者缪哲曾这样赞誉:“他(刀尔登)的名词有确义,动词能使转,小品词的淡妆,更弥增其颜色;至若句式,则如顽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