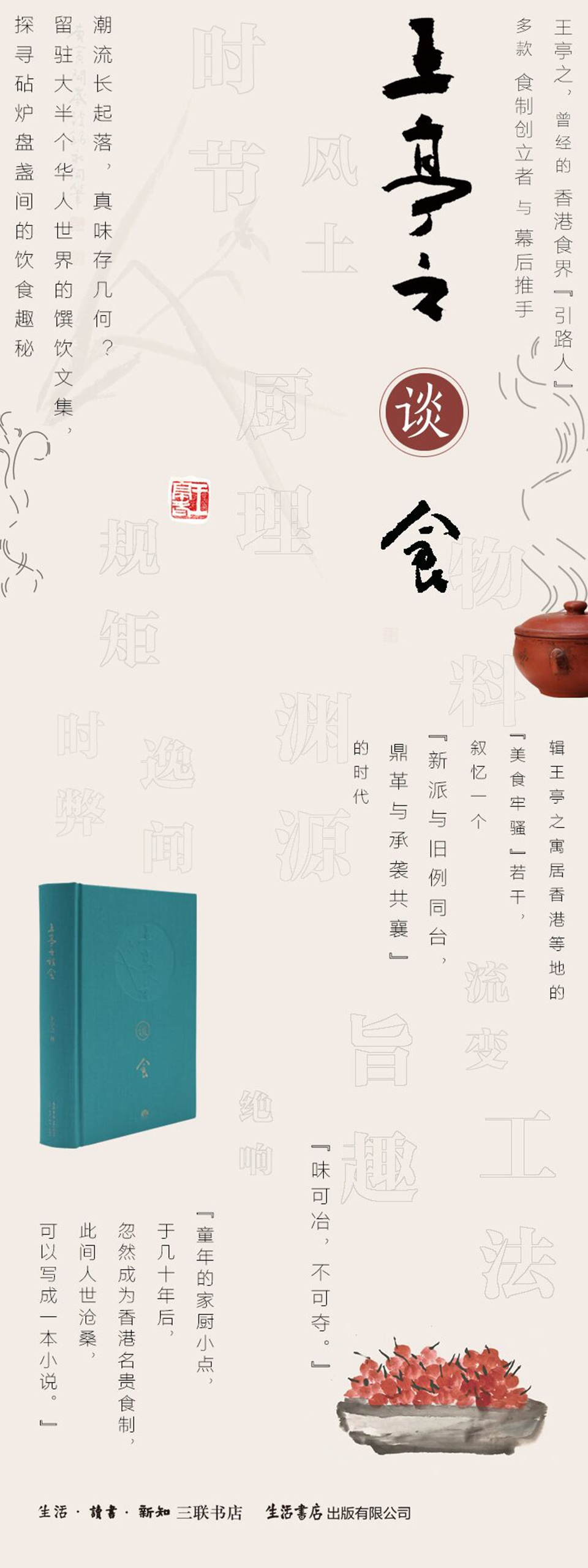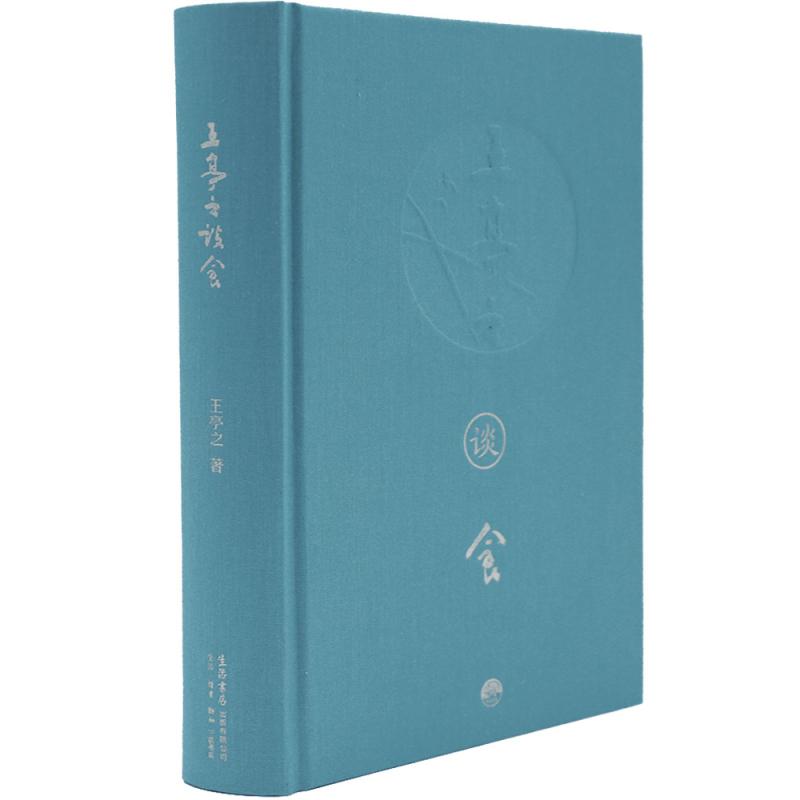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王亭之谈食
ISBN: 9787807681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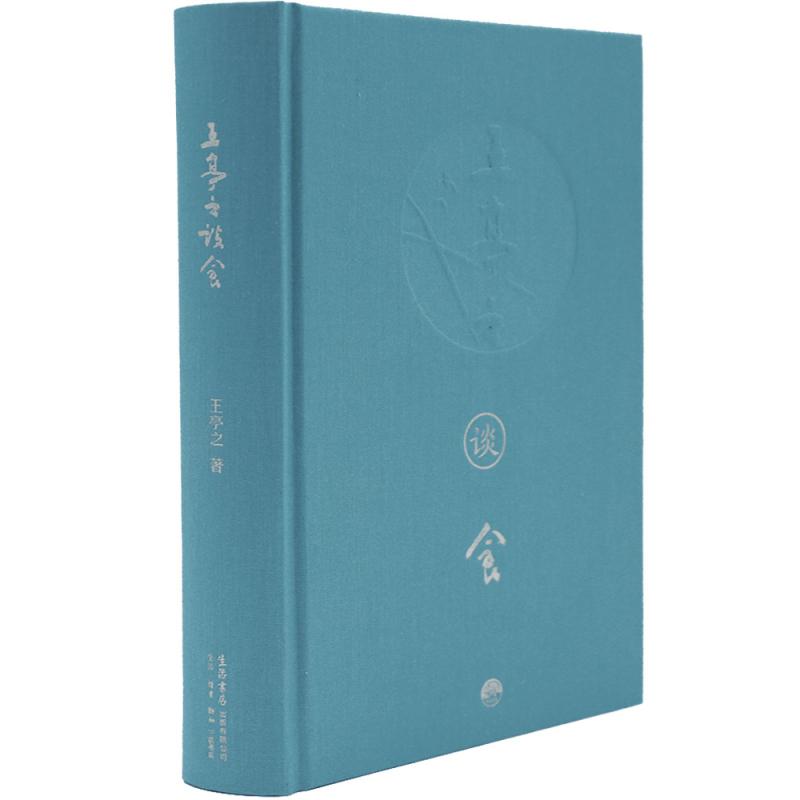
王亭之,本名谈锡永,精研佛学,编注译佛学书籍七十余种。佛学以外书籍,以“王亭之”笔名发表,取“姑妄听之”之意。出身广州驻防八旗,世家子弟,因承旧学,样样求精。世情流变,先后辗转粤港美加等地。于诸般趣好之余,亦乐馔饮研评一项。对中国传统菜系味型、食材配伍之道、厨事原理窍妙等,有独到见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数家无名香港食肆有赖其前往“试菜”时的点拨,得以扬名海内。“阿一鲍鱼”“炸奶黄包”“京酥奶皇月饼”“王亭之糖水”“XO酱”等知名食制均系其手笔。同期业余时间始撰写若干“谈食”文章,陆续登载于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及《经济日报》,忆叙旧日家传滋味,言及割烹之要,不迎时俗。惜佚散多年。今“谈食”文字重新结集,乐知者当于此一睹其妙。
秋风时节谈食蟹 一 王亭之食蟹,最不耐烦剥壳,如今的“大闸蟹”剥壳,虽出动“剥蟹钳”亦觉费力。 记忆中从前的毛蟹则并不如是,所以王亭之食蟹,照例天一半、地一半,八只脚每只只食半截,甚为暴殄天物。宁愿有人剥肉,造一味蟹羹,王亭之反而食得爽快。 但食黄油腌仔则不然,王亭之却有耐心慢慢剥食,可以食到片肉不留者也。此种心理可谓甚怪。 故从前大闸蟹当造,王亭之宁愿去食“蟹粉小笼”,虽有人恐吓王亭之曰,蟹粉都是用死蟹蒸剥而成,王亭之未之理也,但求快捷,一口一个,只要蟹肉仍然甘鲜,理得他用什么蟹来剥蟹粉。 王亭之初尝大闸蟹风味,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偶然经过蟹档,小贩叫到力竭声嘶,而买者依旧寥寥,因为广州师奶怕卖相,看见大闸蟹两只似乎粘满泥浆的生毛蟹钳,便早已敬而远之。王亭之过去问价,小贩如获救星,不答价钱,却教王亭之如何烹调。此小贩的确是内行人,居然识得教王亭之吃蟹之后饮姜茶,可以辟寒。 这一次吃蟹的印象,并不甚佳,因为蒸蟹的人蒸惯河蟹,故无论王亭之如何吩咐,依然照老办法,将大闸蟹切段来蒸,而且清洗内脏,却不知大闸蟹的肥膏不全在蟹壳,给她一洗,腹内肥膏尽去,可谓煮鹤焚琴之甚。 后来在一位地道浙江人家中吃大闸蟹,其时物资供应已经紧张,连浙醋都仅存其名而失其实,但由于火候适中,所以仍然可以在调味品恶劣的情形下,吃到一顿好蟹。 不过说实话,虽云蟹好,但王亭之却依然认为不及河蟹中的“黄油腌仔”1。这样说时,视大闸蟹如命根的人一定抗议,而且还可以举出许多“名人嗜蟹”的例,驳王亭之老土之言。只是王亭之却觉得他们一定未吃过黄油腌仔,若吃过,最少亦会认为一时瑜亮,难分伯仲,未必非尊大闸蟹为蟹霸不可。 喜吃大闸蟹者,每笑粤人治蟹必生剥然后蒸,因此走掉鲜味。王亭之听见缕分条析的分析,亦未尝不心折也,甚且自愧为粗鲁无文的粤人矣。 唯近读《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载治蟹法二则。其“煮蟹法”云──“用生姜、紫苏、桂皮、盐同煮。才火沸透便翻,再一大沸透便啖……”此即煮大闸蟹法也。 另一则“酒煮蟹法”云:“用蟹洗净,生带壳剁作两段;次擘开壳,以股剁作小块,壳亦剁作小块,脚只用向上一段, 擘开。葱、椒、纯酒,入盐少许,于砂锡器中重汤顿(炖)熟。啖之不用醋供。” 王亭之见此段甚喜,盖粤人之法,亦犹元人之法耳。 尝思之,何以吃湖蟹可以整只蒸,吃河蟹则必剁成段块,照王亭之拙见,大抵河蟹的内腔比较污秽,不剁蟹先清内腔则易染河鱼之疾。所以粤人亦非绝不识“原汁原味”之辈。 二 大闸蟹可食之处,在膏而不在肉。虽然许多师奶妙手食蟹,可以一边食一边摆,蟹食完便亦摆回一只空壳蟹,连蟹爪的肉都啜尽,令人叹为观止,似乎大闸蟹的肉亦非凡品,然而如此食蟹,只胜在好看,唯有一落手便啖尽肥膏的人,才算真知食味。 可比较的地方即在于此矣。大闸蟹的膏虽然甘鲜,但与黄油腌仔的黄油比,却仍未免输了一个滑字。甘鲜而滑,吃起来便有润的感觉。故王亭之常作譬喻,大闸蟹乃风韵绝佳的徐娘,而黄油腌仔则属豆蔻梢头的少女。识食蟹的人,当可领会其间的区别。 不妨说实话,目前香港人之嗜食大闸蟹成狂,其实未尝不是随声附和而已。人人都说大闸蟹好食,寻且推之为蟹中的贵族,于是乎便有压力,令到感受不外如是的人亦不敢开声,以免被人讥为土佬。亦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许多人不相信自己舌头的味蕾,宁愿相信别人的称赏,而自己亦极口称赏之,这种食客,应该占半数以上。 此外还有一重缘故,便是真正的黄油腌仔实在难求。王亭之求过一位蟹王,其人在一笼蟹中只拣到三只正货,居然还说幸运,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乎就连移地饲养的所谓大闸蟹亦出尽风头,而黄油腌仔则依然籍籍无闻。甚矣哉,宣传之重要也。 三 饲养大闸蟹,在近年实属生意眼。假如用化学品去养,那么野生大闸蟹一定不足供应,盖嗜之者,除了香港一群蟹狂之外,还有专程由台湾来香港食蟹的台湾师奶。王亭之食蟹,两只为限,这些师奶啖七八只盖属常事,就算将入口数目乘四,相信亦非将蟹种吃尽不可,更何况乘七乘八以到乘十耶。 养蟹的缺点,即使不论那些药物的遗害,以蟹论蟹,蟹肉的鲜味亦大逊于野生。王亭之起初对此点亦懵然不觉,后来偶然吃过一次正货,然后才回忆起从前的蟹味与如今的蟹味,二者果然有点差别,是则所谓一蟹不如一蟹耳。不信的话,不妨同时食一只养蟹,一只正蟹,便知养者实在欠鲜。此亦犹之乎海斑与养斑之别,只能用舌头的味蕾作证,很难用笔墨来形容。 四 烹治大闸蟹,其实绝对不难。名店将大闸蟹抬高价格出卖,只卖拣蟹的工夫,绝不在于烹调。怎样蒸,一次蒸不好,蒸两三次还怕蒸不好耶。甚至调味之道,亦手板眼见功夫1。然而今人这种食蟹之法,在元代已见有文献著录。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便教人怎样蒸蟹食蟹。由元代至今,几乎八个世纪,而食法依然不变,足证天然胜于整治,化浓妆食大闸蟹的女人,于食蟹时最宜体会此意。假如认为化妆好,则不妨将大闸蟹用豉椒来炒也。一笑。 吃蟹必须稍饮酒,通常是饮“加饭”。然而这种酒的毛病是太甜。所以王亭之尝开倪老二阿匡的玩笑,赠其一联云── 文章甜俗如加饭 人品咸酸似减兰 “减兰”即是“减字木兰花”,此调多情词,王亭之故乃谓倪匡为“咸酸”,实谤之耳。然而“加饭”却其实不好,试过有一次,略饮“桂花陈酒”,风味似乎稍胜。但王亭之却不敢以此作为定论,因为王亭之不识品酒,不敢冒充内行。 吃蟹之后,例饮山楂茶或姜茶,则以姜茶为胜,元人已然如此。片糖冲姜茶,滚热而饮,饮后便有一道热气,由喉头一直暖至丹田。若不够热,便难有此暖意。若承暖意,懒洋洋挨在沙发上,与三五知己清谈误国一番,盖乃人生最大享受。 所以王亭之很希望有这样的一次“蟹局”,找一家花园的楼馆(其为澳门的卢九花园耶?)在园中烹蟹,既蒸大闸蟹,亦蒸黄油腌仔;既饮“加饭”,亦饮“桂花陈酒”。四周乃菊花与洋兰,加上一两株丹桂与金桂,三五知己闲坐其间,美人侍座,素手调醯,戒谈政治,亦不许臧否人物,则此间乐,乐不思经济危机矣,只谁人有条件做此东道主耶。 注释 1 “黄油腌仔”是广府人专称一种河蟹的土语,因为蟹身不大,是故称之为“仔”。凡物小者,广府话都称为“仔”。 2 粤俗语,只望一眼,手便能跟着做的功夫,形容其简单,甚至粗陋。 3 倪匡与王亭之同年,可惜迟一个月出生,所以唯有称王亭之为王老大,王亭之则称他为倪小二,他亦无可如何,纵然自大,亦无法改变生朝,倪小二以此为一生憾事。 ? 王亭之,香港“食神”级人物,食界引路人之一,多款食制的创立者及幕后推手。 ? 《王亭之谈食》,一部写在传统饮食文化潮起潮落时代的批评小品,一述中餐饮食砧炉盘盏间的趣秘。 ? 文笔风趣,且见性情。劝诫垂范,以期渊雅。 ? 与金庸、倪匡等同席而谈,面向读者“敢述真言”,与厨人相知相谊。 ? 身世经历皆不寻常,一路行过大半个华人世界,独特的饮食见解与感悟一书而尽、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