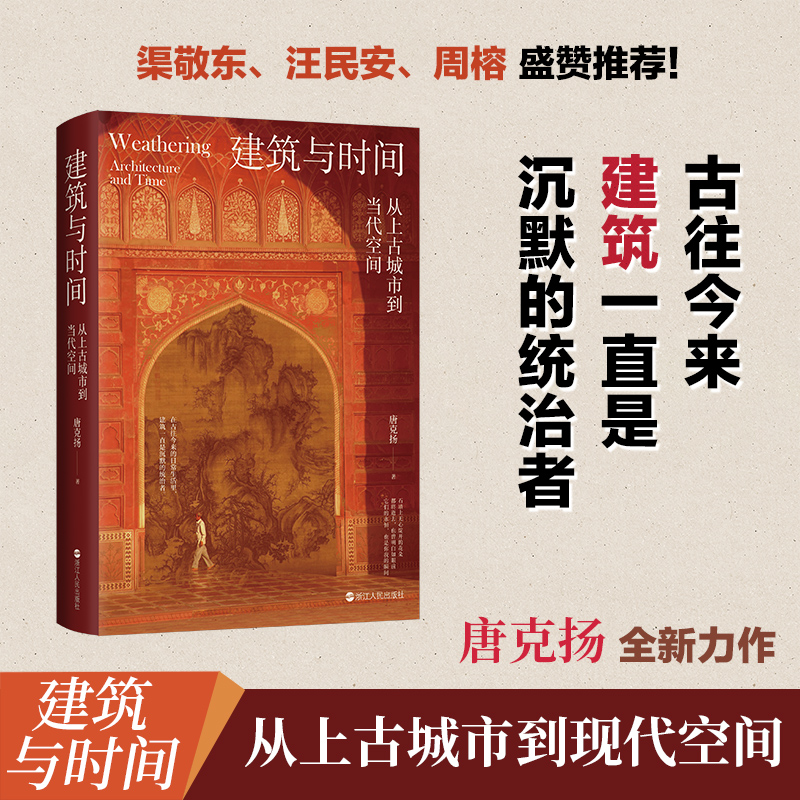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6.80
折扣购买: 建筑与时间:从上古城市到当代空间
ISBN: 9787213112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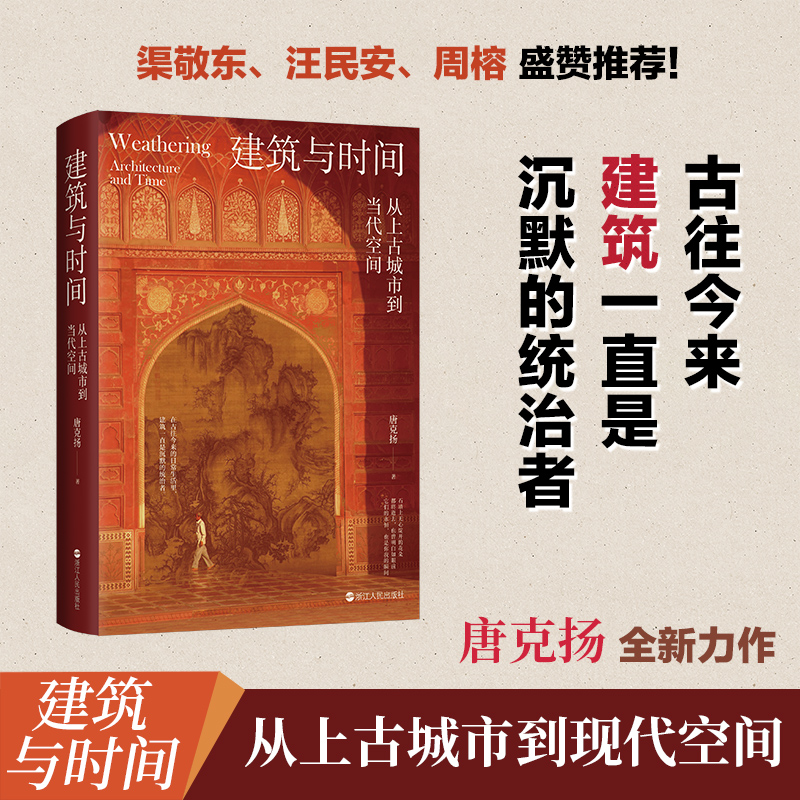
在世人看来,建筑是反时间的,一成不变。当代城市中有太多这样的建筑,拒绝融入城市肌理,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意图成为自己的纪念碑。本书作者认为,时空并不可分,个体只有将本真的生活经验映照其上,才能真正进入逝去的建构的世界。 本书含引言与后记,共21篇文章,以时间为标题与线索,串联成整体。作者基于多年见闻通识和研究心得,将对建筑的审视与反思置于时间的语境中。书中以一个个“镜头”串起了紫禁城的墙和阿尔罕布拉宫的突角拱,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建筑奇迹和灾祸,对照现代化大都市纽约的繁华与堕落,宋徽宗的看不见的艮岳,柯布西耶将“取消一切边界”的光辉城市……无论上古的城市、近代中国的故事还是现代社会的生活,都仅是设定了各篇文章所指时间段落的开端。无论回望过去还是拭目前瞻,作者希望,一次时光漫游会让读者对身处的生活空间产生更多有益的思考。
后记 时间中的现代和人(节选) …… 和“现代”结缘也是和人结缘。我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涉及了太多无法去真正对话的人,他们生活在过去的历史里,是时间的囚徒,和我们此下的境遇并无交集。乍看起来,这和我在本书最初提出的假设有所出入,也就是说,关于建筑的叙说理所应当纠结着生命的时间,可以感知空间,也是你可以浸淫其中的活的历史。好像是生物学家施一公在一场演讲中所说:世上本没有时间,时间就是空间本身发生的变化。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似乎与施一公相反,但异曲同工:“存在”是世界在展开中成为人的舞台,没有时间的考量,就没有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写一部建筑通史几乎不可能,因为具体的上下文里,人对建筑的理解总归有限,历史上并不总是存在爱思考的“设计师”,过去有的只不过是安于本位的“工匠”。 我其实对建筑师的本位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又不得不依赖这种本位,只有把自己定位在这个特定的角度上,漫长时光中的追忆才变得可能。也就是说,“现代”加上“建筑”,在时间中思考建筑,促生了一种独特而清醒的历史意识,它使得人意识到他在世界中清晰而脆弱的地位,并且让他对此的反思变得可能,前者的意识有关空间——建筑师工作的对象,后者的反思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发生学。本书并非一本哲学著作,但着眼于“此刻”和过去的关系,它又绝不是客观严谨的说史。我们在本书中依次展开的时刻,事实上都是一个对于建筑感兴趣的写作者,在“畅想当年”。每一篇文章对应着一种认知历史的角度,有知识的同时或许也有误解,必须是也只能说当代人和专业者的“以意逆志”。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现代建筑”的那一年份,是1979年。那一年我刚刚从乡下回到城里,寄居在外婆家的大院中。我的故乡是中国南方的一座港口城市,长江航运公司所拥有的海员俱乐部大楼是我们城市里最高大的建筑之一,它让我终日里充满了好奇。因为除了它,城市里还不大看得到纯用现代技术建造的房屋,“设计”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从阿斯马拉的加油站算起,“现代”在我们这里整整晚了半个世纪。就在这一年稍早,中国建筑界的代表人物才开始谨慎地拥抱现代主义——而且,只有借着“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名义,以下的呼吁才变得可能,新的建筑文化才在接下来的10年成为现实:“实现建筑现代化,设计思想必须首先现代化”(张开济),“从建筑的艺术性来说,要能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具有充分的艺术感染力和生活气息的内外空间”(徐尚志),“建筑正在从艺术走向技术,走向技术的内面去,更明显地和艺术结合成一个整体。新技术、新功能的要求,产生了新的艺术造型”(哈雄文)。 当然,现在我知道,这是一种显然的误会。“现代”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早已来临,就连我所居住的大院也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民居。就建筑革新这样的事而言,一切是演变,而不是突变。我们大院的主体建筑,有可能和这个区域的“江西会馆”有关,那是一位在1949年左右逃离大陆的资本家的宅邸,最终演化成20多户人家聚居的杂院。我对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二层大楼的正立面上有着两根带着某种“柱式”(想起来,最有可能是富于装饰的柯林斯式) 的立柱,这绝非传统中国建筑所能具有的。此外,建筑的诸多细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比如有着宝瓶式栏杆的阳台和铁杆窗栅,和我在有过更“先进”发展历史的近代城市见到的历史建筑没什么两样。除此之外,旧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更好的观感。比如,它的屋顶依然和中国传统民居相仿,雨季时常穿漏,院子里大家生活所赖的一直还是一口水井,很久之后自来水才接到每家每户。 显然,这种感受和当时差劲的居住条件有关,以至于只要是新式建筑就一边倒地赢得人们的羡慕,小城里大部分青石板道被仓促地铺成了水泥路。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真的了解西方世界的城市,比如日本、欧美不都是社会住宅,或者,香港的廉价写字楼并非代表发达国家CBD的主流,但是从那时起,“现代”显然经有了某种具体的形式标签,这一点和建筑文化的传播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一度流行的科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若见插图,不多的对“明天”的畅想全都是那些白色的塔楼,摩天大厦的外表本身分辨不出建筑的“高级”与否。这样“高大但不高级”的建筑即使今天在北京也还保留着一部分。三线城市的天际线靠这样的愿景草率地赢得了“现代化”。 不仅仅是建筑,如今古老的中国梦想着全方位的“现代”,却没法确认这是否只是一个梦。直到今天,我们对现代建筑的观感依然停留在外表,痴迷高度(高大=高级)、贴面(材料=投资)、造型(形象=艺术)。即使专业建筑师,没来由的“酷”,毫无意义的“构成”,寡淡无味的“秩序”,何尝不也是一种空洞的外表。去除那些不必要的、奢靡的装饰,室内却是模糊不清的。 趣味因人而异,小城里即使“现代”也可以奢靡、复古、俗气,公共空间大多混乱、污浊、不便……但是,人们很少把这一切归咎于建筑设计的思想和系统,而是大多寄希望于“大师”的艺术造诣。也许,这是因为摧枯拉朽的现代建筑,并没有在所有地方都树立一种新的标准,而是留下了很多意义的空白。古老的生活并不能一夜花开。 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大生产模式只有崛起时期的美国可以媲美,起点是与巴西、印度相近的发展水平,结果却远远超过以上的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发,已经催生了数倍于实际需求的城市建筑,密密麻麻,甚至不是五颜六色可以概括。商业化的氛围,又像极了促生波菲尔的那种环境,且势头大有过之。 但是,这绝非“现代”的终结,也不是现代主义者梦想中真正理想的世界。我们将有必要,事实上也已经漫游到了各个不同的时刻里,才好反思此时此刻无法想象的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某种生活方式(民族式样、乡村建设等)总是执拗地在不同建筑运动的呼吁中复活,一而再再而三……或者,巨大灾祸的集体记忆,对个体身家命运的敏感性,如此深刻地纠结在居住文化的潜意识里。即使所托付的空间不再,类似园林那样精致的文人叙事,也可以让它们借助某种风物和实践,隔代流传。当然,宏大的官方叙事早已整齐划一,但是,每个地方毕竟会有属于自己的“大体”(地形、气候、人际关系等),或者承上启下的“情境逻辑”(曾经的租界地、历史上的集镇)。“现代”,恰好更深刻地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有限和走出自身的必要。 这种“超现代”的反思,并非仅仅局限在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也不止于中国经验。通过阅读和思考,可以完成一种特殊的时空穿越,比如去往异域的古城、特殊的戏剧化的场景……重要的是激发共同的人性经验,就像一部电影那样,使人回到似曾相识的世界。陌生的未必一定就不能让人心会,恰恰是因为熟悉而厌倦,使你渴望一种崭新的经验。即使远离生物学意义上的“故乡”,那些遥远的空间,也有可能使你获得如同家园般的安顿感。 就像一场梦。再准确些,运思于不同时间的建筑中是让你履及“梦境”。带一个“境”字,就不是简简单单地沉入仙乡:一个从此刻辗转而去的地方,也可能是当下时髦的虚拟世界,超越个别,如天边虹霓,似乎比身边的一切更让人神往,但是毕竟还托付在具体的结构和空间经验上。人们都有“最初”,回归“自然”,就好像婴儿回到宇宙般浩渺的生命起点,事实上是回到了自己,是全部的生命。 不管梦有几重,我要强调的,还是我们自己正是从“现代”出发的。正是生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有幸亲历了一段由前现代的条件转往“超现代”的旅途,在这种复杂而真实的生命中,未来、过去和现实才充分融汇,衔接“古老”和“新”的“生发的朴茂美感,那是既有的文化经验转向新世界的过程中所萌发的某种独特感性。 什么才是“建筑与时间”?“Veni!Vedi!Vici!”(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那是在泽拉战役后恺撒写给元老院的名言,我以类似的方式回答以上的问题:没有空间,改变了的时间就已经是空间。我使用的不仅是现在时也是现在完成时,“Vixere”,是“我(他) 们来过”。 在古往今来的日常生活里, 建筑一直是沉默的统治者。 跟着著名建筑师、清华大学教授唐克扬环游世界之旅, 探访大量名胜古迹,追寻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反思遗迹的意义、文物的价值与现代的生活。 人以生生而不息,单个的人却短暂而易陨,建筑由人所打造,却可历经千万年而永存。人会越活越老,直至死亡,消失踪影,建筑等文化遗迹、空间,会磨损、风化甚至摧毁,却也会不断重生,获取新的生命与意义。 从紫禁城的墙到阿尔罕布拉宫的突角拱,永宁寺塔的光和火,纽约的夜与昼宋徽宗看不见的艮岳到柯布西耶“取消一切边界”。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关于时间,关于意图永续的生命和不时来袭的死亡的变奏。 在有限中探寻无限,在空间中追寻时间。物中残存的意念与踪迹,既在过去,也在眼前,既是瞬间,也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