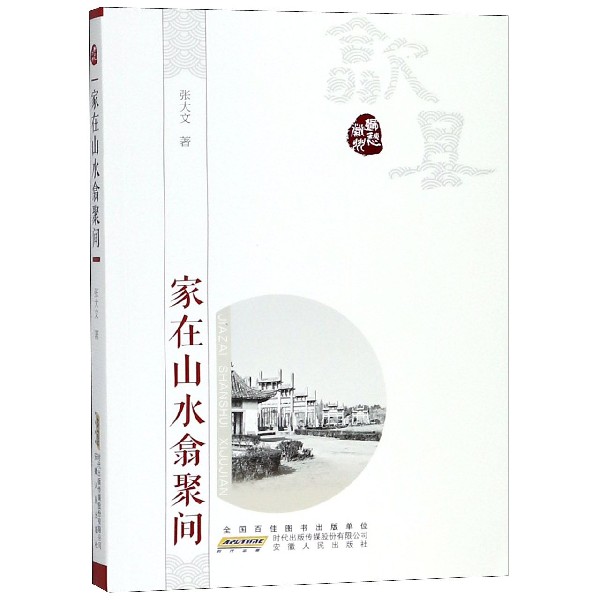
出版社: 安徽人民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家在山水翕聚间/乡愁徽州
ISBN: 9787212099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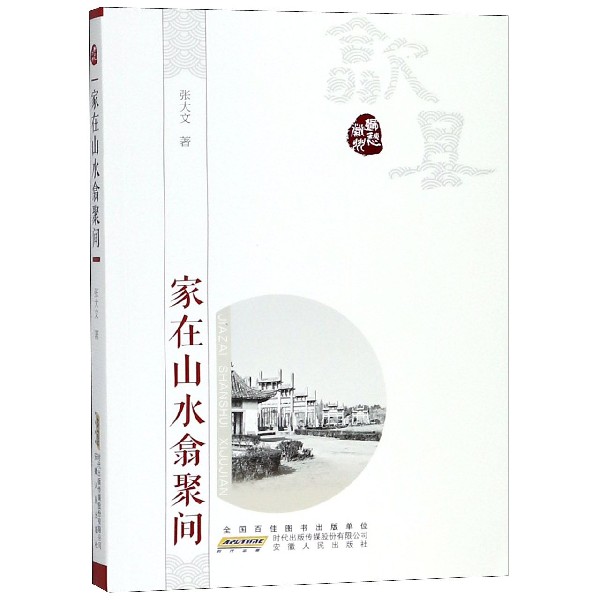
居住在新安江两岸的南乡人多少还能有“渔泽之 利”,对于居住在“源”里的人,大自然显得近乎苛 刻。“街口进街源,只见青山不见田。”纵深百里的 街源,炊烟人家相望,但都局促在山的皱褶里,或是 山的额眉之上。其他源里情形也大抵如此,山势交拥 相对舒缓些的,才在村庄的周边有零星巴掌大的水田 。赶牛犁田转身都不便,脚放直才能行走的田埂上, 也密密地种着四时的菜蔬。这里的人们便把生存的目 光投向四围的山,山势险峻高耸,多悬崖石壁,平缓 处小半辟作茶园,因为近江空气湿度过高,茶叶品质 不佳,却是这里人们一年中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多 半被垦作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地薄土坚,不利保墒 ,顺治年间编撰的《歙县志》这样描述这里的土地: “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日骤雨 过,粪壤之苗荡然矣。” 于是那种学名叫作玉米,被当地人称作“苞芦” 的植物,以坚韧质朴的禀赋,责无旁贷地做了南乡人 生活中的主角,春夏之际,南乡人家房前屋后,苞芦 顶花带露,迎风婆娑起舞。秋风一起,条条山路上男 女老少或挑或背汗流浃背,筐里篮里是清一色刚掰下 来的苞芦。在南乡人眼里,苞芦浑身是宝,“干之能 供炊,埋地可松土,苞皮可制纸,苞心可伺猪”。由 于产量低,且常年作主食,苞芦在南乡人的餐桌上精 心而又巧妙地变化着各种花样。苞芦棵是农忙时节才 能享用的食物,天色未明时各家主妇起床蒸粉做糅, 虽只就着灶膛里的火光,做出的糅却大小如一厚薄均 匀,大多以咸菜为馅,有时也用南瓜或萝卜切成细丝 。农夫匆匆吃过早饭扛着锄头晃荡着盛着糅的布囊走 向各家的山地。太阳当顶的时候,拾来几根枯枝将糅 烘焙得吱吱冒油,就着山泉,迎着山风,看远山近岭 莽莽苍苍,倒也吃得齿颊留香。冬日农闲的时候大多 以苞芦糊作早餐,煮开一锅清水,右手持擀面杖将水 顺时针搅动,左手徐徐下以苞芦粉,苞芦糊渐趋浓稠 且啪啪冒着气泡的时候,投人盐和菜叶。端着一碗苞 芦糊焙着火熄坐在自家门口,冬阳如巨大的火球正跃 出那边山岗,一种温暖便从心底徐徐升腾起来…… 南乡人说:“纵有良田万亩,不如一技在手”, 又说“卖田卖地卖不掉手艺”。他们认为,田地不仅 金贵不易得,而且还有丰歉之时,只有学成一门手艺 ,方可消除衣食之忧。小时耳濡目染,我总是对家乡 那些手艺人精湛的技艺和他们近乎传奇的故事心驰神 往。四邻八乡有人家建造新屋,常常来南乡请了石匠 去下基脚。各形石料经南乡石匠们三錾五錾,立马横 平竖直,棱角分明。无论基脚下多高,石匠们全用石 块沟连铺垫,从不用水泥沙浆黏合。新屋落成之日, 主人设宴犒劳众工匠师傅,砖匠、木匠、漆匠等齐齐 人座,主宾的位置必定是留给石匠的。上天为造就南 乡的石匠特意在这里搭了个大舞台。这里的山多岩石 裸露,为了耕作的便利只能砌起层层的梯田,从山底 到山顶上百道丈余高的石螃气势磅礴,道道都是石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