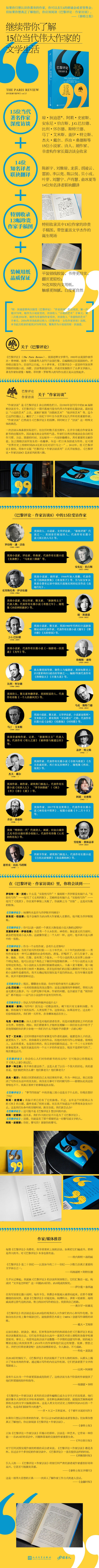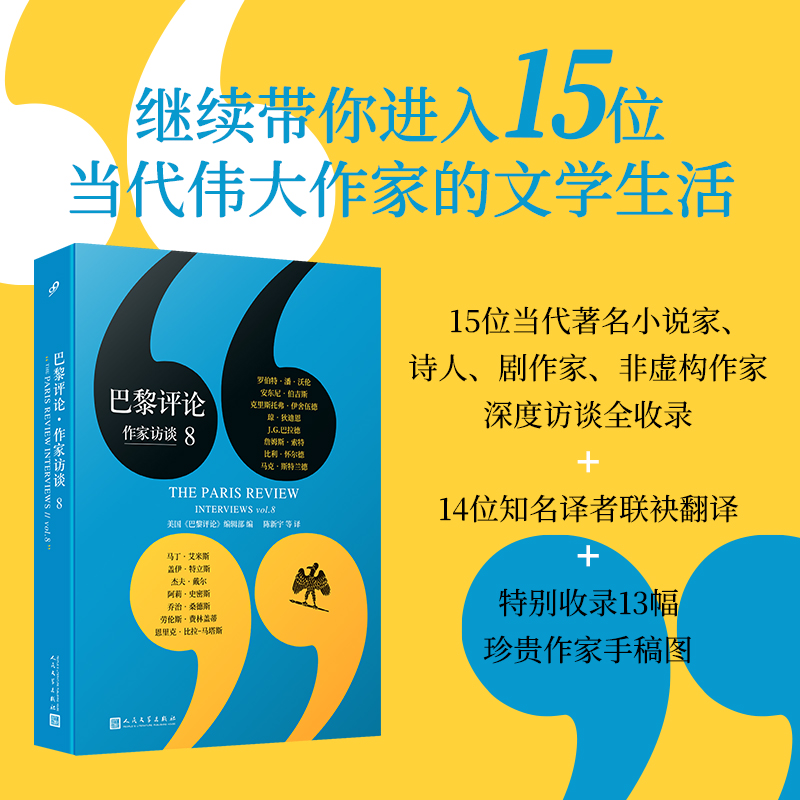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43.50
折扣购买: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8
ISBN: 9787020187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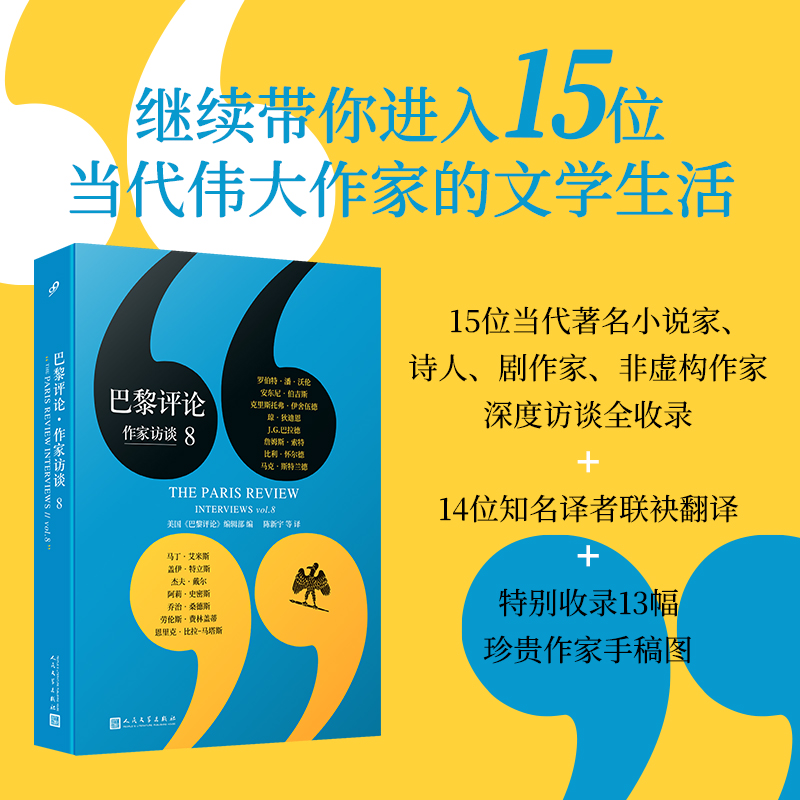
《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美国老牌文学季刊,1953年由美国作家乔治?普林普顿、彼得?马修森等人创刊于法国巴黎,后编辑部迁回美国纽约,并持续出版至今。自创刊之日起,六十多年来,《巴黎评论》一直坚持刊发世界顶级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并成功发掘推介了众多文学新人,著名作家如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等人的写作生涯正是从这里起步。 “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后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400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成稿,往往历时数月甚至数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阅读偏好、困惑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罗伯特·潘·沃伦 罗伯特·潘·沃伦:什么是“实验性写作”?詹姆斯·乔伊斯没有搞什么“实验性写作”——他写了《尤利西斯》。艾略特没有搞什么“实验性写作”——他写了《荒原》。你在某件事情上失败了,你就称之为“实验”,这是对失败的粉饰。 安东尼·伯吉斯 《巴黎评论》:你的专业书评人身份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帮助还是有妨碍? 安东尼·伯吉斯:没有坏处。它并没有妨碍我写小说,反而提供了便利。它迫使我进入那些我不会主动进入的领域。它还能支付账单,而小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巴黎评论》:你选择像乔伊斯这样的巨匠作为你的文学偶像,同时又把自己归类为“二流作家”,你认为这是否矛盾? 伯吉斯:为什么矛盾?不过我从未真正将乔伊斯视为文学偶像。乔伊斯无法模仿,我的作品也没有模仿乔伊斯。你能从乔伊斯身上学到的只是准确使用语言。“二流作家”指约翰逊博士以及我们可怜的专栏作家们,而且约翰逊是语言的精确使用者。 《巴黎评论》:难道当代作家不模仿乔伊斯就不能使用他的某些技巧吗? 伯吉斯:只要你使用乔伊斯的技巧,你就成了乔伊斯。技巧和素材是一体的。除非你是贝多芬,否则你不可能像贝多芬那样创作。文学因禁忌而兴旺,正如艺术因技术难题而繁荣一样。 《巴黎评论》:纳博科夫是否与乔伊斯并列榜首? 伯吉斯:他不会被作为最伟大作家载入史册的。他不配为乔伊斯脱鞋。 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 《巴黎评论》:你可以谈一谈把一个真实人物变成小说人物的过程吗? 伊舍伍德:当思考一个人永恒的、神奇的、象征意义的方面时,就会把他变成小说人物。这就像你爱上一个人时一样,这时,他不再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 琼·狄迪恩 《巴黎评论》:你说过写作是一种带着敌意的行为。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琼·狄迪恩:写作之所以带着敌意,是因为你想让别人用你的方式去看,试图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人,让人看到你所看到的图景。想要如此去操纵他人的想法是带有敌意的。很多时候你想告诉别人你的梦想和噩梦。好吧,没人想听别人的梦,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没人想带着别人的梦生活。作家却总想骗读者听他们的梦。 《巴黎评论》: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会有什么劣势吗? 狄迪恩: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男性作家是有一种可以遵循的社会传统的。酒鬼、肝喝坏了。好几任妻子、战争、捕鱼、非洲、巴黎,没有第二个版本。一个写小说的男人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特定角色,他可以在这个角色之下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一个写小说的女人没有特定的角色。写小说的女人很多时候被看成病人。卡森·麦卡勒斯,简·鲍尔斯,当然也有弗兰纳里·奥康纳。甚至包括他们的出版人都倾向于把女人写的小说称作是感性的。我不太确定现在情况是不是仍然如此,但当年确实是那样,我并不喜欢那种状态。我用我面对所有事的方式面对这些。我只管好我自己的事,并不太关心外界的声音,我觉得我是秘密地在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实际上没让很多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J.G.巴拉德 我们都生活在一部巨大的小说之中,这是一部受即时性支配的电子小说。从很多角度看,时间并 不存在于六十年代,它只是一系列不断增殖的当下。时间在七十年代又回来了,却没有任何未来感。如今,时钟的指针无处可去。不过,我讨厌怀旧,这可能是因为类似的串烧也许会再次出现。另一方面,严肃地说,未来可能会很无聊。我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都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事件的世界里,想象力将消亡,或者只在精神病理学领域里表现自己。在《暴行展览》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也许精神病理学应该作为想象力的宝库,也许是想象力最后的宝库,继续存在下去。 《巴黎评论》:现在,聊聊老生常谈:你对年轻作家有什么建议吗? 巴拉德:一生的经验敦促我发出警告:还是去随便找件事做吧,带别人的金毛猎犬去散步,与一位萨克斯手私奔。作家的问题,也许就在于连“祝你好运”都不能说——运气在小说创作中没有任何作用。不会像摆弄颜料罐或雕刻工具那样会有导致意想不到收获的事故。我不认为我能说得出什么建议,真的。我一直想玩杂耍并且骑独轮车,但我敢说,假如我向杂技演员请教,他会说:“你要做的就是骑上去,然后开始踩动踏板……” 詹姆斯·索特 《巴黎评论》:有些读者抱怨你的作品过于面向男性了,而你却说,女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 索特:我认为英雄是那些肩负更艰巨的任务,毫不畏缩地面对它,而且努力生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就是这样做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写作的最终冲动是什么? 索特:写作吗?因为这一切都会消失。剩下的只有文章和诗歌,书籍,那些被写下来的东西。人类发明了书,这很幸运。如果没有它,过去的一切会彻底消失,我们将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地活在世上。 马克·斯特兰德 诗人主要不是对他的读者负责,而是对他期望使之不朽的语言负责。你想想,例如,我们需要多久才能相互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给予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多少余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予诗歌多一点耐心呢? 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自愿读诗;你必须自愿在半路遇到它——因为如果是首好诗,它便不会再往前迈一步。一首诗毕竟自有其尊严。一首诗不会求你读它;如果是那样,它就可怜了。 诗,至少是抒情诗,试图引导我们重新安置自我。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逃避自我。人们不想坐在家里思考。他们只想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就想出去寻开心。而寻开心通常并不是沉思默想。 一个诗人真正的食物是他人的诗歌,而不是烤肉饼。 我认为诗歌是基本的人类活动,必须持续。我想,当我们停止写诗或读诗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人类了。现在,我不能这样说了,因为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诗;但是我认为,诗歌是我们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从中我们可以懂得活着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从而使我们不会变成机器。这很复杂,但是我认为,正是这种语言,诗歌的语言,使得我们可辨识地成为人类。 马丁·艾米斯 讨厌和憎恶年轻作家算是写作者的通病,他要是你儿子的话,就更烦人了。另外,我仰慕我父亲的作品,而他对我的写作心存疑虑,很难投入,这在我看来,也是很自然的。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当一个二十五岁的作家拿起笔来,他其实就是在向一个五十岁的作家宣告,现在不是那样写的了,现在要这么写。 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作家呢?你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感触,把你从体验中部分抽离出来。作家的体验,从来不会是百分之百地沉浸其中,他们总是有所保留,琢磨它的意义是什么,琢磨它们搬到纸上会是什么模样。永远都会有那么一点置身事外……好像它并不真正和你相关,带着某种冷冷的中立。这种官能,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健全了。 盖伊·特立斯 我一直超然于所有人之外。现在,我在努力写我跟南的生活,我意识到在五十年的婚姻中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察者。如果我将要写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会想着怎样写这件事。我可能在打网球,但想着的是描写网球场上的景象。可以说,这是我做人的一大缺点。我从不在某处。全身心地在那里。 《巴黎评论》:你会担心人们对你的新书的反应吗?它可能会让你想起关于《邻人之妻》的记忆。 特立斯:我不再在意这些了。这是人老了以后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的意思是,他们能把我怎么着?他们算老几?他们算老几? 杰夫·戴尔 我很讨厌那些把自己太当回事的作家,作为一种抗议,我已经取消了写作在生活中的优先权。我仅在无事可干的时候写作——即便如此我还经常啥也不干。我真正喜欢干的事情是洗衣服。我喜欢一边晾衣服一边哼唱二战时的那首老歌“我们要把洗好的衣服晒在齐格菲防线上”,并在我妻子回家之前把洗好晾干的衣服叠好。她称我为“都比·达利特”,因为我还做其他低种姓人做的清洁工作。要知道,在英格兰的天气下,衣服真的很难晒干。你也许对此很难理解,毕竟你是个美国人,生活在滚筒式烘干机无处不在的国度。这事太疯狂了——在爱荷华,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几乎每天都是大晴天,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外面晾晒衣服。 阿莉·史密斯 小说是政治性的。小说不能不具有政治性。但是,如果带着政治性的目的写作,就意味着小说在政治性的同时,并不是小说本身。小说通过捏造事实,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这就是所有小说家能做的。如果你对小说提出任何小说之外的要求,小说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会不够好,行不通。 在边缘,一切皆有可能。那是对立面相遇的地方,是不同状态和元素汇聚的地方。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与时间有关。但长篇小说是关于延续的,而短篇小说总是关于故事会以多快的速度结束,这意味着短篇与死亡有着特殊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短篇小说如此着迷,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短篇小说非常非常难——因为它被塑造成这样的形式,那就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短篇小说很快就会结束,快到你感觉得到它就要结束,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结束一样。长篇小说不这么做,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长篇小说可能会涉及死亡,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关于连续事件的。 我喜欢繁复。越繁复越好。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冒险写出繁复了。为什么不呢?语言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货币。抛洒词汇在我身上吧,我想成为神话中那个被抛洒了硬币的女孩。 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被许可的时代。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不过现在谎言是公开的,在言辞上得到认可。于是形成了某种部落式的现象,也就是没有人会在乎某人是否在撒谎,因为他或她是站在我这边的。真相最终重要吗?真相当然重要。真相不是相对的,但要想让真相重新获得重要性,要想明白真相为什么重要,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天知道这种牺牲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简体中文版《巴黎评论》数字编号系列第8辑,收录传奇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对15位著名作家的独家访谈: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作者)、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作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琼?狄迪恩*、J.G.巴拉德、詹姆斯?索特(《光年》作者)、比利?怀尔德(影史第一编剧)、马克?斯特兰德、马丁?艾米斯、盖伊?特立斯(《邻人之妻》作者)、杰夫?戴尔、阿莉?史密斯、乔治?桑德斯、劳伦斯?费林盖蒂(《心灵的科尼岛》作者)、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琼·狄迪恩曾两次接受《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采访,第一次是1978年,她作为小说家受访,访谈收入“小说的艺术”子单元;第二次是2006年,她作为非虚构作家受访,访谈收入“非虚构的艺术”子单元。2006年访谈此前已收入《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出版,本书此次收录的是其1978年访谈,聚焦作为小说家的琼·狄迪恩。) ★14位知名译者联袂翻译:《巴黎评论》系列翻译采用邀约制,坚持邀请熟谙相关受访作家的译者翻译相应篇目。《巴黎评论·作家访谈8》由陈新宇、刘雅琼、龙荻、胡凌云、雷韵、李以亮、陈以侃、贝小戎、叶芽、刘慧宁、卢肖慧、俞冰夏等14位译者联袂翻译。 ★独家收录10+幅珍贵作家手稿图:本书除收录作家访谈外,还独家收录有相关受访作家的10+幅珍贵手稿图,带你重返文学杰作的诞生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