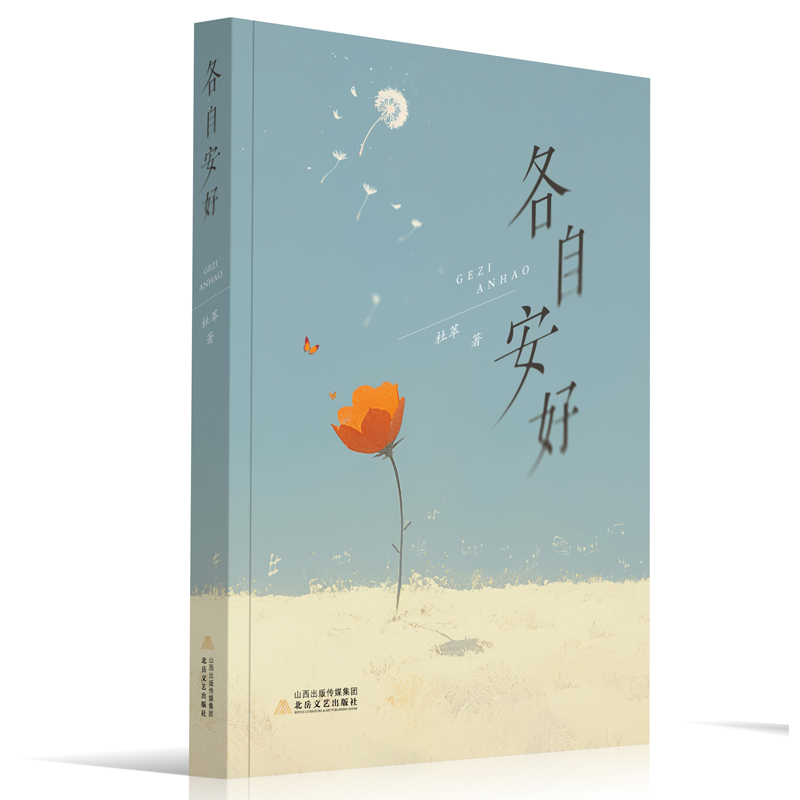
出版社: 北岳文艺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各自安好
ISBN: 9787537868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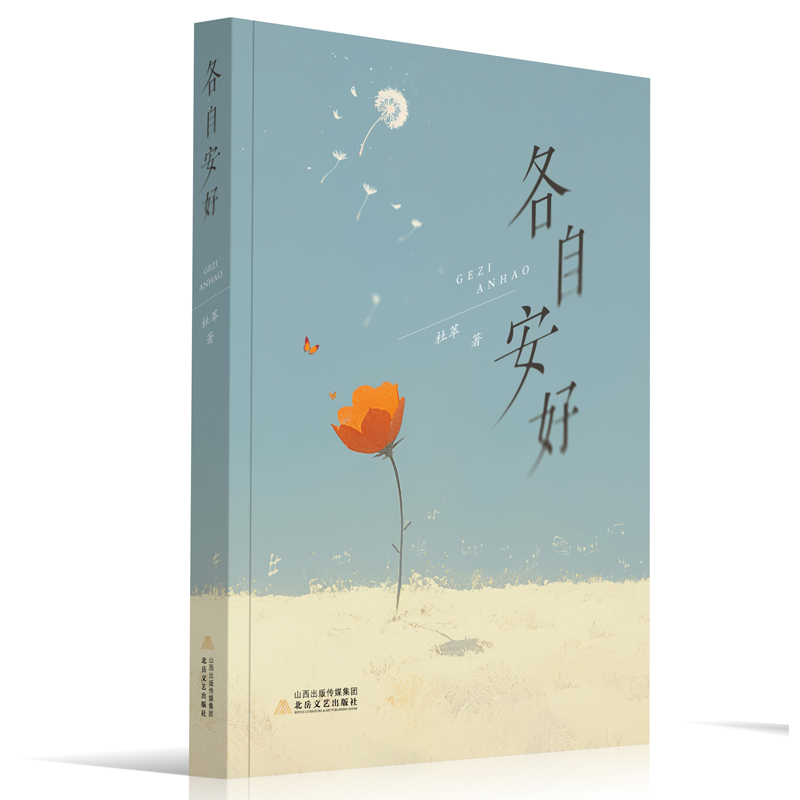
杜萃,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五级村,自幼在农村长大,深受自然与乡土的熏陶。她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生活,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四 在刘沪生走后的半年时间里,彭如月每天都是忧心忡忡的,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说话明显减少了,脸上很少再绽放属于二十岁女孩子的那种纯真灿烂的笑容。 妈妈彭听雨一遍遍劝着:“月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早就和你说过,你们是不可能的,你们的文化信仰、生活习惯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那是可以克服的,他走之前就和我说过,他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尊重我们的文化信仰。”彭如月倔强地反驳着妈妈。 “尊重是尊重,但那并不代表认同;再说了,你们隔着这么远,怎么交往呢?” 彭听雨虽然是家庭妇女,但彭家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男女,只要愿意学习,都可以去礼堂学习文化。以前,大家学些传统文化;解放后,有了专职老师,便学得多了。但女孩子学习的时间短,一般学习二三年,能够识点字,会算个加减法就可以了,回到家里也能帮忙操持家务了。 彭听雨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非常热爱学习,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在彭家庄属于有知识的女性。因此,对于彭如月与刘沪生交往的事,彭听雨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而是把问题摆出来,让彭如月自己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可以写信呀!现在通信这么方便,一个礼拜就能寄到。”彭如月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虽然她半年都没有收到刘沪生的一封信,对刘沪生的承诺难免有些疑心,但嘴上还是不愿意承认。 彭听雨怜惜地望着彭如月,不再言语。 在一个冰雪消融的中午,彭如愿从礼堂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妈妈、大姐、二姐在,但三人见了他很吃惊。一般来说,上了学的孩子中午是不回家的,庄上免费给孩子们提供午餐。彭如愿今天中午回来了,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愿儿,你怎么回来了?”彭听雨正在切菜,她放下手中的菜刀高声地问。 “你们猜。”只有十一岁的彭如愿已经很懂大人的心事了,知道全家人都在为大姐与刘沪生的事烦心,所以在礼堂里见到刘沪生寄给大姐的信后就急忙拿了信跑了回来。但出于男孩子的调皮,他想看看大姐那吃惊的神情,便没有将信直接拿出来。 “把课本落家了?”妈妈见彭如愿神态自如,知道也没有什么大事情,便轻松地问道。 “课本落家还猜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是你们都关心的事情。”彭如愿毕竟是小孩子,故弄玄虚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不就是彭如月与刘沪生的事嘛。 “刘沪生来信了?”从彭如愿进门时彭如月就往这上面猜——不对,她是每天都往这上面猜。她忽闪着眼睛,脸上有点小兴奋地叫道。 “猜对了!”彭如愿看大姐这么高兴,便也痛快地将信拿了出来。 彭如月拿到信后,就跑到别的屋子去看了,留下的三人互相对望着,眼神中难掩笑意。 刘沪生的来信,就像一颗炸弹,在彭家庄这块封闭又古老的土地上炸响了。从古至今,这里人的嫁娶对象除了本庄的,就是邻庄的,最远也不超出县城。像刘沪生这样的,不仅与彭如月相隔万水千山,而且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情况还是十分罕见的。 庄上那些平日里亲切地叫彭如月“月儿”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可不像彭如月的家人那样,更关注彭如月的意愿,他们只会一味地强调老传统,指责便不可避免了。 “平日里看着挺文静的,原来这么不懂规矩。”一天,彭如愿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家辉大爷这样说。 “月儿真的与那个上海人开始交往了?”家辉大娘问道。 “可不是嘛!最近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不是交往还能是啥?!”家辉大爷作为族长,确有掌握全庄人各种信息的便利条件。 围在彭家辉周围的一大圈人,看到彭如愿过来了,都不吱声了。 彭如愿把大家的议论告诉了家里人,彭家良也觉得是该面对这个问题了——以前只是觉得彭如月对刘沪生有点好感,但还不至于发展到谈恋爱的程度。后来,刘沪生回了上海,半年的时间里杳无音信,彭家良便觉得这事“就这么结束啦”。虽然看到彭如月那逐渐消沉的样子时有点担心,但作为父亲,他理性地觉得就这么结束是最好的。现在,看到刘沪生与彭如月书信往来逐渐频繁,彭如月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昂,他就明白了,两人已经正式交往了,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 这天晚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彭家良用略带责备的口气问道:“月儿,你和刘沪生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怎么回事儿?”彭如月对爸爸突如其来的问话有点猝不及防。 “就是问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只是普通朋友之间联系联系,还是像处对象那样正式交往啦?”彭家良对女儿的反应有点不满意,就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我们只是像普通朋友那样联系联系,只是互相介绍各自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之类的,并没有说别的。”彭如月被爸爸问得有点心虚,声音越来越低。 “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是不能随便与一个男性紧密联系的?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彭家良见彭如月显出胆怯的样子,语气便又缓和了。 “爸爸、妈妈,刘沪生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文化,他又特别尊重我,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为了这份友谊,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也请你们相信我,我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我会慎重地考虑我与刘沪生之间的关系的。”彭如月表现出了冷静与理智的一面,她用自信的眼神望着全家人。 “爸爸、妈妈,你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么落后。刘沪生来信说,上海人做饭都是用煤气。煤气管道连通千家万户,一打开煤气管道开关就能点火做饭,根本不用生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不用写信,每人一部手机,一拨手机号码就能说话了。出门就坐地铁,二十几里的路十几分钟就到了。还有很多很多先进的东西,我一下也给你们说不完。”彭如月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刘沪生给她描绘的外面世界,她不再是从前那个胆怯的小姑娘了。 自从彭家良与彭如月在那天晚上正式谈过话后,彭家良对彭如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觉得彭如月已经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能够把握自己、懂得分寸的人;自己对刘沪生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刘沪生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解的人,应该还不至于让彭如月误入歧途。 彭听雨对彭如月与刘沪生的事,以前只是单纯地怕彭如月剃头挑子一头热,到头来白白伤心一场;现在看彭如月如此理智,也就不再为彭如月操心了。 彭如花、彭如男还没有过大姐这样的感情经历,但她们看到大姐最近笑容灿烂,心情很好,便觉得这一定是一件好事。 彭如愿作为一名“信使”,看到大姐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听着大姐讲的那些新鲜事物,他也开始每天都盼着能收到刘沪生的来信,这些信也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时间在这来来回回的信件传递中飞快地流逝着,彭如愿已长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初中毕业的他,考上了县城的高中。 彭如花于年初嫁给了本村的彭新宇。彭新宇按辈分排比彭如花小一辈,但他们之间早已出了二十服,不存在什么婚嫁禁忌,便在全庄人的祝福声中顺利地完婚了。 然而庄上人最关心的并不是彭如花,而是彭如月。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彭如花的婚姻是合规合矩的,自然也必定会是幸福的;而彭如月不遵守规矩,活该得不到幸福——已是一个二十五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嫁出去。 妹妹结婚后,彭如月不怎么抛头露面了,她倒不是与刘沪生之间有了隔阂,而是不愿被那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等到胡杨树又一次变得五彩缤纷的时候,彭如月家门口出现了一辆黑色的奥迪小轿车,从车上走出来两个年轻人,正是刘沪生与他的一个朋友。 彭如月同以往一样,正在家里和妈妈一起打扫客房,忽见刘沪生出现在家门口,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话:“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啊?”刘沪生大大咧咧地说道。 “不是……是你怎么突然来了,也没告诉我一声……”彭如月有些羞涩地说道。 “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嘛!这突然造访算不算惊喜?”刘沪生眼角含笑,边说边与朋友一起从轿车的后备厢里往外搬东西。 刘沪生这次是来与彭如月订婚的。他们俩经过五年的飞鸽传情,终于从一开始的互生好感,到互相了解,再到下定决心冲破来自各自家庭的阻碍,决定要走到一起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令人生疑,漫长到令人精神几近崩溃,但两人都坚持了下来。 彭如月家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一切随刘沪生安排。只是按照规矩,远嫁的姑娘,父母是不能参加她的婚礼的。 刘沪生与他的朋友在彭家庄只待了三天,就要彭如月跟他到上海去结婚。彭如愿跟着去了,算是娘家人的代表。 尽管彭如月、彭如愿通过刘沪生的书信描述,对上海的繁华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那只存在于想象中,并且只是那种基于他们认知范围内的想象。 他们在县城见过四层高的楼房,他们知道四十层高的楼房是四层高的楼房的十倍那么高;但他们想象不到一座四十层高的楼房可以通体发光,它的实体与黄浦江中的倒影形成的那个画面有那么美。他们在县城见过大型商场,想象中上海的大型商场肯定是更大一些;但他们想象不到商场能够大到这个程度——从日常用品、衣服鞋帽到儿童乐园,就餐、娱乐无所不含,转一天也转不完——大就不说了,还哪里都是那样明亮整洁。他们也见过小汽车,想象中上海的小汽车会有很多;但他们想象不到,夜晚的道路上,小汽车的尾灯能汇成一条舞动的红色的火龙。他们自然是见过花草的,想象中上海的花草会更多一些;但他们想象不到花草会被修剪、摆放成各种图案,大气大方,美得已不像花草。 真是落后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彭如月、彭如愿初到上海,堪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哪儿哪儿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跟着刘沪生转了三天,犹如穿梭在梦幻世界中。 婚礼倒是比彭家庄的简单多了,刘家人只在晚上请了四五桌饭,婚礼就算结束了。 仪式结束后,彭如愿一个人坐火车回去了。 家乡与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让彭如愿一下子就成长起来了,他不再是那个顶着传人光环沾沾自喜的少年,他开始思考,上海并没有“传人”“传树”“祭场”“祭台”,为什么人们可以生活得那么好?家乡既然有祖先的护佑,为什么还经常忍受沙尘暴的侵袭?这里的人们为什么还过着这么落后的生活?看到父亲郑重其事地为祭祀忙活时,他心中不再有以前那种神圣的感觉了,有时甚至会觉得父亲的行为有些可笑。 见过世面的彭如愿,有了更强的了解外面世界的愿望。这个愿望也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 经过三年的努力,彭如愿考上了西部大学,他选择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他是彭家庄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五 进入大学的彭如愿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学语言文学的大部分都是女同学,像彭如愿这种身材伟岸、五官精致的男同学,实属稀缺资源,刚入学就引起了众多女同学的关注。 西部大学的女同学自然也有很多是美若天仙的,可彭如愿从小生活在三个美貌姐姐的身边,对美貌有一种审美疲劳;再加上他从小生活在偏远落后的地区,思想比较保守,对那种外向性格的女同学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时间久了,彭如愿的冷漠终于起了效果,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女同学渐渐散去了。 班上仅有的几个男同学早已被女同学“瓜分”完毕,趣味相投的他们上课都成群结队,一占座位一大片。彭如愿总是独来独往,便只能坐在没人坐的最后一排。 坐在最后一排的还有一个女同学,她也总是孤零零的没个伴。这个女同学性格很古怪,从来不与别的同学说话,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上课也没有规律,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彭如愿想,整个班上可能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甚至恐怕连老师也把她遗忘了。 这个女同学虽然长得也是肤白貌美,但她的白似乎与别的女同学的白不一样。西部女孩子们的白是透着红润的,可她似乎只是单纯的白。 莫非她不是来自西部?彭如愿对这个女同学越来越好奇,就在他下定决心要结识这个女同学的时候,这个女同学却好多天没有来上课。 人的好奇心就是这么被吊起来的。从那以后,每次走进教室,彭如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那个角落望去。不过,失望太久的彭如愿已不指望真的能看到她,好像她不在才是一种常态。半个多月后,彭如愿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再也见不到她的准备。 可事情就是这么奇妙。 下午第一节课,彭如愿带着些许睡意踩着点进入教室,只一瞥,他便睡意全无,仿佛有一个炽热的太阳,一下子就照亮了他的眼球——他看到她了。 他不再有一丝的瞌睡,径直走到了最后一排,走到了她的身边。他在她身边站定,才发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来自哪里,更不知道她为什么来上课,又为什么不来上课。那么,自己每天渴望见到她的冲动竟没有一点合理性。想到这儿,他呆住了。 见他举止奇怪,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老师也走进了教室。 “彭如愿,你有什么问题吗?”哈尼老师亲切地问道。 “老师,她……她好长时间没来上课。”彭如愿真是昏了头,这举报别人的事竟也做得出来。 “你是说爱丽丝吧?她不是咱们班的,她只是来旁听的。”哈尼老师语气轻松地说道。 教室里传出了一片笑声,就好像大家刚看了一出滑稽表演。 彭如愿也窘得红了脸,赶紧坐在了座位上——大家好像都了解爱丽丝的情况,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 下课后,坐在彭如愿前排的塔吉古丽与韩小红私语道:“怪不得不理我们呢,原来是喜欢洋妞。” 彭如愿本来是对别人的事毫不关心的,更不会留意别人的私语;但他今天却是格外敏感,塔吉古丽与韩小红的私语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赶紧看向爱丽丝,希望爱丽丝没有听到。 但很明显,爱丽丝听到了,这从他看向爱丽丝时她也向他看过来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好!她们说的可是真的?”爱丽丝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普通话问彭如愿。 彭如愿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成了自己喜欢爱丽丝了?慌乱之中,彭如愿只说出了四个字:“我不知道。” 这算什么回答!不仅爱丽丝不满意,估计连彭如愿自己也不满意。 爱丽丝以前听完哈尼老师的课就走,今天却破天荒地又听了下一节英语课。 彭如愿整节课都大气不敢出,只是不时地看着手表,希望快点下课,自己好逃脱爱丽丝那充满疑问却又有些炽热的眼神。 这哪像那个自己关注的冷冰冰的、从来不与人说话的、只躲在角落里听课的爱丽丝呢?彭如愿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喜欢这样一个爱丽丝,他觉得他对爱丽丝的种种自始至终都只是出于好奇。 彭如愿曾是那么热切地希望爱丽丝能来上课,但现在热望变成了恐慌。 回到宿舍的彭如愿想,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爱丽丝不要再来上课了。 可彭如愿没能如愿。 第二天,爱丽丝早早就到了教室,比大多数人去得都早。 彭如愿为了避免尴尬,也早早地去了教室,但他一眼就看到了爱丽丝。爱丽丝也看到了他,彭如愿无法逃避,只得硬着头皮走进了教室。 “你在逃避我吗?”爱丽丝看着彭如愿躲闪的眼神发问。 “没有……没有……这从何说起呢!”彭如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爱丽丝双眼紧紧地盯着彭如愿。 “爱丽丝,你误会了,我对你没有丝毫的了解,这喜欢二字根本就无从谈起。”彭如愿还真是慌不择言,连这样不礼貌的话都说得出口。 “可我对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爱丽丝还真是一个特别的人,搞得彭如愿都没有招架之力了。 “今天晚上八点,在图书馆门口见。”就在哈尼老师走进教室之际,爱丽丝向彭如愿发出了不容拒绝的邀请。 下课铃声响起,爱丽丝看向彭如愿,用眼神告诉彭如愿要守约,然后她就走出教室,速度之快,让彭如愿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彭如愿都在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让爱丽丝产生了误会。昨天之前,自己都没有和爱丽丝说过一句话,只是出于好奇看过她几眼,莫非就是因为自己看她的那几眼? 彭如愿为晚上的约会找到了一个很正式的理由,他也很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让爱丽丝产生误会的。 刚刚入冬,校园里树木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只有松柏与松柏下的小草还在努力地将生命的绿色呈给大地。有风吹过,将树枝上挂着的最后的枯叶吹落下来,枯叶飘飘荡荡地游弋在低处。 彭如愿如约来到了图书馆门前,见来来往往的同学那么多,便在心中埋怨起爱丽丝来:怎么把约会地点定在了这里?这里进进出出的同学这么多。 爱丽丝就像听到了彭如愿的心声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彭如愿的面前,说:“怎么,还怕找不到我?”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里人这么多,我怕……”彭如愿想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怕什么来。 “你是怕找不到我呢,还是怕别人看到你在和我约会呢?”爱丽丝说起话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与闪烁,这让不善言辞的彭如愿很为难。 “什么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对我可能有什么误会吧。”面对爱丽丝的坦率与直言,彭如愿也只能直来直往了。 图书馆门口虽然人来人往的,但大家都是静悄悄地来去,并没有高声喧哗的情况,彭如愿与爱丽丝说话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却已然引起同学们的观望了。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这里不太合适。”彭如愿环顾四周,唯恐周围有熟识的人。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位于学校西北角的一片小树林里,这里的树木以杨树为主,树木中间的小路铺满了红黄的落叶,走在上面,唰唰作响,更显出这里的静谧氛围。 “爱丽丝,我是昨天才知道你的名字的,并且这也是我对你唯一的了解。”彭如愿见爱丽丝正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 “那又怎么样呢?所谓爱情,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我一直觉得,爱情只产生于一见钟情的两人之间。”爱丽丝的中文水平还真不错,将复杂的情感问题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你是说……你对我一见钟情?”彭如愿终于理清了爱丽丝讲话的核心内容了。 “不是,是我们两人一见钟情。我对你一见钟情,你对我也一见钟情。”爱丽丝纠正着彭如愿的表述。 “爱丽丝,非常抱歉,我对你只是有点好奇。”彭如愿如实地说着自己的感受。 “好奇就是一见钟情的表现啊!”爱丽丝用肯定的眼神望着彭如愿。 彭如愿有点无话可说,只觉得自己与爱丽丝的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 爱丽丝见彭如愿眼神中带着不解,便进一步引导道:“你对别的女同学可有过好奇?” 彭如愿没有吱声,仔细回顾一下,发现自己对别的女同学还真没有产生过好奇。 “我对她们是没有产生过好奇,但那是因为你与她们不同。”话刚说完,彭如愿就发现自己掉进了爱丽丝的思维逻辑中。 爱丽丝也敏锐地感知到了彭如愿真实思维中的爱情成分,她带着些许激动说道:“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产生爱情,就是因为对方在自己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是可以使你产生好奇心的,这种好奇心驱使你勇敢地去了解他。” 爱丽丝就像一位爱情专家,滔滔不绝地阐述着她对爱情的理解。 彭如愿似乎也开始觉得爱丽丝的爱情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想起自己那独特的身份、传统的思想以及彭家庄那落后的环境,便赶紧打消了要去了解爱丽丝的想法。 “我不想了解你,你也不要了解我。”彭如愿被自卑情绪支配着。 “不好意思,我对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爱丽丝见彭如愿又想将自己束缚住,便有了些许不满。 彭如愿张了张嘴,想说话又不知该说什么。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前一段时间没有来上课。”爱丽丝用平和的眼神看着彭如愿,直到彭如愿点头示意后,才又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我去了哪里?” 彭如愿睁大了两只眼睛,他曾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爱丽丝为什么不来上课。 爱丽丝笑着看了看彭如愿,又继续说道:“我去了彭家庄,还在你家住了几天。” 这下彭如愿可激动不起来了,他满眼都是震惊、惊愕。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震惊之余的彭如愿只会说这两句话了。 “我怎么不可以,作为游客,在你家住几天,不是很正常嘛!”爱丽丝轻松地说道,完全没有理会彭如愿的惊愕。 “那你见到我家人了?”无可奈何的彭如愿只得面对现实了。 “除了你大姐,都见到了。”爱丽丝就像拉家常一样自如。 “我大姐去了上海。”彭如愿又像解释又像介绍地说着,一边还用余光小心地扫了一下爱丽丝,他想从中看出爱丽丝对他家,对他们那个地方,甚至对他们那近乎原始的信仰有什么反应。 很显然,彭如愿没达到目的,因为爱丽丝的表情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爱丽丝就像一位对一切了然于心的访客,前去造访也只是走过场。 彭如愿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夜深了,一阵风吹来,衣着单薄的爱丽丝打了个冷战。彭如愿本想上前抱住爱丽丝,给她一些温暖,但只向前走了一步就停了下来,他还是没有勇气,于是只轻轻说了句:“我们该回去了。” 突如其来的约会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彭如愿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了什么收获——好像是有收获的,知道了爱丽丝失踪的那半个月的去向,知道了爱丽丝对自己一见钟情,并且还知道了,按照爱丽丝的标准,自己对她也是一见钟情。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固执的人呢?回到宿舍后的彭如愿,想着约会时爱丽丝与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自己明明已经说了“不想了解她”,却还是被她扣上了对她“一见钟情”的帽子。彭如愿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被误会,他决定明天一定要找爱丽丝说清楚,说自己对她并没有一见钟情,并且也不想了解她。 第二天并没有哈尼老师的课,彭如愿无法联系到爱丽丝,他既没有爱丽丝的手机号码,又不知道爱丽丝是哪个班的,更不知道爱丽丝住在哪个宿舍,有些什么朋友。 晚饭过后,彭如愿像被什么指引着,径直走到了他们昨天约会的小树林。没了树叶的杨树少了几分妩媚,灰白色的树干单调而乏味,没了兴致的彭如愿刚要转身,一抹红色跳入他的眼帘,那正是爱丽丝昨天穿的红色风衣呀!彭如愿心跳加速,莫非心有灵犀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呢?”爱丽丝远远地就与彭如愿打起了招呼。 “我不知道你要来这儿,我只是随便走走。”刚才还热切地想要见到爱丽丝,并要与她说清楚自己对她并没有一见钟情的彭如愿,现在见了爱丽丝反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来我们不仅一见钟情,还心有灵犀呢!我就是来这儿等你的。”爱丽丝见彭如愿走了过来,就打趣道。 彭如愿四下里看了看,唯恐爱丽丝说的话被别人听了去,好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爱丽丝,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我对你没有一见钟情。”彭如愿非常严肃地说道,脸上似乎有些不满。 “是我不漂亮吗?”爱丽丝似乎也认真了起来。 “不是,你很漂亮,你很好,只是我不能接受你。”彭如愿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让爱丽丝明白他的心意。 “那是为什么呢?”爱丽丝的脸上有了一丝忧郁。 “是我的出身不允许我接受你。”彭如愿怕爱丽丝伤心,只得用缓和的语气说道,“我只能与我们那里的姑娘结婚,其他地方的不行;你是外国人,更不行了。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我是美国人。”爱丽丝也觉得到了该与彭如愿好好谈谈的时候了,“我们没有婚姻禁忌。” “我知道,第一次听说美国,还是从我姐夫那里。美国是个很发达的国家。”彭如愿不自觉地与爱丽丝交流了起来。 “发达是发达,但它没有历史。它就像一个加入发酵粉而快速膨胀的面包,又像一个用肥皂水吹起来的气泡,虽然看起来庞大、美丽,但禁不起时间的考验。”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打着手势,唯恐彭如愿不能理解。 “不是吧,爱丽丝?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美国的科技很先进,教育体系很完善,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去美国学习的学生。”彭如愿很少讲这么真心的话。 “是的,正如你所说,很多学生都想去美国学习。美国汇集了很多高科技人才。但你知道是什么把他们吸引过去的吗?”爱丽丝的两只大眼睛闪着理性而睿智的光芒。 “不是因为那里先进吗?!”彭如愿不假思索地说。 “那只是表象,其实吸引他们的是资本。美国的资本非常庞大,它把全世界的人、财、物都吸引到了它的周围。”爱丽丝说起来滔滔不绝。 彭如愿也从他大姐寄来的信中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昂贵的苹果手机、先进的别克汽车、花园别墅、夏威夷海滩、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一切好似都是更高级、更先进的代名词。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更高级、更先进”是怎么形成的。 “那很好啊。”彭如愿不解地看着爱丽丝。 “短时间内可以很繁荣。但你知道,资本都是逐利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靠资本吸引过来的人也是些逐利的人。当人的思维体系中只剩下了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只有利益关系了。所以,一些美国人高傲而冷漠,虚伪而自私。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美国就离衰退不远了。”爱丽丝俨然一个社会学家,能够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彭如愿第一次听到这么不可思议的观点,他无法判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只能避重就轻地说道:“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观点,但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有批判精神的人。” “可能是吧。我爸也说过,我们要做美国的鲁迅。”爱丽丝一边轻松地说着,一边慢慢向前走去。 “你爸也持有你这种观点?”彭如愿追随在爱丽丝的身后。 “准确地说,是我持有我爸的这种观点。”爱丽丝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郑重地对彭如愿说。 “你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彭如愿对爱丽丝的爸爸也产生了兴趣。 “同你们国家的鲁迅一样,也是大学教授。”爱丽丝边说边又走动起来,红色风衣掀起了小小的气流,带起了身后的落叶。夕阳西下,小树林披了一层暖光,爱丽丝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公主,走在树林中,超凡而脱俗。 与爱丽丝交流越多,彭如愿越感觉爱丽丝就像天边的云朵,就像雨后的彩虹,美丽而遥远,可他已是心向往之。 没有再说什么,两人默默地在树林中走着,直到夜深了,彭如愿早已忘了今天来小树林之前的目的是什么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这片小树林成了彭如愿与爱丽丝心灵的港湾。每天晚饭过后,二人都自觉地前往这片甜蜜的港湾。不需要事前约定,不需要语言告知,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凛冽的寒风与皑皑的白雪都无法阻止两个年轻人前去约会的脚步。 彭如愿那最难以言说的传人身份在爱丽丝眼中成了闪光点,彭如愿所描述的在祭场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爱丽丝那里成了增强凝聚力、体现人文关怀的有意义的行为。而美国却被爱丽丝评价为“虚假的繁荣”。 这是爱屋及乌吗?好像不是。爱丽丝说过,她是因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来中国学习的。爱丽丝认为越古老、越传统的文化才越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越能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难道是“爱乌及屋”了?彭如愿计划着要让爱丽丝亲眼看一看他心中认定的那些“乌”。 转眼就到了学校放寒假的时间,国际学生的圣诞假期还没有结束,爱丽丝为了能够多与彭如愿相处,圣诞假期也没有回美国。现在,国内、国际的学生都在放假,学校几乎没有什么人,彭如愿便决定让爱丽丝以游客的身份跟随他回到彭家庄。 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各自安好》《墙》等几篇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情感,以及村庄发展变迁的故事,叙事带有生活流的风格,无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冲淡、温暖而质朴。尤其是同名篇目《各自安好》描写了各色人物、不同国度、多种信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融合,传达了尊重多样文化风俗,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