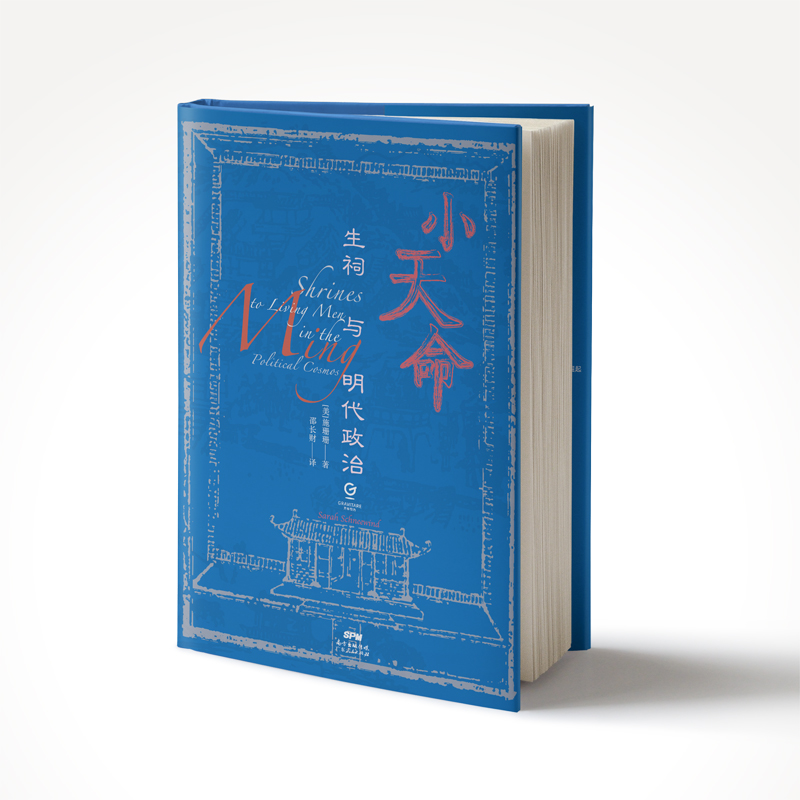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20
折扣购买: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ISBN: 978721815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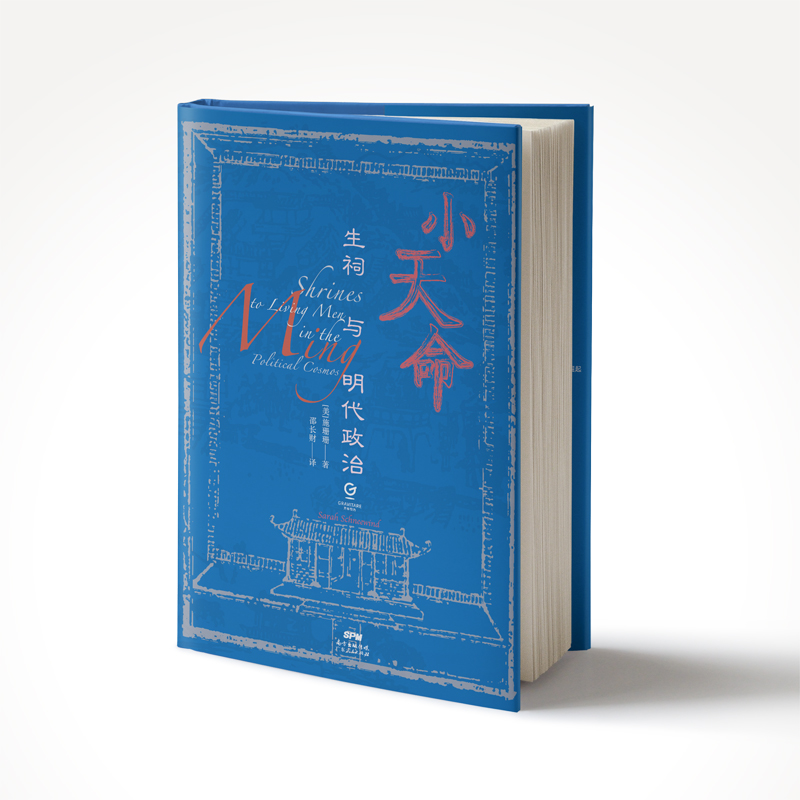
施珊珊 著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着重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曾著有《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两个西瓜的传说:明代的皇帝和大臣》《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编有《吾皇万岁!》《200年前东亚史纲》。 邵长财 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
明代的公论与平民主义 研究生祠的第五个原因在于它揭示了在专制制度与官僚体制下明代国家内发表政治言论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帝制晚期“公共领域”的研究颇为兴盛,学者们热衷于讨论当时民众自由结社、集会,对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质疑从中国历史中寻求欧洲理论结构有效性的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宗教领域及其他地方发现了与现代国家不同程度相关的合法社群。这些社群并不一定反对国家,而是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所言,“自晚明以来……在培养参与性思维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帝制晚期的“公论”是一个公认的、合法的可以讨论国家治理问题的场域—不过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当的限制。首先,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仅仅是地方性的,直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之后才正式提出了国家层面的问题。其次,它缺乏出版媒介。再次,它只代表精英人士的意见,更确切地说,只代表官员。最后,和当时的欧洲一样,它可能只意味着一种中立的事实:清朝官员陈宏谋曾认真考虑并试图遵循“公论”,但最终的结论仍是他所权衡的才是正确的。陈氏引述明代改革家吕坤的话说:“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这是一种仅限于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士人的公论。 但这一研究多以清代为中心,正如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所指出的,公共参与和政策讨论处于“极度低潮”之中。但如果我们考虑戴福士(Roger V.Des Forges)、周启荣(Chow Kai-wing)、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及其他学者所说的明代“平民主义”(populism),可能会发现颇为不同的明代政治图景。平民主义有许多方面。商业经济和科举考试促进了人员往来和社会流动,科举考试亦然。晚明士绅领导的慈善团体不仅吸纳了平民,而且明确模仿他们的组织形式。纵然少数精英依旧把持着政治言论的发表和书写,阳明心学却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他们的思想及讲学活动大大推动了平民主义在普罗大众间的传播。各类识字阶层喜欢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包括政府公报、文学剧本、歌曲小调和涉及公共事务的故事话本等。在明代,自皇帝以下,不仅能接触到廉价的书籍,还能直接接触到宗教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经由专职的灵媒—某个平民,通过扶乩的形式创造出新的经文。司徒琳(Lynn Struve)及其他学者指出,明末中国有一种“反叛精神”,表现为奴变、抗租、罢工、兵变、教乱和民变。社会流动、学社林立、哲学运动、廉价书籍、参与性宗教和阶级斗争都促成了“平民主义”的标签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流行。 在这种广泛的平民主义文化中,有明确的政治因素存在。贺凯(Charles Hucker)解释说,在明代的政治运作中,来自御史、各地官员乃至平民的上书经过相关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监察渠道上交内阁,经辅臣充分讨论后,拟出皇帝的批复。然后皇帝或者向几个大臣征询意见,或者召集更多的官员进行廷议,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理想情况下,直到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为止。按照惯例,皇帝应当执行这一致的决定。此外,明太祖还赋予几乎所有臣民上书进言的权利,以纠正弊政;在他统治后期,他还为平民提供了举报甚至逮捕官员的途径。生员(那些在县学及以上就读的学生)是唯一被剥夺进言权利的群体,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积极参与到政治讨论当中。一位学者称晚明是“一个人们希望舆论尽可能大声的时代,不管决策者是否会听到,人们普遍认为它对国家事务有积极的影响”。财富(阶级)和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任职可能性)并非总是保持一致——于是会产生富有而有权势的平民群体。除了古老而深刻(全球皆然)的对稳定的社会等级作为秩序之源的信仰之外,明代还体现了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所称的“深刻内化的平等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有时体现在轮流领导或领袖选举之中。我们绝对不能不加考证地就判定清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民众在政治上都是“传统”的,保持着“绝对臣服”的姿态。我将指出,明代的生祠为平民主义者的“公论”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焦点。公论十分重要:正如一位明代作者所解释的,就像一个人依靠“气”来维持健康一样,这是一个王朝国家(国)的原始生命力(气),使之延续了240余年。 一旦生祀话语体系发展起来,它就进入了学术与政治讨论的范畴。这是研究生祠的第六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生祀有可能成为官场上的谄媚之道,以资博取上级的赏识。对官员祖先的尊崇可能会起到同样的效果,但生祀的问题更加突出。真心纪念与阿谀奉承之间存在张力,在特定情况下的处置形成了一系列惯例。这些惯例随后以多种方式促进了对这一现象的阐述。首先,生祀现象对真挚的民众情感的关注,预示了16世纪前期阳明学派关于各阶层人民内在道德能力的论断。其次,如前所述,16世纪晚期东林党与阉党都利用并发展了生祀理论,以谋求其“主权”(米海瑞语)。最后,地方性荣誉的授予,包括生祠的建立,旨在补正官吏频繁调任的缺憾;地方希望将循吏良臣重塑为“贵族”,这一点后来发展为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主张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明代的生祀理论产生于旧思想的新语境中,通过将官员的合法性寄托于民众的认可,有助于进一步的观点论证与思想阐述。正因为它所展现的矛盾与紧张,明代的生祠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细加考察。 ? 民与官的博弈、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一部“自下而上”的明朝政治史; ? 由生祠切入,描绘专制皇权下,明朝真实而复杂的政治生态; ? 从大量碑文、方志与文集中,发掘中国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的复杂互动,展现平民的“反叛”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