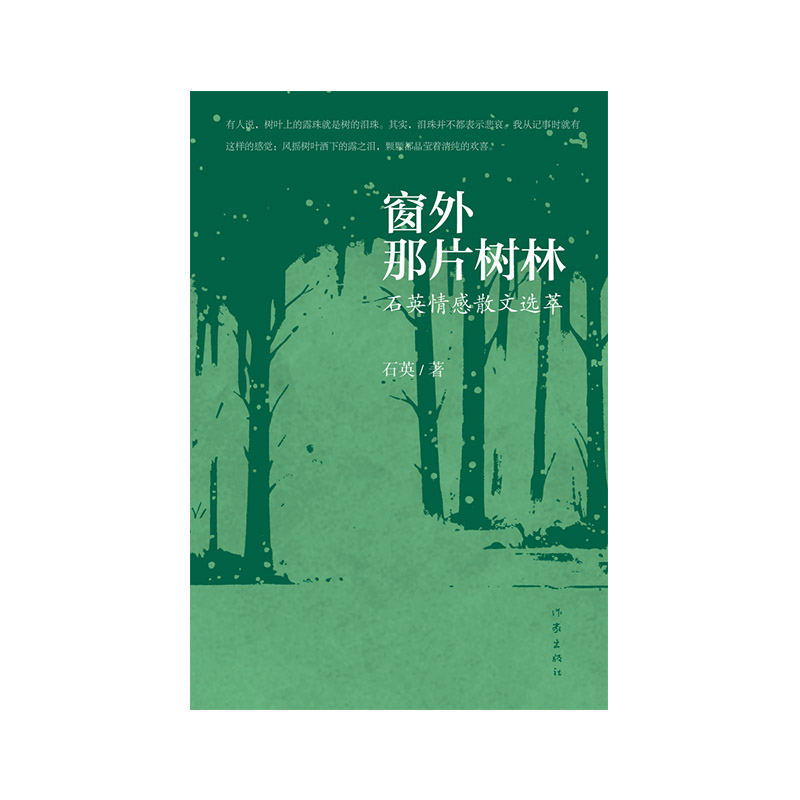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窗外那片树林:石英情感散文选萃
ISBN: 9787521226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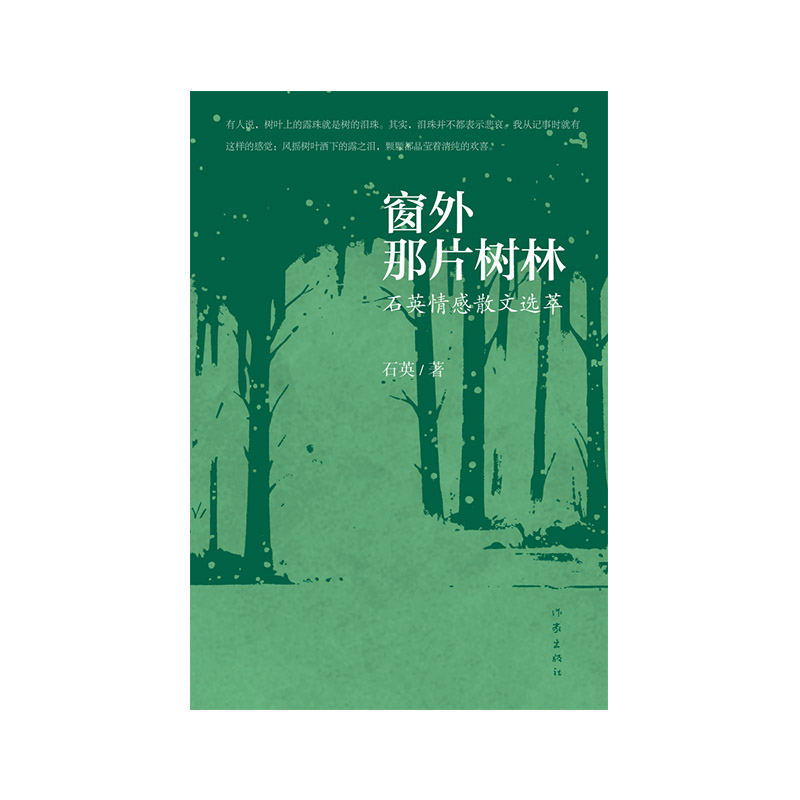
石英,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少年时(全国解放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内做机要密码电报工作,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先后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审等职,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 乡情三味 幻觉与幻听 不论我离故乡多远多近,也不论故乡对我是亲是疏,都不必过于计较。因为,有一个事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故乡是我的出生地。常听人言:离得故乡愈久,就愈是怀念故乡。我却觉得另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别离故乡太久,许多事情已淡漠了记忆。然而,唯有每当填写个人履历表时,都要清晰无误地写准原籍。作为我,就更加仔细和认真,常常在籍贯那个县级市的名目下,再加括弧里的“原×县”,以表明我出生于地道的乡村,是顶着高粱花子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不敢妄称城市人。另一方面,隐隐地也透出对生我那块土地的怀念之意。每当写这几个字儿时,那手劲就像当年在田里扶犁。也许是因为上了些年纪吧?——如今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产生出这样的幻觉和幻听。那幻觉,仿佛看见家家屋顶上都有一缕炊烟;那幻听,耳边总好像听到当年母亲唤我回家吃晚饭的声音。 其实,如今我们家乡的农户,大多已用上了煤气灶,屋顶上已没有昔日的袅袅炊烟;而我却为什么,心目中还烙印着这旧日的特征?是因为我与故乡这息息相通的有形呼吸吗,还是那梦中最易辨认的旌旗使我常常回眸?哦,我怎么能消失了那幸福的幻听呢?纵然将来我到了耄耋之年,在母亲唤我回家吃晚饭的殷殷声中也永远是一个孩子。 另一种怀念 我怀念,怀念梧桐树上的露珠。 回到故乡的第二天,我就发现家门外小河边那片梧桐树不见了。我到处打问,急切地追寻。 我问现代化的“广场”,那冠以“广场”的百货商场不语;我问实际上是住宅小区的“花园”,那名叫“清宫花园”的不语,另一处名叫“罗马花园”的也不语;我问高低参差的水泥林带,水泥林带也滞重无声,而且任凭风来雨去,这水泥林带自是纹丝不动;我问新起的“写字楼”玻璃钢屏风,它也没有回答。这时,只有空中几只翠鸟鸣叫,见附近无枝可依,向远方逸去。 尽管如此,我还是欢呼“花园”,也欢呼“广场”,惊叹我的故乡的酒店,有的也跃上“星级”。可所有这些,还是不能弥补我心中的缺憾——还是怀念那片梧桐的林带,那蒲扇般大叶上的露珠啊! 有人说,树叶上的露珠就是树的泪珠。其实,泪珠并不都表示悲哀。我从记事时就有这样的感觉:风摇树叶洒下的露之泪,颗颗都晶莹着清纯的欢喜。至少在我们这片地方,如今没了梧桐和其他传统的林带,没了叶上洒下的泪珠,我的眼眶却反而双双被润湿…… “花园”也好,“广场”也好,却不能没有绿色的生命衬托;没有足够的树的枝叶,不仅是鸟儿,就连露珠也无可附着。如果“花园”缺花,“广场”无树,不也顾此失彼,煞了些风景?! 仍然渴望春雨 我本以为,在多年来倡导不靠天吃饭,尤其是大兴水利、科学种田实施重大跨越的新世纪伊始,人们对春雨的匮乏不再过于介意,其实这只是我的想当然而将问题过于理想化。回乡几天,叔伯二舅舅就对我数落说:“老天爷真够绝的:冬天三个月只下了一场小雪;春天两个月滴雨没下,大田干得快冒烟了。” 从他的介绍中我还得知:水库耗得只剩下盆底儿;机井是不少的,但汲不了多大一会儿就得下去淘。其实天上地下水是循环往复的整体,相互赛着比心眼儿:你比我悭吝,我比你更抠门儿。谁也不能设想,天上不舍得掉一个雨点儿,地底下会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仙湖。于是,自我穿开裆裤时就在那里玩得开心的村东小河完全干涸了,老姐姐几年前还是满头的青丝也被岁月或许还有“天渴”抽走了。如今,当然没有愚昧的求雨之举,但在春雨睡懒觉的日子里,还是有不少乡亲渴盼的目光穿越新落成的十八层高楼而移向远天,下意识地数着天空的云丝……就在这时,路口的加油站生意却忒火,“富康”在前,桑塔纳2000断后。勾山集团女老板的“公爵王”擦得锃亮,与女主人的皮鞋一样显眼。她看重的是时间,急于进城与一家韩国企业谈项目,而不在意最近油价略有上调:“请快点儿,加足加够!”油,在汽车数量骤增的情势下固然可贵,而机井里抽得渐少的水波却似在悄声提醒人们:“可别忘了——春雨贵如油!”或许大自然也不想做得太过分,终于在我离乡的前两天,送来一个疏离已久的湿漉漉的早晨,急盼春雨的柳芽儿也齐刷刷地洇出一色嫩黄(我相信这可并非出于我的幻觉)。只可惜时间太短,斜风拽着细雨匆匆地想要溜走;幸而从东南山那边又涌来一片雨云,水珠在瓦檐上滴得更急了,乡亲们脸上的笑纹里堆满了挽留之意。春雨似乎也被感动了,不好意思点到为止,田野上染遍了湿褐色的柔情,村东小河里的鹅卵石变得又清又亮,我的老姐姐一时看花了眼,竟以为是欢快的青蛙们在翻筋斗。可过了一会儿,她自己也笑了:还不到那个季节呢。离乡的归途中我还在想:改造大自然当是积极的必要的举措,但合理地顺应大自然仍应是一条不败的法则。譬如当天旱时,乡亲们仍然渴盼下雨。他们大多懂得:“改造”,也只能是有利于调风顺雨,而不是任意虐待大自然。春雨,还是贵似油。 念蜀 我最早熟悉的祖国西南那块盆地的名字不是四川,而是“蜀”。 那是在山东老家,一个风雪交加的初冬,我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课桌就在靠门处,教室里炉火半睁半闭,但我仿佛忘记了寒冷,只是因为李老师在讲历史课。他是因为战争隔绝交通而暂以教书维持生计,其实他当时正在北平上大学历史系四年级,暑假回故乡而未得返校。不过,这倒是给我们这些乡村小学生带来了福祉。 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学生心目中,李老师就是最有学问的人。也真是,他讲课从不拘泥于课本,更没有什么讲稿,就是靠他口若悬河、丝丝入扣地说下去,便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讲汉末三国的纷争,使我们一会儿扼腕蹙眉,一会儿又眉开眼笑,一会儿揪着颗心,一会儿又几乎为之欢呼。现在看来,他的感情倾向与《三国演义》一样,是站在刘备尤其是诸葛亮一边的。也许是这出自于正统的观点也极大地影响了我,我对离我们家乡最遥远的西蜀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僻远之地却成了我心目中的正宗。而离我家乡最近也包括我家乡的所在地的北魏却成为我所不齿的邪恶之域——因为这大片地区是在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奸雄曹操统治之下的。 不论这种感情倾向在一个十岁孩子的头脑中是多么幼稚,但“蜀”这个字儿以至于它代表的一切对我来说却是美好的象征,而且在若干年以后,它一直是我既神秘又亲近心向往之的所在。 尽管少年参军离家,但涉足大江南北,京、津、宁、沪,后来又上大学,当编辑,直至“文革”,我也未去过巴蜀,好像也未接触过四川人。 说来很有意思,我遇到的第一个“蜀”人却是一位热心的女同志。那个年代是相互称呼同志的,故仍沿用当时称呼。有一天我正从油车车间干完活回来吃饭,记得当时穿着浑身油污的工作服,手里还提着一个大电钻。一个身量不高但匀称灵巧的女子从大门外走来,用一种带有外省口音却很动听的普通话问我:“师傅,设备科往哪儿走?” 厂子很大,我仔细告诉她顺着这条大路走到金工车间再向右拐一百米就是科室楼,设备科在二楼。她道声谢,很灵动地去了。 转天是周末,我已有三个星期没回北京家了,十分心急地想回去看看。下班后,我匆匆地乘公共汽车赶往车站。但到车站后才想起:没开进京证明信;其实说穿了也不完全是忘了,更是因为担心当时的处境碰壁开不出来。这时我急中生智,走近窗口说去保定。心想路过北京中途下车就是了,无非是白费了那一段的票程。这想法是合理的,却没料及别生故障,买保定的车票钱要多一倍有余,我衣兜里的钱还差九角,我当时尴尬极了,欲购不得,欲罢不甘,急出了一身冷汗。 “你到底是买不买?”售票员理所当然地不耐烦了。 “哎,同志,给!”一和悦清脆的女声在我身后响起。我一回头,这位女同志递给我一元钱。在短暂的惊诧之余,我意识到她是支援我买车票的。我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接了过来——票终于拿到手。 当这位女同志买了去北京的票之后,我认出她来,就是头天在厂中心大路向我打听去设备科的那一位。她那清秀的圆脸、藏青色的十分合体的的确良裤褂和半高跟黑皮鞋就是特征。虽并无多少特别,却还是有别于当地女性的。 “原来是您,昨天您到我们厂的,嗯……真是太感谢您了,不然……”由于不好意思,我话说得也不那么得体。 她好像并不甚介意,只是轻淡地笑说:“那有什么。”始终也没说明她在帮助我时是否已认出我来。 由于我们是同一车次,座位又挨着,上车后便自然攀谈起来。她说她是四川宜宾人,“文革”前考入上海的一所工科大学,“文革”中毕业,分到了重庆。她的丈夫是上海人,比她高几个年级,也分配至重庆。她丈夫业余非常喜爱音乐,因此她在天津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还为她三岁的女儿买了许多玩具。她说四川的企业中,女同志跑供销跑设备的很多,她这次来东北华北就是跑设备的,任务已接近完成,即将回去,离开重庆已近两月,很有些想家了。 这位女同志给我的印象是:热心、机灵干练而且富有情趣。当时我真诚地提出到北京后回家拿钱还她。她笑说:“不用,一块钱算啥?”我也没有执意坚持,不然反而显得小气了。 在北京下车分手之后,当然就是永远的分别,那一元钱始终也没有还人家。此后若干年,我一直把这位女同志的印象视为对四川女性的总体印象。而且心存一种感激,这不仅因为当时的一元钱其价值不同于现在的一元钱,更为可贵的是在我尚处于苦难日子里感受到美好人性的精神力量。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落实了政策,重新回到了文学界,在参加一些笔会等活动中,结识了不少四川朋友。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5年由《散文》月刊和四川作协联合举办的乐山散文笔会,我与四川文友共事中,深感他们的挚切与厚重,热情而重时效。两天的乐山笔会收获甚丰,最后一天晚上在依山傍水的碧津楼上话别,那环境那氛围就诗意浓郁,我觉得我平生未曾置身于如此佳山丽水与挚友感情交融的氛围中,当即赋下了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长短句,记得其中有几句是—— 大佛心地,峨眉姿首,肩披青衣,胸怀大度,是乐山风流…… 天静云低,二三流萤竞彩;惜未见星月,攀登无钩。 这时刻不知怎么,我想起了苏轼,想起了郭沫若,想起了名不见经传的我的小学历史教员李老师,眼前还浮现出他写的那个大大的黑板字:蜀。 人的意念有时是不连贯无界限的,可以跨越一切时空;但细想,也许或多或少都有某种联系…… 又过了几年,我与几位四川新闻界和教育界的朋友一起去九寨沟,一路上山重水复,雨雪交加不必细述,始知蜀道之难绝不限于自陕南汉中入川的金牛道,其实哪条蜀道都要历经千难万险。九寨沟胜景固然罕见,但获此真“景”也堪比唐僧取经殊为不易。归途中在平武与江油间遇雨,车轮卡在淤泥之中,进退不得,时间已近夜深,司机师傅和四位乘客一起动手抠挖车轮两侧的硬泥。但此时乌云密布,星月不见,天地间漆涂墨染,能见度极差。司机先用打火机,不料又出了故障。我想起背包里还有一盒火柴,一位年轻朋友十分节省地划着火柴为大家照明,他的额上沁出汗珠,将一绺头发粘贴在额头,但绷着脸儿,神情十分投入;借着火柴的微光,我看到另一新闻界朋友被石子划破的手,但仍不顾一切地扒、扒……这场景,这神情,我永生也不会忘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伊始的一个深夜,我真正体味到“同舟共济”的全部内涵,每个人都在为同一个目的倾全力地奉献。在川北四外没有人烟的山路上,人们忘记了饥饿,偶有大雨点儿打在嘴唇上,谁也没有顾及,谁也不分彼此,四个四川人加一个山东人……五颗心就是发动机,终于驱动了车子。 从我在历史课堂上第一次听到“蜀”之名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我脑子里建立起的“尊蜀抑魏”的倾向也许已经纠正或应该纠正,但从那时开始生成的对“天府之国”的美好感情却不妨永存,而且不致因去过几次四川而减弱。蜀之山川、蜀之文化以至蜀人,对我来说始终是一部神秘的读不尽的长卷厚书,将始终寄予美好的向往。 “女侠”洪兰 “剑侠”“侠客”这类词儿,在金庸小说中肯定是常见的,只可惜在下读金大侠的作品不多,倒是参军前在故乡时读了不少晚清和民国期间出版的公案、剑侠小说,那里面的侠客之类的人物有的也算活灵活现,至少在当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虽说那些剑侠的生活和性格很有虚幻色彩,但现实生活中我的确也遇到过具有侠肝义胆的真实人物,他们那种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和行为,给青少年时期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长达数年我个人和家庭遭受恶势力欺凌时,这种侠性人物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遏了恶徒们的凶焰;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有一簇代表光明的微火给了我相当大的安慰——在敌伪统治下暗无天日的年月中,肯定是这样的。 我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的侠性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男侠”邢广明,他比我大三岁,是我东邻家的独子。他身强力壮,话语不多,却生性爱主持正义,恶霸之类的“少爷”及帮凶们大多惧他三分,他与我一起上学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位就是“女侠”洪兰,她是本村首富的二小姐。她家主要的人丁大多在天津经商,她本来也在天津上学,只是在城市学校放寒暑假时才回家乡度假。因为我们乡村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收假,时间不一致,她才利用在乡期间,来我们小学插班听课,借以“补习”。洪兰比我大五岁,当时我十一二岁,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阴丹士林大褂,白力士鞋,戴一只发卡,面容端正白皙,时常透着一种庄严。看得出,她对恶少和帮凶们妒忌我学习成绩好、家长老实无助而百般凌辱我的行为早就怒目而视,但可能是出于“客位”不便多加干预。但邢广明告诉我,洪兰常在班主任老师甚至校长那里表达她心中的不平,揭露恶徒们的种种恶行,只是由于老师们也慑于恶少们家长的淫威而不敢正面加以管束。终于有一天,当恶少和为虎作伥的帮凶们对我进行群殴,在我的脸上抹秽物时(当时邢广明因为在家忙农活未来上学),“女侠”洪兰爆发了,她当即一拍课桌,手指恶徒们大声呵斥:“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坏,你们这样仗势欺压良善是要遭报应的!人不敢管你们,天也会管你们的!你们这样恶下去注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恶徒们在她厉声呵斥下一时有点被惊呆了,但缓过神儿来后,对洪兰污言秽语相加,一派下流嘴脸。洪兰一跺脚,大跨步地离开了课堂,我清楚地听到,她踏着深秋时节飘落的树叶,一去不回头地走了,永远地离去了…… 过了些日子,贫农户老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本村第一个秘密党员)告诉我母亲:洪兰没有回天津,而是独自去南山根据地当了女八路。 后来,八路军开过来,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不消说,我满含热泪地投身革命,欺压我的恶少们大多随家长逃至“美蒋”盘踞的青岛。我参军后,多少年也未听到“女侠”洪兰的任何讯息,直到1954年秋天我回乡探望父母,老党员老梁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洪兰所在单位,来村里了解洪兰的家庭情况,并介绍了她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她在野战军中一直担任主治军医,开始学的是内科,但她后来坚决要求做外科医生,因为她看到有太多的伤员需要救治,她要为他们做手术,救活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战胜敌人的力量。后来在实战中历练,她成为她所在那个军的“一把救命刀”,不光是抢救和医治伤员,紧要关头,这位“女侠”性子的军医也是一挺机枪、一门炮。在朝鲜战场第五次战中,由于部队日日夜夜阻击敌人,伤亡很大,一名负伤经洪兰刚刚救活过来的机枪射手在敌方炮击下牺牲,敌军趁机蜂拥而上。情急之下,洪兰端起那名烈士的机枪,突突突……敌军应声倒下一片,他们被这个猛然出现的“女共军”打蒙了。殊不知洪兰平时摸过各种枪械,入朝鲜后,轻重机枪、卡宾枪、汤姆逊冲锋枪乃至迫击炮,她都向老兵学习过,都使得挺溜。(溜,在方言土语中是“麻利熟练”的意思)洪兰和余下的战士“不要命地硬顶”,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成功地掩护了大部队安全北撤。由于在非常关头的破格表现,洪兰医生被部队领导机关特记一等功。但洪兰医生也因右臂负重伤而被同志抢下火线,并转至东北后方医院治疗。军医院在研究对她的治疗方案时,曾有过截肢的动议。洪兰得知后,苦苦恳求有关领导和大夫们尽力保住她的胳膊,她说我还要给我们的同志做手术呢。为此她竟号啕大哭起来。据说,这是她平生的两个“第一次”:一是苦苦恳求别人,一是号啕大哭。为此领导还请来了地方医院的外科“大拿”,大家集思广益,小心翼翼地保住了她的胳膊,也保住了许多生命和健康。洪兰千谢万谢拯救了她的同行。康复后,她转业到一家军工保密单位医院工作。但她一以贯之地保持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做人风格,从不表功居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在十年军旅生涯中,是一位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多次三等功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功臣。平时她除了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德技兼优之外,还自愿地加入慈善事业,在逢年过节时,给相识和不相识的贫困善良人寄点钱去。她这样做,出发点也极为朴素:我的待遇不低,多余了没用,让它多发挥点作用吧。其实她个人的生活非常节俭,人们说没见她添置过什么新衣裳。 老梁在转述时,还特别提到一桩有趣的事,这件事我乍听颇感意外:原来洪兰当年在军中虽然是正营级,待遇还可以,却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在入党问题上几度“卡壳”。1954年深秋,军工单位这次“彻底”的外调解开了这个疙瘩。当时外调人员问老梁洪兰参军前的表现。老梁的回答坚决明确:“她家庭成分是资本家,这没错。可人家上几辈就是正经的买卖人,从来没欺负过谁,一句话,没作过孽缺过德。不是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吗?那就看她本人。她年少在家乡时就很正,跟共产党、八路军有缘,说实在话,比我这个老贫农老党员的革命性儿半点也不差!”“革命性儿”,在我们老家一带,这种语言场合是带儿化的。 据说就是经过这次外调,洪兰的入党问题算是解决了。从十七八岁到将近而立之年,也算经历了十年长征。但不管怎样,终于实现了她人生的一桩夙愿。 待到我九十年代最后一次还乡时,老梁已然过世,也巧,所幸又遇到了在内蒙古与洪兰见过面的老梁的儿子。他于六十年代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去支援内蒙古建设,在一次去医院查体时,偶然碰上其父经常念叨的洪兰姑娘。洪兰当时也大感意外,她说,这是离乡二十多年来头一回遇到真正的老乡(同县还是同村的)。在交谈中,小梁告诉她:“咱们村的石恒基后来也参军了,你们不是也认识吗?”(石恒基是我原来的名字)洪兰听到这个信息显得特高兴,立马问他:“在啥地方工作?”小梁说:“好像是机要部门,具体啥单位我也不清楚。”所以尽管洪兰得知我亦参军,她并没有与我联系,那个年代又没有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类寻人途径;再说小梁说我在机要部门已足以打消洪兰主动联系的念头,像她这样性格的人,是绝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其实小梁并不清楚,其时我早已离开机要部门报考了大学,甚至已毕业到文学编辑部门工作了。 小梁说他也曾对洪兰提过她为啥不回家乡看看。一提起这点,洪兰脸色骤变,显露出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最后她还是吐了句话:“那里有我心里抹不去的痛。”小梁当时不晓,但我能够想到:在村校“补习”时那班恶少们的嘴脸和无耻行径,在她心底留下了太深的刻痕;还有由于她的仗义执言而遭到恶言秽语的辱骂,她可能还很难忘记。如确乎如此,那么在这位“侠女”开阔的胸怀中也还有一个柔弱的角落…… 在此后几年发生的“风暴”中,小梁说也有人在医院门口给洪兰贴大字报,炮轰她坚持施善行为是“假仁假义、封建余孽”等等,但洪兰从容应对,她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但那以后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小梁去医院看病,洪兰的同事告诉他,洪大夫歇病假在家。至于她的家庭子女等情况,小梁一点儿也没有涉及,是他不肯说,还是洪兰从来也未对他透露过,不得而知。 其实就在我最后这次回乡时,小梁已年届五旬,退休在家。由于他从内蒙古回来也有数年,我估计他对洪兰的情况也不见得详知。但当我问起时,他欲吐又止,最后他对我讲了实话:最近与内蒙古那边的老朋友通电话,他们有的说洪大夫已经走了,小梁解释说:“因为我怕传言不准,所以刚才没有对你说。”我觉得不是不说,而是像洪兰这样难得的大好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走了…… 她这年应该是七十岁,如“是”的话,未免也太匆促了。 自从她走后,几十年间始终未见一面,这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但她作为“侠女”的形象,绝不会因此而磨灭。而且,正因有此人真实存在过,我则坚定不移地认为世上确有侠性人物。" "★“文学常青树”、“多栖作家”、新时期散文的领路人石英的情感散文选萃。 ★岁月积淀的智慧与情感,阅历丈量的风光与景色,在真挚的书写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