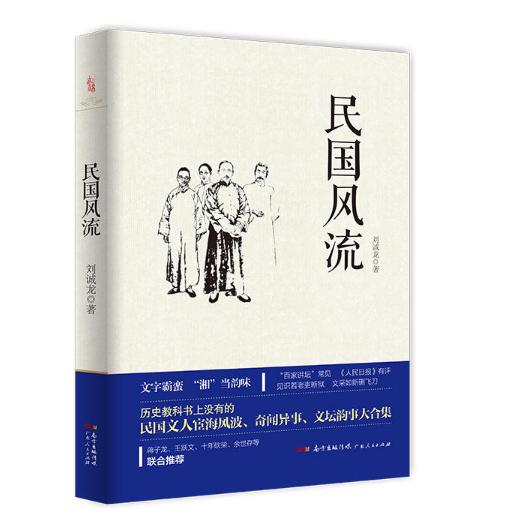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40
折扣购买: 民国风流
ISBN: 9787218113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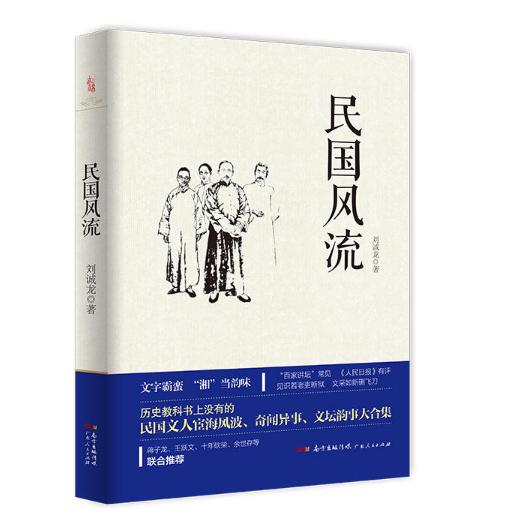
刘诚龙,年龄冇老冇少,到中年;身份非士非仕,公务员;处境不尴不尬,靠边缘;面目无*无派,自个玩;文体难解难分,乱成篇。自1990年在《湖南*报》发表散文以来,至今已在《人民*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散文》《书屋》《天涯》《四川文学》《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30个省市280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随笔3000来篇,数百篇作品曾被《读者》等100多家文摘报刊转载,有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新编教材》,100多篇杂文、随笔、散文入选各版本年选,出版散文杂文集《腊月风景》《暗权力》《暗权术》《暗**》《恋爱是件奴才活》《**弱音》《谁解茶中味》与《历史有戏》《回家地图》《心心点灯》等。
当年武大没教授 苏雪林本来是在安徽大学当教授的,月薪两百元,名号好,工资高,苏雪林挺满意的,打算在这里安富乐教,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她无比伤心。当年的安大学风不太好,管理比较松弛,男生可以随意到女生宿舍去串门,经常闹到半夜还不消停。苏雪林除了教授之外还兼任女生指导员,她做事很认真,对这个风化问题很是看不惯,经常去干涉,勒令男生九点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这让男生很记恨。有天,苏雪林从外面回家,经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一块小石子飞来,打中她前额,血流如注,到医院缝了几针,在额上留下了一个终生没消的疤痕。 恰在这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往武大任教,同时被邀的还有其好友袁昌英、凌叔华,这让苏雪林有点喜出望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往武汉赶。可是,到了武汉,却碰到了一件让她觉得比那块小石子*伤心的事,校方送到府上的聘书上写的是特约讲师,在安徽大学当的是教授,到了这里却是讲师?一块小石子打在她额上,只感到身痛,现在一纸轻慢的聘书却击中心房,让她心痛。在苏雪林看来,小石子是学生打的,学生毕竟是*教育者,少不*事,不值得耿耿于怀,而这聘书却是一所大学给的,其中透露的是对她的蔑视与怠慢。 苏雪林的自尊心一直是很强的,当年她还是个文学女青年,是美女作家,在一次文人的派对中,她伸出一只手,想跟迎面走来的鲁迅先生相握,而先生只是向她微微点头,没伸手来接应,这让苏雪林怀恨在心,余生皆与先生交恶。这次武大把她给卖了,让她气愤异常,卷起铺盖又想走人。袁昌英知道后,赶紧来解释:“武汉大学为尊重**,*高职称只是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你这特约讲师,等于是别校的副教授,将来升格为副教授,等于别的大学的教授了。” 袁昌英所言不虚,在1928年就被胡适所聘担任中国公学教授的沈从文,1931年,他被聘请到武大来任教,职称跟苏雪林一样,由正教授降为讲师,连降两级;而其时名气甚大而且当了文学院院长的陈源,其职称也只是副教授。苏雪林从头数,还真发现,当年武大人文荟萃,少长咸集,还真没一个正教授。这下使苏雪林安下心来,无话可说。 苏雪林职称虽然比较低,但其薪水却不低,当年武大的讲师月薪是两百元,助教一百二十元,其薪水与在安徽大学持平,然而,苏在武大,只专心当讲师,并不兼“班主任”,工作量少了,工资未少,比较而言,她在武大的教学工资是比安大高的。 在武大这里,当教师的“利”可以给你多开,但当教师的“名”却不能给你乱戴。 “武汉大学为尊重**,*高职称只是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这可能让我们这代人很不理解,我们所谓尊重**,就是使劲地批发**,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对某大学给的教授指标越多,教师职称越高,就表示对这所学校越重视,越看重,就表示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某学校给的职称指标越少,越低,就意味着看不起这所学校,就意味着薄待知识分子。当年的武大价值观却是相反,对教授这名号卡得越紧,卡得越死,就是对这名号保持着敬畏,放得越松,放得越多,就是对这名号不当回事,就是把这名号看贱了。 在武大看来,教授是一个崇高称呼,不是市场上的小菜,也不是专卖店的帽子,不是略有点才气,略有点学识,就可以批发的。比方圣贤,两三千年来,能够戴上这名号的,只是一两人而已,教授虽然没圣贤那么尊,但也很贵的,不能甩卖。世界上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多了,也就滥了;滥了,也就贱了,其反命题是:少了,也就贵了;贵了,也就尊了。当人人都可以叫做大师的时候,把大师当瘪三来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谁还对教授、大师以及圣贤保持*基本的敬畏呢?多则滥,滥则贱。现在喊人做大师,多半用于讽刺场合了。红灯区的女子都被称为小姐,这小姐还值价吗? 额外说个事。我平时很少看新闻,偶尔看了一个新闻,说的是**学生到大陆求学,**对这些学生的学历很是“歧视”,除了有限的几所大学**承认学历之外,其他大陆大学,在**是不被认可的,粗粗一看,我还挺愤青的,**居然还歧视大陆大学,怎不让人出离愤怒呢?细细一想啊,这不是歧视,而是正视。教授如果也搞“***”,那学历当然多有注水的了。人家需要干货,**要挤一下大陆学历的水分,不也是很正常的吗?**的其他事情不好说,*少这事情,在我看来,不是政治事件,只是学术尊严话题。 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先生高文硕学,蔚为近代鸿儒。”其个性特立独行,被人目为章疯子,当然是人文学上的疯子,不是病理学上的疯子,这是一种极高的名誉。一得名高学硕,二得超拔群氓,二者必须得兼,方可获取疯子盛誉,诚如其自道曰:“大凡**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有神经病……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太炎先生是神经病,首先是因为其敢想敢说。比如说,社会爱的是尧舜,恨的是桀纣,而太炎先生却放言高论,“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他希望清**从皇帝到保长个个暴戾无比,比夏桀商纣过之;都因太炎先生反清之故,盼望清**“多行不义必自毙”“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庚子事变后,张之洞创办《楚学报》,请了梁鼎芬为“总办”,请了太炎先生当主笔。人家梁总编是清**的喉舌,谁反清他就毙谁。偏偏这太炎先生是反清斗士。这两人搞到一起,将会如何?有人分析两人前景,肯定会打架:“他*梁节庵(即梁鼎芬)与章太炎必至用武。”果然,《楚学报》**期出版,太炎先生洋洋洒洒写了六万字,字字都是“驱除鞑虏”,呈报“梁总编”审稿,梁总编气得七窍生烟,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有好事者给其记数,喊打喊杀者上百次。言喊又脚行,马上叫人备轿,往张之洞之总督府,请捕拿章太炎。张之洞也拟照办,旁有人明骂实保,说章太炎是“章疯子,即*逐出境,可也”。张氏就采纳了“驱逐”一策,领导发话了,梁总编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人家梁总编是忠臣,为清朝出了这样的逆子气愤难平,“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活活被打了一顿屁股,太炎先生对此段情节并不咬牙切齿。他*,太炎先生与人争决,有人就喊:“叫梁鼎芬来!”太炎先生都是一笑而过了。 太炎先生因为革命意志曾经十分坚定,不但与梁鼎芬之流闹翻了,而且与其老师也断*了师生关系。他师从俞曲园先生七年有余,师生情谊甚是深厚,此后太炎先生出乡梓,流*本,与其师不见者十又余年,一*归省恩师,被俞老师臭骂了一顿,话语难堪死了:“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且十分*情,要永断师生关系,说“曲园无是弟子”。惹得太炎先生生了点毛毛火,做了一篇《谢本师》,谢者,非谢谢也,乃谢*也,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弟子,那我也不认你这个老师。在太炎先生那里,师情,我所欲也;革命,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师情而取革命也。**吊诡的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周作人先生也写过一篇《谢本师》,因为太炎先生后来思想渐趋保守,引起了其时革命性很高的周作人强烈不满:“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敢自嘲者真名士也。太炎先生因反清,而****,国已非家,国这个家,已不容他了,所以,他出走*本。到了*本,他的生活曾经**困窘,常常是一连好几天都冷火冷灶,举不了火,每天买一块小麦饼过*子,穿在身上的衣服,盖在肚皮上的被子,也有三年而未洗的,“困厄如此”而“德*弥厉”,性情也不曾稍改。他与*本人山根虎次郎一起办报,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就斥诸武斗,互挥老拳。他又常常**,高呼“反革命”口号,多次差点进“局子”。一*,*本警察来查户口,叫填写调查表,太炎先生一挥而就,填的是——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太炎先生并非私生子,本来是私生子者都极力遮掩,非私生子而敢以私生子给自己头上扣粪的,太炎先生可能是千古一人吧。 鲁迅先生曾经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其实,在革命家与学问家的中间,太炎先生还做过小段时间的宦家。他与袁世凯恩怨两难忘却。袁欲***,太炎先生曾于1914年1月7*,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地来到总统府,袁明知其来者不善,拒不接见。章太炎在传达室久等不至,好不耐烦!章太炎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传达室的桌椅,打碎门窗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事件。此后袁下令对章太炎监禁,两人因大义而交恶。 其实,在此之前,太炎先生与袁世凯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他曾致书袁世凯,力陈人才之重要,袁世凯看了,高兴地答道:“至理名言,亲切有味。”还把太炎先生招致麾下,于1912年委任东北筹边使。太炎先生曾自供:“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要不得呢!”在东北筹边使“现目前的时候”,太炎先生的神经病是不是立刻好过?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太炎先生获得了这一任命,高兴地往长春走马上任了。太炎先生本色是书生,哪知道这所谓筹边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装相罢了,可是,他不太懂,上任之时,想象场面一定隆重热烈欢迎的:机场有官员列队拍巴掌,路边有小学生列队打腰鼓,晚上有文艺明星弄歌舞晚会,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惹得太炎先生大发雷霆:“本使为民国**所任命,吉林地区官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国民**。”太炎先生还真把这帽子当回事了,可是呢,吉林都督陈昭常也不抗辩,只是微微一哂。这不是自找难堪?这是王蒙先生所谓的尴尬**吧,却是没了**,只剩尴尬。 是真名士自**,可是,一入官场还会是真名士吗?一入官场谁也名士不起来,哪怕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后来脱了蟒袍,又当名士去了,敢掀袁世凯桌子了,敢砸袁世凯家的玻璃了,好!好!好!这才是真名士。 “百家讲坛”常见 《人民*报》有闻 独立评论民国** 自由书写刘氏风格 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民国文人宦海风波、奇闻异事、文坛韵事大合集 蒋子龙、王跃文、十年砍柴、余世存等联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