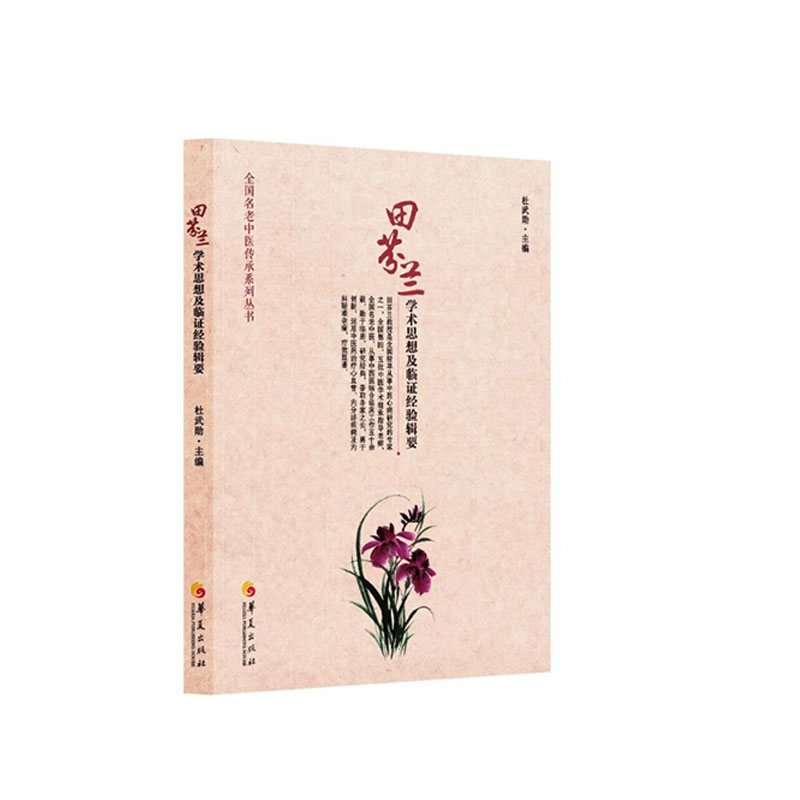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2.80
折扣购买: 田芬兰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辑要
ISBN: 9787508088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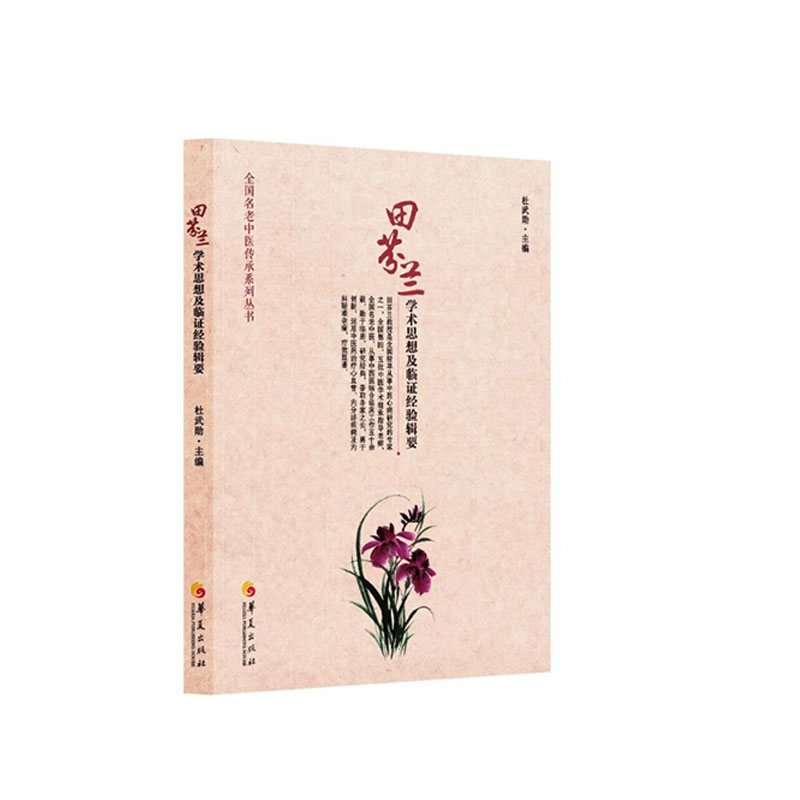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杜武勋,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先后师从全国名老中医田芬兰教授及张伯礼院士。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心病重点专科专病和中医心病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科部部长、心内科主任、中医内科学教研室主任,天津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主任。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工作。先后主研与参研“跨世纪重点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国家科技部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及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课题等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和参编著作7部。先后荣获天津中医药大学“131人才工程”青年名医、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天津市首届中青年名医、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青年首席知名专家、2011年度天津市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2012年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14年度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等荣誉称号。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抗衰老学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高血压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务理事、高血压中医临床诊疗实践指南专题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书摘(20%-30%) 第三章 学术思想概述 田芬兰教授悉心钻研中医理论和各家学术思想,潜心汲取其精华并融汇于临床实践。田教授对《脾胃论》颇有见地,在心系病证的治疗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心病从脾胃论治”的学术思想。 第一节 “心病从脾胃论治”学说 田芬兰教授对《黄帝内经》及李杲的《脾胃论》有较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并在临床中有所发展。田教授认为脾胃的盛衰直接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化和预后。在理论上,她认为脾胃是人体健康之根,乃养生之道,发病之源,治病之要,康复之本,如“内伤脾胃”,则“百病由生”,对脾胃衰败是引起各种疾病根源做了高度概括。在临证思维上,田芬兰教授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健旺,五脏可安”,明确提出“执中焦以通达四旁”的治疗思路,主张以“脾胃为中心,整体调理,治病与防病并举”,外感祛邪亦要照顾胃气,邪势既衰则应尽早恢复胃气;内伤诸病更要着眼脾胃,分主次轻重缓急,妥为调治。田教授处方用药多甘平无毒、甘淡健脾、甘润养津之品,临证治病每见处方用甘药,认为味甘入脾,甘味能存胃气,常道“有胃则生,无胃则死”,“用药则反对滥施攻伐或滞补,以免损伤胃气”。 第二节 脾统四脏,以滋化源 田芬兰教授认为“脾统四脏”理论含义有三:脾胃为气血精微生化之源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精气源于脾胃;脾胃是人体精气、气机升降出入枢纽,脾胃通过调节气机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任何疾病的成因均由脾胃调护不当而起。因此在临证中强调脾胃作用,治病崇脾,处处顾护脾胃中气,燮理中焦。 第三节 “土枢四象,一气周流”学说 田芬兰教授接受“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观点,主张运气学说应根据四时节气的实际变化,从脾胃中气角度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提倡“治病不用古方而自为家法”,这在理论和治疗上就摆脱了前人的束缚。其临证十分重视“中气”,认为“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神病则惊怯而不宁,精病则遗泄而不秘,血病则凝瘀而不流,气病则痞塞而不宣。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一旦中气升降滞塞,脾土下陷,胃土上逆,则阴阳化生乏源;胃逆则火炎金逆,神扰气滞;脾陷则水沉木陷,血瘀精滞。 田芬兰教授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田教授推崇黄元御“土枢四象,一气周流”学说,认同黄氏“脾为阴体而抱阳气,阳动则升,胃为阳体而含阴精,阴静则降”及“胃以弛阳而含阴气,有阴则降,脾以纯阴而含阳气,有阳则升”的疾病观,对于疾病也多从中气升降失调来阐释其病机,认为中气虚衰则百病丛生,临证也始终贯彻黄元御“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进而形成了其调理脾胃的学术思想。 第四节 “五脏相关,脾胃轴心”学说 在人体五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五官七窍等分别组成了五个脏腑系统。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各脏腑之间,在生理上是密切联系的,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脏腑发生病变,都会影响到整个机体,而使其他脏腑发生病理改变,脏病及脏、脏病及腑、腑病及脏、腑病及腑,产生了脏腑组织之间病变的转移变化。在生理上,以心系为例,心系内部、脏腑系统之间、心系与人体大系统之间,及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着纵横交叉的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病理上,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这就是“五脏相关”。 田芬兰教授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各有所主,又互相关涉;五脏相生相克,实为相成;五脏有可分,有不可分。脾胃居五脏之中,为升降之枢纽,脾胃有病影响他脏,他脏有病也影响脾胃,脏腑辨证尤重视脾胃。心、肝、脾、肺、肾五脏之间在生理功能上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脾居中焦,上下相连,脾与他脏并调。五脏之间,生理上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病理上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他脏有病鲜有不累及脾脏者,而脾胃有病更常患及他脏。对脾胃除了抓住脾胃本脏外,还要重视与他脏的关系,即“治脾胃安五脏”。 田教授运用脾胃学说指导心、肝、脾、肺、肾诸脏病治疗,她认为,脾胃有病影响他脏,他脏有病也影响到脾胃,在脾胃失调的基础上继发的脏腑功能失常,更加重了整体气血阴阳的失衡,导致气滞、血瘀、痰浊、水饮等病理因素的产生,是心系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田芬兰教授继承了《黄帝内经》“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之经旨,发扬李杲“脾胃论”之学说,提出以“五脏相关,脾胃为轴心,整体调理,治病与防病并举”治疗理念,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思想。 第五节 “心病从脾论治”学术思想基本构架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脾胃与心经脉相连、五行相关,在生理上和病理上都是密切相关的。 其一,经脉关系。从经脉循行来看,《灵枢·经脉》曰:“脾足太阴之脉,于大指之端……入腹属脾络胃,上隔,挟咽,……连舌本,散舌下,支者,复从胃别,上隔,注心中。”《素问·平人气象论》云:“胃之大络曰虚里,贯膈络肺,注于心前。”《素问·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仁斋直指方》云:“心之包络,与胃口相应,往往脾痛连心。”由此可知,心与脾胃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二,五行关系。脾胃属土,心属火,火为土之母,土为火之子,子病及母,二者乃母子关系,联系密切。生理情况下,脾主运化,为水谷精微化生之本,是以滋养心阳;然脾喜燥恶湿,心阳又能温煦脾土,助脾运化,脾胃必得心火的温煦,才能维持正常的运化功能。若脾胃虚弱,则水谷精微不能上输,心之阳气虚弱,而发胸痹。 其三,气化关系。心与脾胃的功能联系还表现在协同化生方面,并以心主血、脾统血两功能控制血液运行周身,内濡五脏六腑,外养肢体、官窍、皮毛。《景岳全书》曰:“血者水谷之精也,源源而来,而实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胃为气血水谷之海,而心主血脉,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两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另外,心还有化生血液的作用,即《灵枢·决气》中所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机体一切功能活动及生命的维持都要依赖五脏的精气,而五脏之精气莫不来源于脾胃之运化。正如《素问·经脉别论》中所说“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 在血液形成与运行过程中,宗气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枢·邪客》中云:“五谷入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遂,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也就是说,宗气是由脾胃水谷所化,积聚于胸中的气。它循行于喉咙,贯通心肺,而司呼吸,行血气,是具有促进心肺作用的一种气。《灵枢·刺节真邪》说:“宗气不下,则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可见宗气不足则导致经隧不通,血凝留止,也是胸痹心痛等的发病基础。 其四,气机关系。脾胃位属中焦,互为表里,为气机升降枢纽。脾主升清,脾气一升,则肝气随之而升发,肾水随之气化,脾气升则水谷精微转于肺脏而敷布周身;胃主降,胃气降则糟粕得以下行,心火随之下潜,心肾得以相交。脾胃健,则心之气血充盛,心火下交,肾水上升,平和调顺。若寒邪入胃,饮食伤胃或情志不畅,致脾胃气机升降失司,影响上焦,则诱发心脉不畅,出现心痛。 唐代医家孙思邈强调“五脏不足,调于胃”,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金元李杲著述《脾胃论》,使脾胃学说得到阐明和发挥,脾胃是主宰后天营养的大本营,因而有“胃气无损,诸可无虑;胃气一败,百药难施”,强调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重要性。 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脾运化水谷精微,濡养脏腑,脾虚运行无力,气血生化不足,心失所养则心气虚衰,无力鼓动血脉而心悸、乏力,动则加剧。脾为气血化生之源,脾虚则气血化生乏源,心失荣养而致心血不足,脾失健运,湿浊中生,循经上逆胸中,痹阻胸阳,均可导致胸闷、气短、心前区憋闷疼痛,胃胀、恶心、呕吐、腹泻、疲劳乏力、腰酸腿沉、浮肿头晕等。 其发病的机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脾气亏虚运化失常,水液代谢障碍,水湿停聚,郁久成痰、成饮、成湿,而致痰湿壅盛、水饮内停。二是脾气亏虚生化乏源,引起气血不足、阴津亏乏。三是脾气亏虚,卫外不固,易受外邪尤其是寒、湿邪入侵,更伤脾胃。四是湿性黏滞,湿邪积聚,日久生瘀,瘀阻经络,使气血运行不畅,而致痰湿兼血瘀。痰瘀互结,阻痹心经脉络,加重血瘀而致胸部疼痛、胸闷憋气反复发作,舌质瘀点、瘀斑。五是湿邪常与寒、热夹杂,寒性凝滞,侵犯经脉,使血行迟缓,甚至凝滞不通;热邪循经入血,煎熬血液使血行塞滞成瘀;气虚,推动血行无力,则血流不畅,日久成瘀。痰湿日久与瘀血夹杂而致痰瘀互结。田芬兰教授认为,健脾和胃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关键所在。 田教授的学术思想在临床用药上有充分体现。脾胃气虚者,胸部隐痛、胸闷憋气、气短乏力、心悸心慌,舌质淡、苔薄白,脉虚弱或沉而无力,多用黄芪、党参、炒白术、茯苓、炙甘草、扁豆、山药;脾虚湿盛者,见脘闷、恶心呕吐,舌苔厚浊,脉缓滑,常用制半夏、砂仁、薏米、泽泻、茯苓、白豆蔻;脾虚肝气滞者,见胸闷胀满,胸胁胀痛,胸闷憋气,精神刺激或情绪激动诱发加重,精神抑郁,脉沉弦或弦,常用枳壳、香附、香橼、佛手等;脾虚中气滞者,见胸闷憋气、胸部胀闷,脘腹胀满,嗳气吞酸,食少纳呆,大便不爽,舌质淡、苔薄白或白厚或白腻,脉弦滑或沉,多用木香、苏梗、沉香、砂仁;脾虚血瘀者,见胸痛剧烈,痛引肩背,胸部刺痛,固定不移,入夜更甚,舌质、口唇紫黯,舌有瘀斑、瘀点,脉弦涩,多用丹参、檀香、三七、五灵脂、葛根、益母草、桃仁等;脾虚痰热者,常用瓜蒌、竹茹、黄连、知母等清热不滋腻的药物;脾肾阳虚者,见面色苍白,形寒肢冷,腰膝酸软无力,小便多,舌淡苔白,脉沉细,常用熟附片、炙桂枝、熟地黄、仙茅、淫洋藿、菟丝子;脾虚津亏者,常用太子参、天花粉、知母、麦冬、五味子、沙参、玉竹、柏子仁等;肾阴虚者,见面白唇红,头晕,睡眠不佳,口干咽燥,腰膝酸痛,舌质红嫩,苔薄白或苔少,脉细数而弱,常用何首乌、山萸肉、桑寄生、女贞子、旱莲草、太子参等。 第六节 心病应以调理脾胃为先 田芬兰教授认为脾胃在整体中具有重要地位,善治脾胃者可以调五脏。因此治疗疑难病症,常从调理脾胃入手、善后。正如周慎斋所言:“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何以言之?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疾病日久矣。万物从土而生,亦从土而归,补肾不如补脾,此之谓也。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颇多。”此外,对脾胃除了抓住脾胃本脏外,还要重视五脏的关系:脾胃居中焦为升降之枢纽,脾胃有病影响他脏,他脏有病也影响到脾胃,脏腑辨证尤应重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机体生命活动的源泉,是心主神志与心主血脉的基础,而且是提高和巩固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脾胃居五脏之中,上及心肺,下及肝肾,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脾胃失调易致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失衡,气血逆乱,则心病由生。另外,中医对病后调理,都着眼于脾胃。“五脏不足,调于胃”,“久病不已,宜从中治”。胃气的盛衰亦决定了疾病的预后,“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一败,百药难治”。 田芬兰教授临床常把“顾护胃气、养脾阴”作为重要的治疗原则,认为五脏六腑皆可分阴阳,脾也可分为阴阳。然而,古医籍中却很少提及脾阴,存在着重视脾阳而忽视脾阴的现象。运化是脾的主要功能之一,脾主运化是指脾具有助胃消化、吸收、输布水谷精微转化为气血津液,以营养各脏腑组织的作用。脾的运化功能包括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液两个方面。脾之运化既需要脾阳的推动作用,也需要脾阴的参与,脾阴是脾运化功能的物质基础。正如唐容川所言:“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 关于脾阴学说,《黄帝内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却具有脾阴学说的雏形。《素问·奇病论》曰“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灵枢·本神》曰“脾藏营”。关于“营”的含义,明代李时珍解释为“营者,阴血”,表明脾阴客观存在,指出了脾阴是以“营血”形式存在。明代万密斋在《养生四要》中提到:“受水谷之入而变化者,脾胃之阳也,散水谷之气以成营卫者,脾胃之阴也。”明代杜文燮《药鉴·病机赋》载:“胃阳主气,司受纳,阳常有余。脾阴主血,司运化,阴常不足,胃乃六腑之本,能纳受水谷,方可化气液,脾为五脏之本,能运化气液,方能充荣卫,胃气弱则百病生,脾阴足而诸邪息。”秦景明的《症因脉治》中提到“脾虚有阴阳之分,脾阴虚者,脾血消耗,虚火上炎”,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认为“凡劳倦伤脾而发热者,以脾阴不足,故易于伤,伤则热生于肌肉之分,亦阴虚”,并主张在治疗上使用玉女煎、五福饮、六味地黄丸等方剂,薛生白则直言“脾阴虚则便溏”。 田芬兰教授重视脾胃功能,善于从调理脾胃治疗内科疾病。明代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首次将“脾阴不足”作为病理理念提出,制订了治脾名方“资生丸”,填补了前人专注脾阳而忽视脾阴的空白,此方是由,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参苓白术散加味而成(山药、莲子、薏苡仁、芡实、茯苓、扁豆、人参、白术、甘草、桔梗、麦芽、陈皮、山楂、神曲、砂仁、白豆蔻、藿香、黄连),方中寓养阴以调运,体现了补脾阴之法度。田芬兰教授深谙缪希雍用药心法,用药以甘平、甘淡、质地濡润、补而不燥、滋而不腻为宜,常用药物有山药、薏苡仁、扁豆、莲子、茯苓、芡实、玉竹、甘草等。山药质地平和,不腻不燥,周慎斋曾言“山药引入脾经,单补脾阴,堪为补脾阴之佳品”。 因此,田芬兰教授主张治疗心病重在调理脾胃,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脾胃气虚:症见胸部隐痛,胸闷憋气,气短乏力,心悸心慌,舌质淡,苔薄白,脉虚弱或沉而无力,多用黄芪、党参、炒白术、茯苓、炙甘草、扁豆、山药等。 (2)脾虚湿盛:症见脘闷,恶心呕吐,舌苔厚浊,脉缓滑,常用制半夏、砂仁、薏苡仁、泽泻、茯苓、白豆蔻等。 (3)脾虚肝郁:症见胸闷胀满,胸胁胀痛,或胸闷憋气,精神刺激或情绪激动诱发加重,精神抑郁,脉沉弦或弦,常用枳壳、香附、香橼、佛手等。 (4)脾胃气滞:症见胸闷憋气,胸部胀满,脘腹胀满,嗳气吞酸,食少纳呆,大便不爽,舌质淡,苔薄白或白厚或白腻,脉弦滑或沉,多用木香、苏梗、沉香、砂仁等。 (5)脾虚血瘀:症见胸痛剧烈,痛引肩背,胸部刺痛,固定不移,入夜更甚,口唇、舌质紫黯,舌有瘀斑、瘀点,脉弦涩,多用丹参、檀香、三七、五灵脂、葛根、益母草、桃仁等。 (6)脾虚痰热:症见胸闷心悸,口苦,便干,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常用瓜蒌、竹茹、黄连、知母等。 (7)脾肾阳虚:症见面色苍白,形寒肢冷,腰膝酸软无力,小便多,舌淡苔白,脉沉细,常用熟附片、炙桂枝、熟地黄、仙茅、淫洋藿、菟丝子等。 (8)脾胃津亏:症见口干唇燥,形体消瘦,手足心热,大便干燥,舌绛红而干,少苔,脉细弱,常用太子参、天花粉、知母、麦冬、五味子、沙参、玉竹、柏子仁等;兼肾阴虚者,见面白唇红,头晕,睡眠不佳,口干咽燥,腰膝酸痛,舌质红嫩,苔薄白或苔少,脉细数而弱者,常用何首乌、山萸肉、桑寄生、女贞子、旱莲草等。 以治急性心肌梗死为例,急性期可表现出胸痛胸闷、心烦急躁、发热汗出、口苦黏腻、腹胀纳呆、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之痰热蕴结之候;或胸痛胸闷、口黏纳呆、舌苔厚腻、脉弦滑之痰湿蕴结之候。治疗以健脾清热祛痰或健脾燥湿祛痰为主。恢复期转化为口黏纳呆、舌苔厚腻(时兼黄腻)、舌质嫩胖、脉弱之气虚湿阻之候;或心悸不宁、舌苔薄黄少津、舌质嫩红、脉细滑之脾虚湿阻、热郁津伤证。治疗以健脾益气、燥湿化痰或健脾燥湿、滋阴清热为主。陈旧性心肌梗死需要继续用药巩固,调理脾胃,以益气养阴、健脾补肾为法治疗。 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经常有脾胃气虚及痰浊、血瘀的表现。气虚的表现如胸闷憋气、心悸气短、全身疲乏无力、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痰浊的表现如胸膺痛或有压迫感、肢体困倦、麻木不仁、纳呆、便秘、舌苔白腻或厚浊、脉弦缓、脉滑或弦。血瘀的表现如胸痛、舌质紫黯、有瘀斑或瘀点、脉涩,且临床上常常相互夹杂。即使上述症状不很显著,如心力衰竭患者仅有肢体浮肿、食欲减退、喘促,也是痰湿饮邪阻于胃、脾、肺的表现,也必须健脾以化湿。 另外,在用药过程中,田教授主张“以和为贵”,善用药对。常用的药对有:柴胡、黄芩;桂枝、白芍;当归、川芎;竹茹、枳实;黄连、半夏;瓜蒌、薤白;沙参、麦冬;延胡索、郁金;柏子仁、酸枣仁;地龙、水蛭;红花、丹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