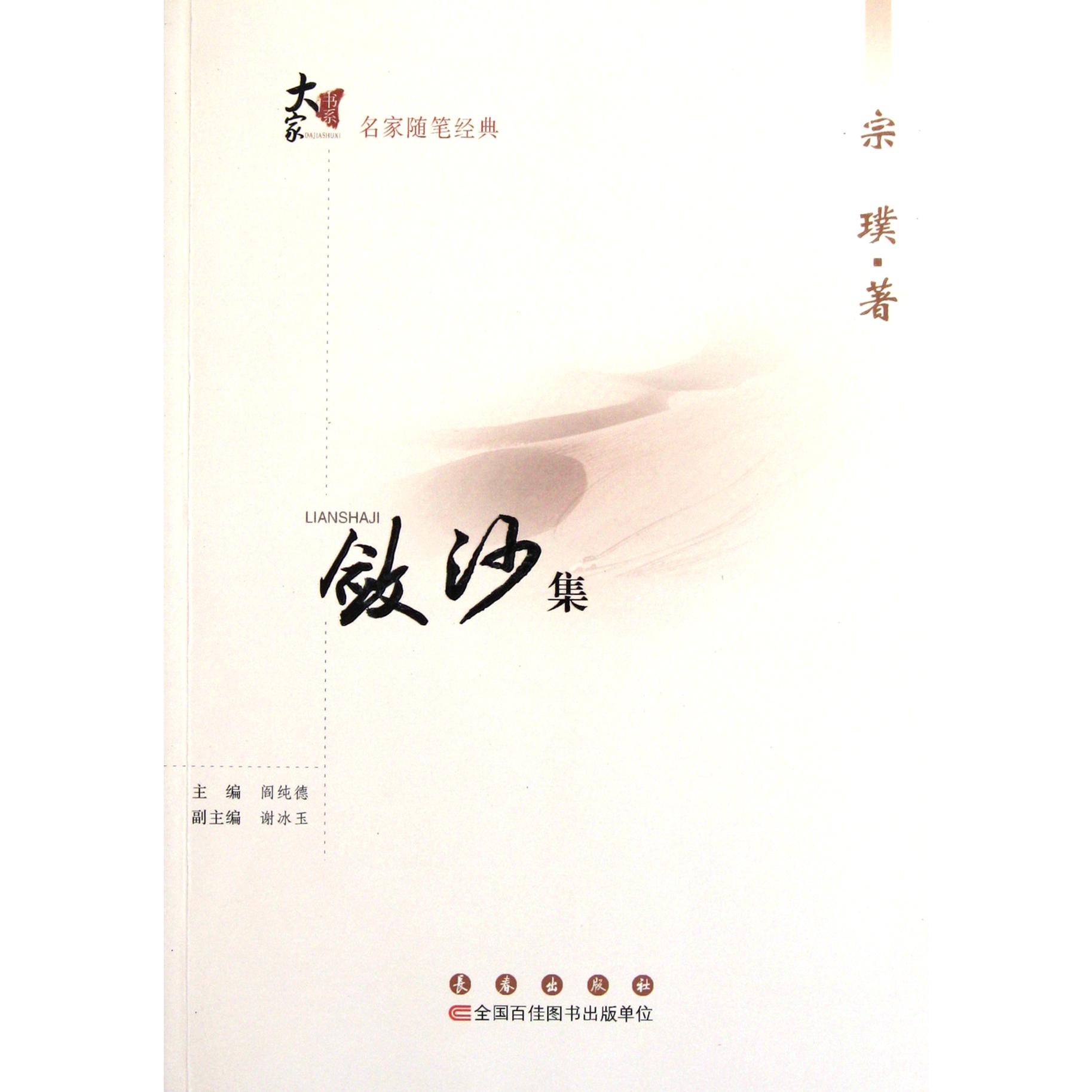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春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5.30
折扣购买: 敛沙集/名家随笔经典/大家书系
ISBN: 9787544519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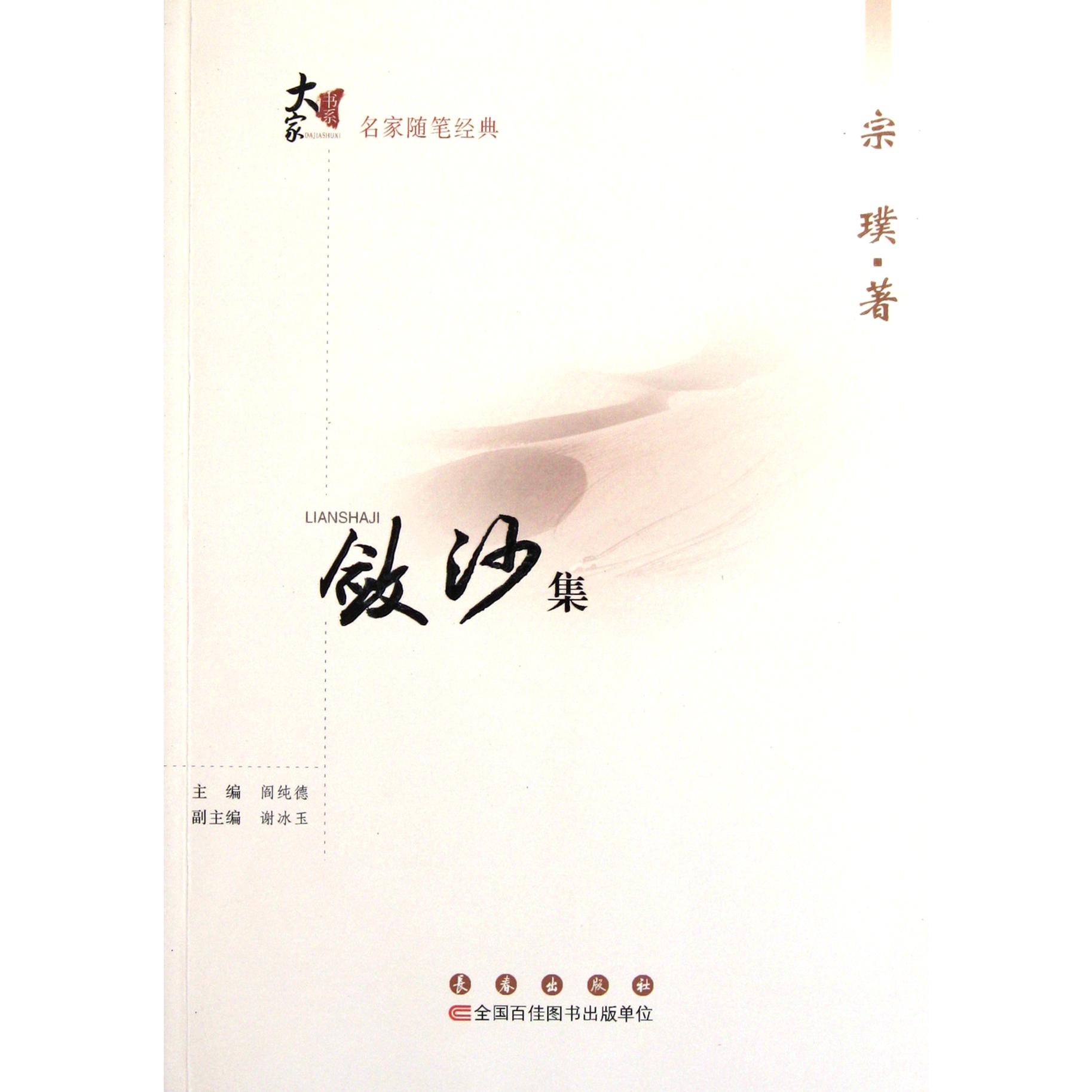
宗璞: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1928年生于北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处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1948年起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野葫芦引第一、二卷),中篇小说《三生石》,短篇小说《红豆》、《鲁鲁》、《我是谁》等,散文集《宗璞散文选集》、《铁箫人语》等。并有童话、短诗、译作等多种,已编为《宗璞文集》。
仲上课回来,带回两头水仙。可不是,一年在不知不觉间,只剩下一 个多月了,已到了养水仙的时候。 许多年来,每年冬天都要在案头供一盆水仙。近十年,却疏远了这点 情趣。现在猛一见胖胖的茎块中顶出的嫩芽,往事也从密封着的心底涌了 出来。水仙可以回来,希望可以回来,往事也可以再现,但死去的人,是 不会活转来了。 记得城居那十多年,潋莱与我们为伴。案头的水仙,很得她关注,换 水、洗石子都是她照管。绿色的芽,渐渐长成笔挺的绿叶,好像向上直指 的剑,然后绿色似乎溢出了剑峰,染在屋子里。在北风呼啸中,总感到生 命的气息。差不多常在最冷的时候,悄然飘来了淡淡的清冷的香气,那是 水仙开了。小小的花朵或仰头或颔首,在绿叶中显得那样超脱,那样幽闲 。淡黄的花心,素白的花瓣,若是单瓣的,则格外神清气朗,在线条简单 的花面上洋溢着一派天真。 等到花叶多了,总要用一根红绸带或红绉纸,也许是一根红线,把它 轻轻拢住。那也是潋莱的事。我只管赞叹:“哦,真好看。”现在案头的 水仙,也会长大,待到花开时,谁来操心用红带拢住它呢。 管花人离开这世界快十一个年头了。没有骨灰,没有放在盒里的一点 遗物,也没有一点言语。她似乎是飘然干净地去了。在北方的冬日原野上 ,一轮冷月照着其寒彻骨的井水,井水浸透了她的身心。谁能知道,她在 那生死大限上,想喊出怎样痛彻肺腑的冤情,谁又能估量她的满腔愤懑有 多么沉重!她的悲痛、愤懑以及她自己,都化作灰烟,和在祖国的天空与 泥土里了。 人们常赞梅的先出,菊的晚发。我自然也敬重它们的品格气质。但在 菊展上见到各种人工培养的菊花,总觉得那曲折舒卷虽然增加了许多姿态 ,却减少了些纯朴自然。梅之成为病梅,早有定庵居士为之鸣不平了。近 闻水仙也有种种雕琢,我不愿见。我喜欢它那点自然的挺拔,只凭了叶子 竖立着。它竖得直,其实很脆弱,一摆布便要断的。 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点固执,是无与伦比了。因为固执到 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断。 她没有惹眼的才华,只是认真,认真到固执的地步。50年代中,我们 在文艺机关工作。有一次,组织文艺界学习中国近代史,请了专家讲演。 待到一切就绪,她说:“这个月的报还没有剪完呢,回去剪报吧。”虽然 她对近代史并非没有兴趣。当时确有剪报的任务,不过从未见有人使用这 资料。听着嚓嚓的剪刀声,我觉得她认真得好笑。 “我答应过了。”她说。是的,她答应过了。她答应过的事,小至剪 报,大至关系到身家性命,她是要做到的,哪怕那允诺在冥暗之中,从来 无人知晓。 我们曾一起翻译《缪塞诗选》,其实是她翻译,我只润饰文字而已。 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常译到很晚。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有时为 了一个字,要争论很久。我说译诗不能太认真,因为诗本不能译。她说诗 人就是认真的,译诗的人更要认真。那本小书印得不多,经过那动荡的岁 月,我连一本也没有留得下。绝版的书不可再得了。眼看新书一天天多起 来,我指望着更好的译本。她还在业余翻译了法国长篇小说《保尔和维绮 妮》,未得出版。近见报上有这部小说翻译出版的消息,想来她也会觉得 安慰的。 她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事业,那点译文也和她一样不复存在了。她从 不曾想要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只是认真地、清白地过完了她的一生。她在 人生的职责里,是个尽职的教师、科员、妻子、母亲和朋友。在到处是暗 礁险滩的生活的路上,要做到尽职谈何容易!我想她是做到了。她做到了 她尽力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很少要求回报。她是这样淡泊。人们都赞水 仙的淡泊,它的生命所需不过一盆清水。其实在那块茎里,已经积蓄足够 的养料了。人的灵魂所能积蓄的养料,其丰富有时是更难想象的吧。 现在又有水仙在案头了。我不免回想与她分手的时候。记得是潋莱到 干校那年,有人从外地辗转带来了两头水仙,养在漏网的白瓷盆里。她走 的那天,已经透出嫩芽了。当时两边屋里都凌乱不堪,只有绿芽白盆、清 水和红石子,似乎还在正常秩序之中。 我们都不说话,心知她这一去归期难卜。当时每个人都不知自己明天 会变成什么,去干校后命运更不可测。但也没有想到眼前就是永诀。让她 回来收拾东西时间很短,她还想为在重病中的我做一碗汤,仅只是一碗汤 而已,但是来不及了。她的东西还没有收拾好,用两块布兜着,便去上车 。仲草草替她扎紧,提了送她。我知道她那时担心的是我的病体,怕难见 面。我倚在枕上想,我只要活着,总会有见面的一天。她临走时进房来看 着水仙,说了一句“别忘了换水”,便转身出去。从窗中见她笑着摆摆手 。然后大门呀的一声,她走了。 那竟是最后一面!那永诀的笑容留下了,留在我心底。是她,她先走 了。这些年我不常想到她。最初是不愿意想,后来也就自然地把往事封埋 。世事变迁,旧交散尽,也很少人谈起她这样平常的人。她自己,从来是 不愿占什么位置的,哪怕在别人心中。若知道我写这篇文字,一定认为很 不必,还要拉扯水仙,甚至会觉得滑稽吧。但我隔了这许多年,又在自己 案头看见了水仙,是不能不写下几行的。 尽管她希望住在遗忘之乡,我知道记住她的不止我一人。我不只记住 她那永诀的笑容,也记住要管好眼前的水仙花。换水、洗石子,用红带拢 住那从清水中长起来的叶茎。 潋莱姓陈,原籍福建,正是盛产水仙花的地方。P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