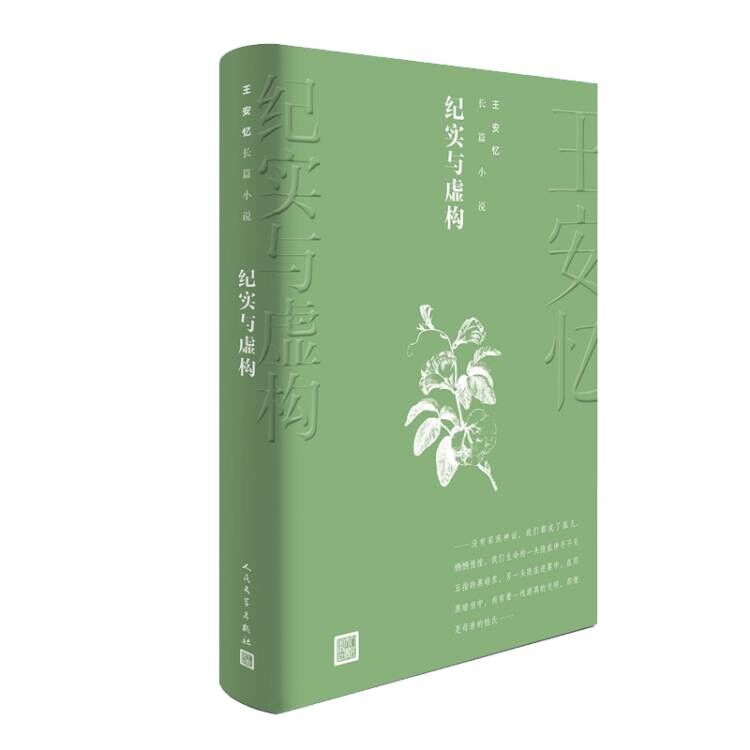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53.00
折扣价: 35.00
折扣购买: 纪实与虚构
ISBN: 9787020144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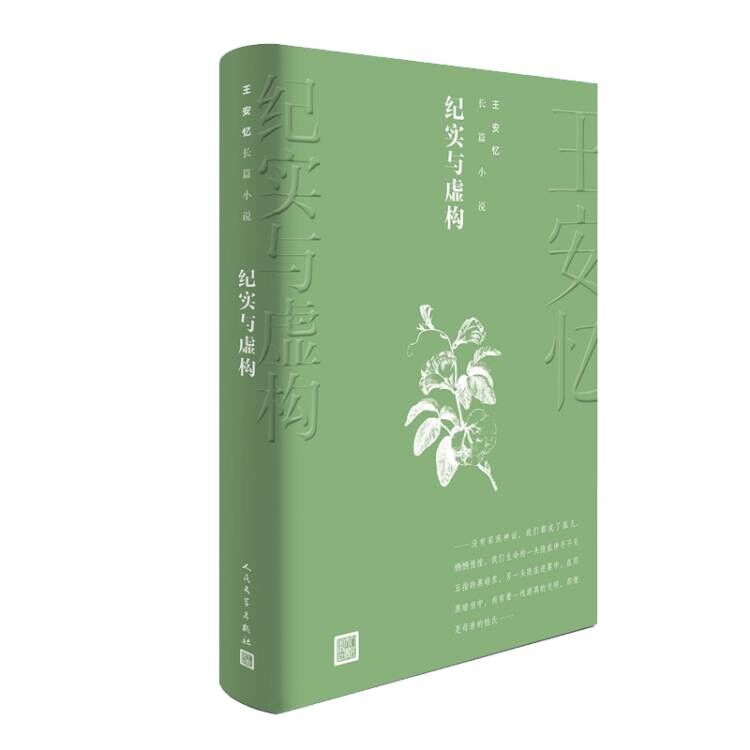
王安忆,生于1954年,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同上海,存《儿童时代》社任编辑。1980年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同年年底学习结束回原单位。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至今。著有《小鲍庄》、《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等。
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母亲总是坚 持说普通话,虽然她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还比普通话更标 准。普通话是我们家中的语言,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 。我常常闭口无言,人们就以为我是个沉默孤僻的孩子。 等我将上海话越说越流利,不再惮于开口的时候,人们反 以为我变得聒噪了。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 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 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时时警惕着,却不知 应当警惕什么。可是偶尔的,我的某一个表现,便会遭到 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批评我们从不以激烈的态度,她只 是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羞惭,这羞惭将伴随我们一生。母亲 批评我们的标准,我很久以来难下判断,不知该往哪一类 型归纳,这其实反映了母亲的经过了嫁接的价值观念,这 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母亲从不带我们去看越剧这样带有 村俗气的剧种,可是要抵制越剧的诱惑在我们所住的那幢 房子里几乎不可能。越剧里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是各家 保姆奶妈们热心的话题。保姆偷偷带我们去看了一场《梁 祝》,那绚丽的服饰和婀娜的身姿使我们顿时倾倒。从此 ,我们的游戏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后 花园里的悲喜故事。心里则充满了犯罪的感觉,生怕被母 亲发现,便做贼似的蹑着手脚。有一回,母亲到我学校去 开家长会,出于向母亲表现的动机,这晚上我便分外活跃 ,走进走出,喊这喊那,情绪亢奋。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责 为:行动琐碎。和同学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许的,这 是俗气的姿态。母亲还经常检点我们诚实、勇敢、勤劳、 俭朴的品格。汇总起来看,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具有大 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再具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品质和理想。 邻居们称呼父亲母亲为“同志”,态度恭敬,这使我 觉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这种称呼延续了许多年,后来的 改变是由于我们家新来的保姆。她进门就称父亲为“先生 ”,母亲为“师母”,无论母亲怎样纠正,请她叫“同志 ”,她只说:我不会叫。她是那种生来就为保姆的人,一 看见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随她去米店买米,一见如故 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岁就来上海帮佣,那时已是四十 岁,懂得一切雇佣和受雇的规矩。在这点上,她对母亲起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头就是关于称呼这一件事。我觉得 ,对于我们进入上海城市生活这一桩事,她是有着不可抹 杀的功劳。她还喜欢带我们到她昔日的东家家中去,让我 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结成朋友。在她离开我们家后,同样也 带了她新东家的孩子来玩。这拓展了我们家的单一的“同 志”式的社会关系,对于我们家契入上海社会,也是一个 有力的推动。她帮佣过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对各家的底细 ,也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被引进宽阔的客厅,她和 她昔日的师母娓娓而谈,我则流连于一排玻璃橱前,橱内 满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飞禽走兽,一层又一层,这给我的 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笔。我们有时候只能坐在黑暗的 灶披间里,小孩子在后弄里冲来杀去。她不时出去拖进一 个,呵斥着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领,再放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