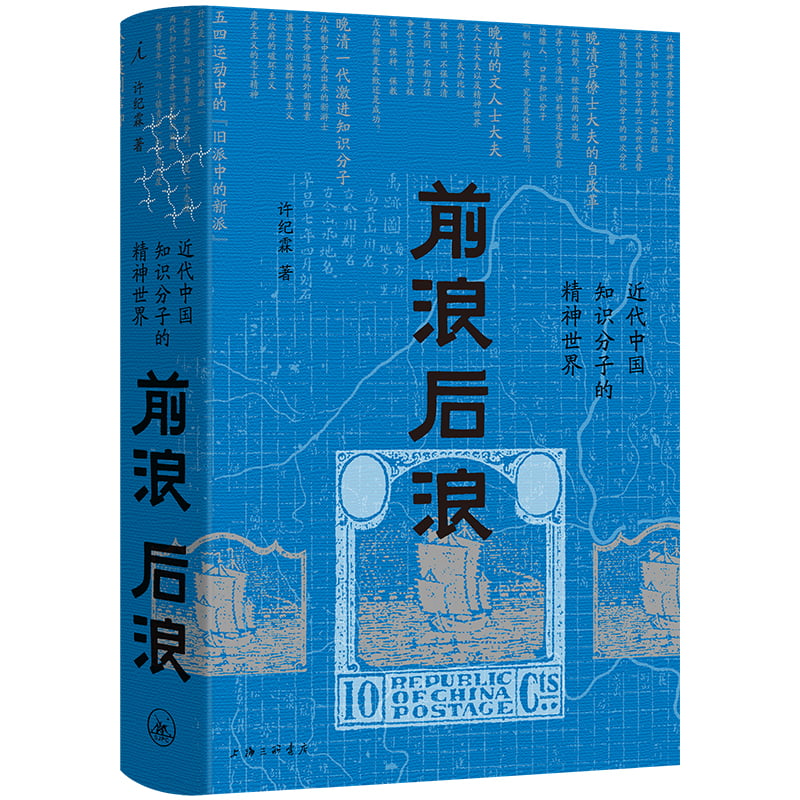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ISBN: 9787542686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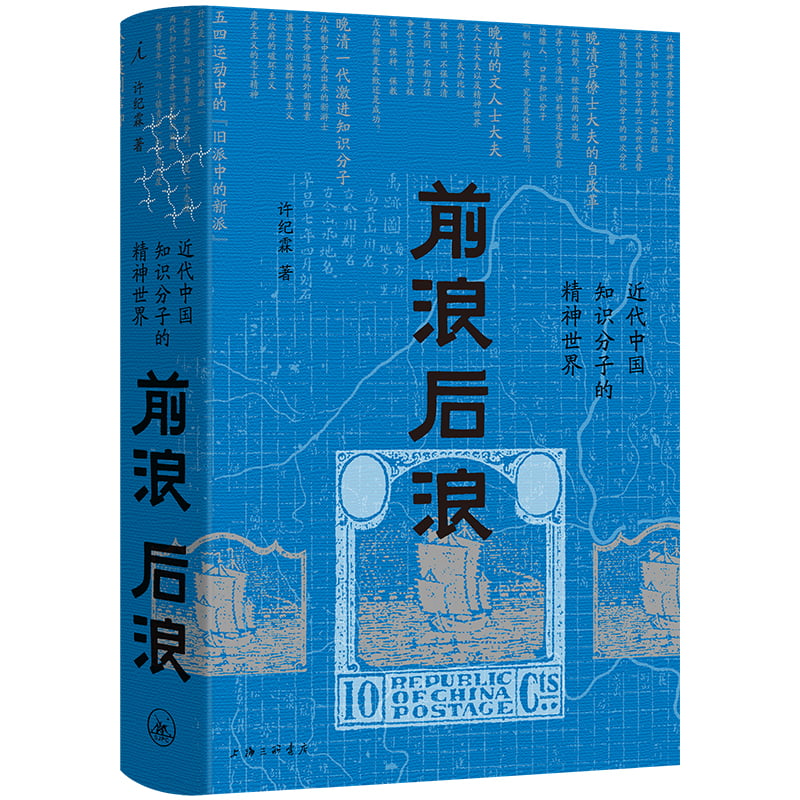
“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许纪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
从晚清到辛亥,是中国近代变革的开端。 众所周知,晚清改革七十年的整体图景,走过三个阶段,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晚清新政。 社会政治的变革,不是客观的自然演化,它首先取决于改革的主体知识分子思想与精神的变化。 那么,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来说,晚清士大夫的思想与精神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变化,触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走上了改革的不归之路? 又是什么样的精神气质,使得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迥然有异呢?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前后出现过三次大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这三次革命,知识分子都是发起者和鼓动者。 在传统的中华帝国之中,本来读书人都是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守护者,为什么到了清末的世纪之交,会分化出激烈的革命者,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些读书人? 是什么样的社会处境与思想因素,催化他们走向反满的激进道路? 罗家伦当年嘲笑《东方杂志》的杜亚泉诸人:“你说他旧么,他又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这种不新不旧、半新半旧、亦新亦旧,正是“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时期的独家特色。在五四时期,与“旧派中的新派”相映成趣的,还有另一类“新派中的旧派”,即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从海外留学归来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现代学人。 新的问题意识在于—— 从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时代更替来看,这批“旧派中的新派”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他们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共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那么两代启蒙者的区别究竟何在,是知识上的还是态度上的? 最后,当“新青年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旧派中的新派”对年轻一代的影响真的消失了吗,如果还在,那么究竟何在? 从1915年到1925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 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 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马列主义之路,从思想史角度而言,依然有若干问题值得继续发掘—— 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之前的两大思潮,那么,这三大思潮之间的逻辑脉络究竟如何?它们在类型上究竟有何不同,以至于革命知识分子最终会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马列主义? 第二,“主义”总是与一定的组织形态发生关联,五四时期的组织类型与什么样的“主义”类型有着对应的关系? 第三,现有的研究大都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称,或者以马克思主义,或者以马列主义命名之,但我们都知道,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分裂,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列宁主义泾渭分明,那么,创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什么阶段接受的是未分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什么时候最后认同了俄国的列宁主义? 五四的新式知识分子,在1910年代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然而,这批曾经在同一个壕沟里向传统旧学并肩作战的同道,进入1920年代之后步入了分岔之路。 其中,最大的分歧有两条脉络—— 一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相信救世之道在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后来趋向了温和的自由主义;而坚信通过皈依主义、全盘解决中国危机的,随之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 另一条分歧的脉络,在于依然坚守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中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迁到上海、变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之后,京城知识圈中,继承《新青年》启蒙传统的杂志中,最有影响的,当为《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群知识分子虽然同以启蒙者自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一半的精力用来打内战。其中有很多意气的成分。 值得追问的是,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分歧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这一特定的问题意识切入,透过激烈争论的表象,研究“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 首先,知识分子背后的“文化惯习”差异,如何形成了名士与绅士之间的不同格局,二者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延长线上,他们与学术体制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其次,在“语丝派”文人内部,作为名士的周作人与作为斗士的鲁迅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差别,酿成了之后进一步的分歧? 再次,鲁迅在《语丝》之外与高长虹等合作创办《莽原》,更激进的狂飙青年又如何攻击周氏兄弟,试图从五四老师一代手中夺过舆论的话语权? 1920年代中期启蒙知识分子内部这些剧烈的分裂与对抗之中,鲜明地呈现出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的不同面相。 “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 所谓“旧派中的新派”,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杜亚泉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 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分子为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与“启蒙派”的论战,是新派知识分子的内部较量。 为什么同样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文化立场截然相反? 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活动场域与“文化惯习”有何关系? “学衡派”与“启蒙派”各自接续了晚清以后什么样的知识传统的精神脉络? 为什么“学衡派”在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不是“启蒙派”的对手? 作为受过新学洗礼的古典主义者,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紧张? 在1949年之前的中共历史上,曾经有三代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第一代是五四时期的创党知识分子,第二代是“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大革命”知识分子,第三代是抗战爆发前后的“一二九”知识分子。 政治与文化层面的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虽然取决于年龄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与政治与文化的时代氛围有关,特别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显然定位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由此形成“创党”和“大革命”及“一二九”这三代革命知识分子。1 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与他们的家庭背景、少年经历和早年心理有什么关系? 影响他们成为左翼青年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社群和老师? 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最容易成为革命者? 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之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其间,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浩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 对抗虚无的途径之一,就是付诸直接的行动。 如果说在高层的著名大学学府中是“天才成群结队而来”,那么在底层的师范学校当中,则是“革命者成群结队出现”。 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取决于内在的四大精神气质 :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 革命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也是精神磨难的大炼狱,它要求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自由文人从传统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的一分子。 内部分化与世代更替交替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内在突出的精神现象。 知识分子不仅是政治的动物,也并非仅仅是理性的存在,知识分子也是情感和意志的主体,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之中,从“文化惯习”观察不同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对立,会深化对知识分子整体的认知,以接近历史完整的本相。 文化品位的差异,形成了晚清士大夫的等级化落差。 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 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三百年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 历史上的任何变法,最后所触及的深层问题,必定是人事,也就是权力的再分配。 事实上,即使到了现代,公民政治的意识依然不是部落政治、身份政治的对手,以血统和民族为本位的族群意识被激发出来,将如决堤之洪水,冲破和摧毁一切理性的大坝。 江湖社会当中虽然有侠气,但,那是梁山好汉式的草莽英雄,与读书人基本无涉,后者只能充当农民起义幕后的谋士,不再是历史中的主角。 在启蒙的阵营当中,知识的理性主义与态度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 “新青年们”要从老一代启蒙者那里夺过舆论的话语权,需要的正是那种革命家的绝对自信、斩钉截铁和不容反对,而这种狂飙的气质,最能吸引在新旧冲突中迷失了方向感的年轻人。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有儒道两面,但是从底层翻上来的“游士”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出身的,还有闻一多所说的第三重灵魂“匪气”。 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 对确定性的追求,终究是五四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超克虚无、安顿生命的终极目标。 群众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动容易收场难,具有自我加油、愈演愈烈的惯性。 绅士与名士在“文化惯习”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信念立场上,是公理与文明优先,还是个人的真实优先? 从林语堂和鲁迅这里,可以发现,所谓的“土匪”精神,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说真话,不是冒充公允、理性、文明,而是有一种直面黑暗的批评勇气。 名士与道学家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有否绅士相,而是有否真性情、真精神。 文化话语权争夺战的背后,并非仅仅与利益有关,其中涉及深刻的思想观念的分歧。 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心理上的孤苦伶仃、对温暖共同体的热切渴望,正是流浪读书人纷纷投入革命怀抱的原因所在。 革命是崇高的,但通向那条神圣之路的起点,有时候却是世俗的、卑微的,充满了个人命运的偶然性。 未来巨变中,历史还会重演吗?复盘百年中国,一张“精英迭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奋楫中国,有营养的思想从哪里来?一代要比一代强,我们如何脉动? 作为一个国家课题,从1840年到1949年,从魏源、黄遵宪、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林琴南、章太炎、杜亚泉……到张东荪,从蒋梦麟、梁漱溟、傅斯年……到朱自清,从丁玲、萧军、杨宪益……到王元化——《前浪后浪》纵现上百位知识精英的广阔心灵图景,再见“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 人,可否逆转运势?以行动,对抗虚无!一部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的全新之作—— 少年不读鲁迅,是无血性。中年不读胡适,是无理性,晚年不读林语堂,是无灵性。 一个成熟的人格,如何兼具血性、理性和灵性?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如何做到越来越“敢”? 命运的齿轮,仍在转动!《前浪后浪》揭示,世代更替不是历史的瞬间,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 昨天的教训,明天的答案?一份开阔视野的延伸书单+原汁原味的晚清民国报刊+知识群英的信息导图—— 今天,《前浪后浪》以当代视角,透过纷繁复杂表象,抓住底层逻辑,用精神、现象双线结构,简洁有力阐释我们先贤的百年精神历程——大变局,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四个内部分化。 像萤火虫一样,有一分微光,发一分热。一条一条人生线索,读者可寻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