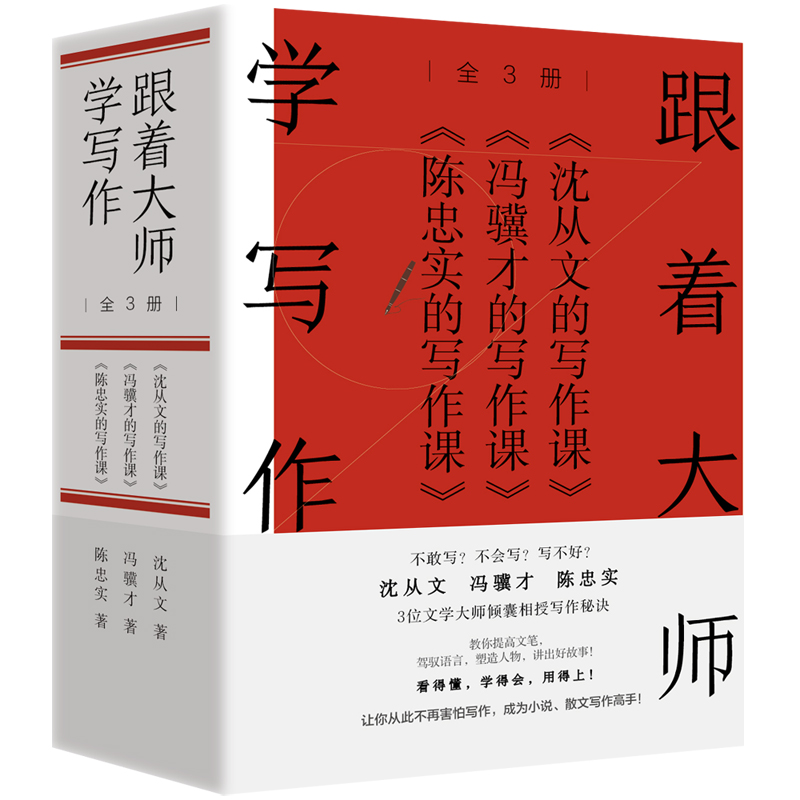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149.80
折扣价: 89.90
折扣购买: 跟着大师学写作(全3册):《沈从文的写作课》+《冯骥才的写作课》+《陈忠实的写作课》
ISBN: 9787559477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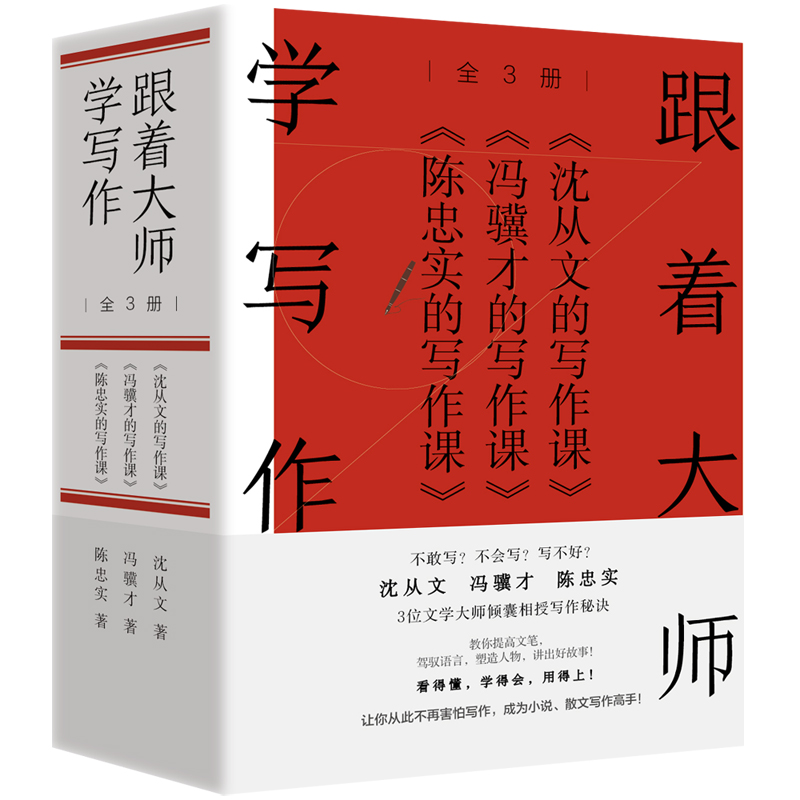
"沈从文(1902—1988) 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922年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 曾在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历史文物及工艺美术图案的研究。 主要作品包括《边城》《湘行散记》等,并有《沈从文全集》行世。 冯骥才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化遗产保护者。1942年生于天津市。以小说和散文闻名于世,善于描写民间传奇、世态人情,捕捉生活细节、场面,语言生动传神,充满画面感。代表作品有《俗世奇人》《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艺术家们》《珍珠鸟》等。 陈忠实(1942—2016)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鹿原》家喻户晓,获得1998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成影视剧。创作生涯前期以中短篇小说蜚声文坛,著有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白鹿原》至今已发行数百万册,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被中国出版集团列入“中国文库”系列,2008年11月入选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商报联合组织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人的30本书”,2009年全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沈从文的写作课》: 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帖、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帖,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 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第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第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唯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茅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似乎符咒,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行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做杠杆、做火炬、做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冯骥才的写作课》: 小说的艺术 我跟大家谈的中心是小说的艺术。 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大家讲得很多了,我不讲这些。我也不只讲小说的艺术在什么地方,而是主要讲通过什么手段,使小说成为艺术品。我要讲的是,你有了很好的立意,也有了比较深刻的思想,还有了酝酿得比较成熟的题材,这时你甚至全身都回荡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你的大脑已经展开想象的翅膀,你想动笔写作了,在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一个艺术问题。小说里所要考虑的艺术问题,都是在这个时候考虑进去的。这时,你要调动自己的艺术手段、审美趣味来进行创作。我要讲的就是要调动哪些手段。你要进入创作阶段,就同演员要进入角色一样。演员要控制角色,这控制就是艺术,就是分寸。我主要是讲分寸怎么控制。 准备分八个小题讲: 第一,讲小说的样式; 第二,讲小说的基调; 第三,讲小说的容量; 第四,讲小说的眼睛; 第五,讲小说的角度; 第六,讲小说的空白; 第七,讲小说的境界; 第八,讲时代·艺术·信息。 一 小说的样式 从古到今,小说一共有多少样式?我们现在可以数出来的,有章回体小说,有寓言体小说,有象征小说,有荒诞小说,有笔记体小说,有日记体小说,有散文化的小说,有情节性小说,有情节淡化的小说,有戏剧性的小说,当然还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小说,有正剧,有悲剧,有喜剧,有轻喜剧,有寓谐于庄的,也有寓庄于谐的,还有悲喜交加的,更有不动声色的,也有全景式的,还有焦点的……无穷无尽。 小说有多少样式?我说,人类有多少服装,小说就有多少样式。我们搞文学创作的,在这个观念上一定要解放。小说是发展着的,它的样式无边无际,没有止境。艺术永远不会灭绝。艺术的魅力就是艺术是无止境的。 大家熟知的中外文学大师,都创造了各种样式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比较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咱们叫批判现实主义),但是,他也写带点儿荒诞味道的小说,如《驴皮记》;也有带浪漫色彩的小说,如《沙漠里的爱情》。再如鲁迅,他写的小说不多,可样式很多,玩了很多花活,用了很多手法。他的小说几乎是一篇一个样式。例如《狂人日记》是一种样式,带着荒诞色彩;《祥林嫂》又是一种样式,这个小说就是很严肃、很庄重的悲剧;《古小说钩沉》则是一个寓言式的、讽刺的小说;而《伤逝》就带有契诃夫味儿,还带点儿屠格涅夫味儿。尤其是屠格涅夫,他创造了一种小说的样式。照我理解,屠格涅夫最善于写两种东西,一种是失恋,另一种是俄罗斯的大自然。他笔下的俄罗斯大自然大部分是阴天,非常阴暗,非常雄浑。他把他那失恋的美表现得非常雄壮。俄罗斯人表现失恋跟中国人不一样,不是死乞白赖地哭啊哭的,俄罗斯人把失恋表现得非常美。柴可夫斯基在失恋的时候曾写过一首钢琴协奏曲,他弹给一个朋友听,弹完之后,他问那个朋友:“你说我写的是什么?”他朋友说:“是海。”柴可夫斯基把头低下说:“不是海,我失恋了。”他把失恋写得像海那样壮阔。屠格涅夫在表现他那种失恋的伤感的美的时候,他往往让主人公(大部分是男主人公)过了多少年以后又回到了那个地方,触景生情,他大部分是那么写的。鲁迅的《伤逝》恰恰是用了这套格式。契诃夫只有在《带阁楼的房子里》使用了这种样式,他的主人公过了若干年之后,又到了以前那个女的原来住的那个带阁楼的房子里去了。 我接待过一个叫高登的美国作家。他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我问他:“你的小说主要写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讲得挺有意思。他怎么写呢?他听说谁家死人了,他就跑到人家去了,他跟人家说,我是作家,你家死的这个人一生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我想知道一下。遇到不愿讲的,把他当疯子给轰走了,有的就对他讲一讲死者过去的一些事情。他若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儿意思,引起他什么感触,或引起他什么思考,或者碰上了他心里已经成熟了的,对人生哲理某一种思考有结果的时候,他就来劲儿了,要来死者生前的照片,接着就写了一本关于死者的书发表出来了。他认为很真实,专门写这样的小说。在我们这里,一般管这个叫报告文学。前不久,黄宗英鉴于报告文学总惹祸,几乎写一篇惹一次祸,而且作家惹不起戴乌纱帽的,于是她想出了一个法子。她说,最好采访完之后,在写的时候换姓换名换地点,都换了,让他们想对号也对不上号。她想了个词儿,管这叫“非虚构小说”。实际上“非虚构小说”在国外叫“非小说”。“非小说”的小说,它也是一种样式。 我想把文学样式再扩大点儿讲讲。 我觉得,最近的文学正在向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往“雅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上发展;另一个就是往通俗文学上发展。前者,例如大家所熟悉的作品,张承志的、邓刚的、张贤亮的,等等。特别是《绿化树》,大家看法不同。我认为这个作品是把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发挥到了一个有魅力的地步。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实际上是我们已经看腻了的,艺术感觉有一点儿疲劳的那种方式,被张贤亮又重新用作家特有的、我认为是很天才的艺术感觉和他那种非常难得的艺术本能发挥出来了。近年来,影视文艺的发展,正逼着文学去追求文学性,向“雅文学”(或“纯文学”)上发展。日本的“雅文学”(或“纯文学”),就是在电影、电视普及之后,于最近出现的。有人担心影视文学的发展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流通。照我看,不会的。为什么?文学可以而且已经开始向“纯文学”上发展,向追求文学性上发展了。要知道,欣赏电影、电视的审美过程是人家演什么,你就看什么,你完全被动地、机械地接受人家的表演。读文学作品却不同了。如读诗歌“枯藤老树昏鸦”,读者要去想象,这样,作家就调动你的感受,调动你的审美,调动你的生活积累,调动你的情感,跟作家一起再创造。这也就是文学的文学性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再说通俗文学的流行。因为现在广大农村的确是富起来了,农民对文化的要求普遍提高了,增强了。通俗文学,正好适应我国农民现有的文化水平和欣赏水平,所以,通俗文学就流行起来了。前不久,武汉的农村读物出版社办了一个刊物,叫《中华文学》。据出版社一位同志说,要是敞开发行,印一百万份发行出去一点儿问题没有。天津办的《影视文艺》把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叫《书剑江山》)和他的《金蛇郎君》这两个作品登出来了,靠这个在天津就销售了八十万份。这使所有严肃的文学、打着很高招牌的刊物,包括《人民文学》,简直望尘莫及!文学往两个极端分化的趋向已经特别明显。而通俗文学提供的样式就更多了。这里不能一一细讲。 上面我说了这么多的小说样式,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小说看得很简单,以为就是那么一种或几种样式。我们搞创作的人,必须去熟悉去研究各种各样、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小说。在你进入创作过程的时候,你对要给自己的小说以什么样的样式,应该是十分清醒的。就你这个题材,你是把它写成正剧,还是悲剧,你是给它一个日记体的,还是写成抒情散文式的,或者写成戏剧性的,你首先应该非常清楚。当代小说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家运用技巧和决定它的样式,是有充分的自觉性的。在契诃夫写《草原》的时候,他并不是对于要把它写成情节淡化的小说这一点很清楚,那时也还没有“情节淡化”这个词儿。作家当时只是为了使作品不留人工斧凿的痕迹,使之一如生活本身那样自然,作家就自然而然地不让小说的情节过强,削弱了它的情节性,他是这样把情节淡化了的。我们当代小说的这一特点就不同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预先决定把它写成情节淡化的小说,如《迷人的海》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写小说要在动笔之前,先把你给它一个什么样式定下来,犹如请客,你是给人家上川味菜呀,还是上广东菜呀……上哪个菜系的菜,是必须首先定下来的。 下一个题目讲:小说的基调。 二 小说的基调 小说作者在落笔之前,首先要考虑作品写成个什么调子——它们或者是浓烈的,或者是甜蜜的,或者是忧伤的,或者是苦涩的,或把它写成“男子汉气”的(现在文学界不是有人很强调所谓的“男子汉气”吗?——这阳刚之气,就是要写出那么一种独特的“男子汉味儿”,像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像《二十二条军规》的那个味儿),或者,就干脆把它写出个“女子文学”的味道来(像石家庄就办起来个《女子文学》的刊物)。总之,作品要写成个什么样的基调,一定要事先把它定好,不能中途随便地就“串”了“味儿”。否则,作品就非得失败不可。我们当代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充分注意总体的把握和总体的构思。我们一些业余作者写的作品,则往往对此注意不够。比如,最近我看了一个刊物上的作品,便有这感觉。有些作品,写得还是很不错的,但大都是开头挺好,蛮有味道的,读着读着那“味道”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串到哪个音上去了。其毛病,大概就出在落笔前,还缺乏一个总体的构思。因此,在创作中,作者一定要有意识地控制它,充分地注意总体把握。 去年,达式常到北京去,拍我那个《走进暴风雨》的电视剧。我便趁这个机会,邀了陈建功、郑万隆、李陀几位与达式常同志交流了几点意见。我们曾经谈到,一些中外影响较大的演员(如日本的高仓健和中国的潘虹)为什么能赢得那么多的观众?其原因何在?就以潘虹在《人到中年》里演的陆文婷为例,从头到尾,她就贯穿了一个总体的认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那就是十足的“疲倦感”。由于她把握了这么一个调子,所以自始至终,她总像多了一层眼皮似的,眼睛总是睁不开的样子,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我们如果闭上眼睛,脑海就依然能浮现出陆文婷的疲倦。 所以说,小说的总体把握要非常清楚、十分自觉,作者定下的调子要紧紧地把握住。这正如我们画一幅工笔画,总不能画着画着,突然又来上一笔写意。果真如此,那么写意这一笔非是败笔不可。试想,如果有谁在用工笔画一幅“仕女图”,可又突然在仕女的脸上又写意上那么一下子,那么,这仕女便非得立刻变成了一个小花脸不可。所以,工笔画就是工笔画,写意画就是写意画。小说的基调也是一开始就应该定下来的。 下面讲小说的容量。 三 小说的容量 有人说,短篇小说容量小,都是很短的东西;中篇小说都是适中的题材,适中的容量;更多的东西,那就只有写长篇。这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但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是不对的。有时,一个很广泛的内容,可以写一个很好的短篇。为了说明问题,我想结合具体例子谈一下。 苏联有个作家叫拉克莎,她写了一篇叫《树后面是太阳》的小说,很短。写的是苏联战后的一个孤儿院,里面有很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那些打完仗失去孩子的男人和女人便到这里来领孩子,以重新组成新的家庭。小说是这样开始的:保育院院长对坐在对面的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退伍军人说:“已经跟你说了,这男孩子身体不好。”退伍军人说:“我也已经跟你说过了,只要是男孩子就行。”接着他告诉院长,他曾有过一个女儿,被德国飞机炸死了。战争中他曾想打完仗要领一个女儿回去,可战争结束后,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怕女孩子,不敢要个女儿,倒想要个男孩儿,他怕要女孩儿后再想起以前那个女孩儿。她这就写得非常棒,实际上是写了退伍军人的命运这一条线。短篇小说是各种线的交叉点。她把这个人的命运缩成那么短,插到这个地方上。退伍军人又问那个男孩子叫什么名字,院长说:“叫阿列克,这儿的男孩子都叫阿列克。因为孩子们来时没有名字,照看他们的男保育员叫阿列克,男孩子们就也都叫阿列克了。女孩子们都叫娜塔莎,因为女保育员叫娜塔莎。保育员阿列克也在战争中被炸死了。”这样就交代了保育院的经历,也是很感人的!这一条线也交叉到这个点上来了。这时小说开始出戏了。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很枯瘦的小男孩儿。一帮小男孩儿、小女孩儿的脸立刻把窗户堵上了,有的说:“但愿是他的爸爸。”因为经常有领错的。有的说:“可惜他爸爸掉了一只胳膊。”小女孩儿说:“如果我爸爸来,他没有胳膊我也高兴。”这样,作家又把孩子们的命运这条线写了出来,也交叉到这一点上。小男孩儿进来后很紧张,退伍军人也很紧张,都怕对方不认自己,院长也很紧张,怕认不成伤了孩子的心。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退伍军人同小男孩儿开始了谨慎的对话。退伍军人问:“你记得咱们家那个屋子吗?”他感到问得很聪明,因为谁家都有屋子。男孩儿说:“我记得屋子很大。”他又问:“你还记得屋里有一个窗户吗?”他又觉得自己问得聪明,因为谁家屋子都有窗户。小男孩儿说:“对,有一个窗户,那窗户也很大。”他又问;“窗户外面呢?”“窗户外面是树。”“树后面呢?”小男孩儿把眼睛眯起来说:“树后面是太阳。”退伍军人和院长忽然都感到有一种温暖。退伍军人沉浸在过去和女儿在一起的岁月里,他说:“我过去好像还教过你一支歌。”于是小男孩儿就唱起一支很古老的民歌,其实这支民歌是谁都会唱的,歌中唱道:“我认为你已经把我遗忘,但今天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院长和退伍军人跟着唱起来,三个人一边唱,一边流着眼泪……就这么一篇小说,非常漂亮。拉克莎的这个作品,就是把几条线交叉在一个点上的。 我们往往认为很短的东西才能写短篇小说,我们又把这很短的东西单摆浮搁,这样的短篇小说不可能写得深。好的短篇小说,它应该是几条线交叉:人的命运的线、故事的线、情感的线,交叉在一起,在那个交叉点上提出最闪光的东西来,提出最凝聚的、最有魅力的东西来。这是短篇小说,是真正的短篇小说,是真正有魅力的、有艺术性的短篇小说。这样的短篇小说,它的容量绝不是很淡的,而是很浓的。它可以写得很淡,但它是很浓的。所以我说,长篇小说是面,中篇小说是线,短篇小说是点。短篇小说要写好,就要找准这个点,这个几条线交叉的点。怎样找准这个点?我在第四个问题“小说的眼睛”中讲。 …… 《陈忠实的写作课》: 《白鹿原》创作漫谈 一 这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尝试。此前我没有过任何长篇的构思。而关于要写长篇小说的愿望几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但具体实施却是无法预定的事。我对长篇的写作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不无畏怯和神秘感。我的这种态度和感觉主要是阅读那些大家的长篇所造成的,长篇对于作家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验,单是语言也是不容轻视的。长篇占用大量的生活素材,弄不好就会造成令人痛心的糟蹋浪费,这对作家来说是致命的。我知道我尚不具备写作长篇的能力,所以一直通过写中短篇来练习这种能力作为基础准备,记得当初有朋友问及长篇写作的考虑时,我说我要写出十九个中篇以后再具体考虑长篇试验。实际的情形是截止到长篇《白鹿原》动手,我写出了九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耐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十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终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这大致是一九八六年的事情,那时候我的思想十分活跃。 二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对我构成什么压力。这不是我的境界超脱也不是我的孤傲或鸵鸟式的愚蠢,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多种流派多种主义的姹紫嫣红的景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所以还能保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写作心境。当然,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是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规的制约。当你的双重体验不能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你的创作也就不能达到某种期望的高度,如果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压力在顶,可能倒使自己处于某种焦灼。 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入文学一直到此,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造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我的自信又一次压倒了自卑,感觉告诉我,这种状况往往是我创作进步的一种心理征兆。 三 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在我还是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诸如“围城”“年馑”“虎烈拉瘟疫”“反正”等,那时候只当热闹听,即使后来从事写作许多年也没有想到过要写这些,或者想这些东西还可以进入创作。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是我已经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当然,这个由思索引起的自我否定和新的创造理想的产生过程,其根本动因是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深化。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不过是竭尽截止到一九八七年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 世界史中有一个细节可能被许多人忽视了,而《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号称日本通的赖肖尔却抓住这个情节解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即:西方洋人的炮舰在第一次轰击我们这个封建帝国用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门户的同时,也轰击了海上弹丸之国日本的门户,那门口的防御工事也是靠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那个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所保护着的也是一个封建小帝国,而且这个封建小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照我们这个大帝国仿建的。洋枪洋舰轰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的议会制的“维新”,而且可以说是和平的革命,既保存了天皇的象征又使日本社会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变革;中国却相反,先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接着便开始了军阀大混战,直至我们这个泱泱大帝国的学生(日本自唐就以中国为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学生反倒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难了。绵延了两千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六君子的臂力和孙中山先生的臂力显然力不从心,扛倒了封建大墙也砸死了自己。从清末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 四 关于长篇创作的心理准备,适宜于所有作家的标准答案恐怕没有。回忆当初我所能意识到的需要做的心理准备,便是沉静。为此而立下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在我当时看来,此前的一切创作到此为止,对我的作品的评介已经够了,也应该到此截住。我的长篇将开始一种新的艺术体验的试验性实践,比以往任何创作阶段上都更清醒地需要一种沉静的心态;甚至觉得如不能完全进入沉静,这个作品的试验便难以成功甚至彻底砸锅。 三条约律就是为了保障整个写作期间能聚住一锅气,不至于零散泄漏零散释放,才能把这一锅馒头蒸熟。做到这三条其实也是给自己讲心理卫生的,既排除种种干扰也排除种种诱惑,甚至要冷着心肠咬紧牙关才能聚住那锅气 ,才能进入非此勿视的沉静心态。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以后,便感喟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 " "◆内容全面丰富:一套书囊括沈从文、冯骥才、陈忠实三位文学大师数十年的宝贵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 ◆实用性强:沈从文、冯骥才、陈忠实教你提高文笔、塑造人物、驾驭叙事,掌握写作的底层逻辑,成为写作高手! ◆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理论与案例相结合,不枯燥,不空谈,堪称专业写作者、文学爱好者、写作学习者的创作指南! ◆大师视角,见解独到,观点深刻! ◆特别收录沈从文、冯骥才、陈忠实经典短篇小说、散文各五篇为范本,供广大读者参考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