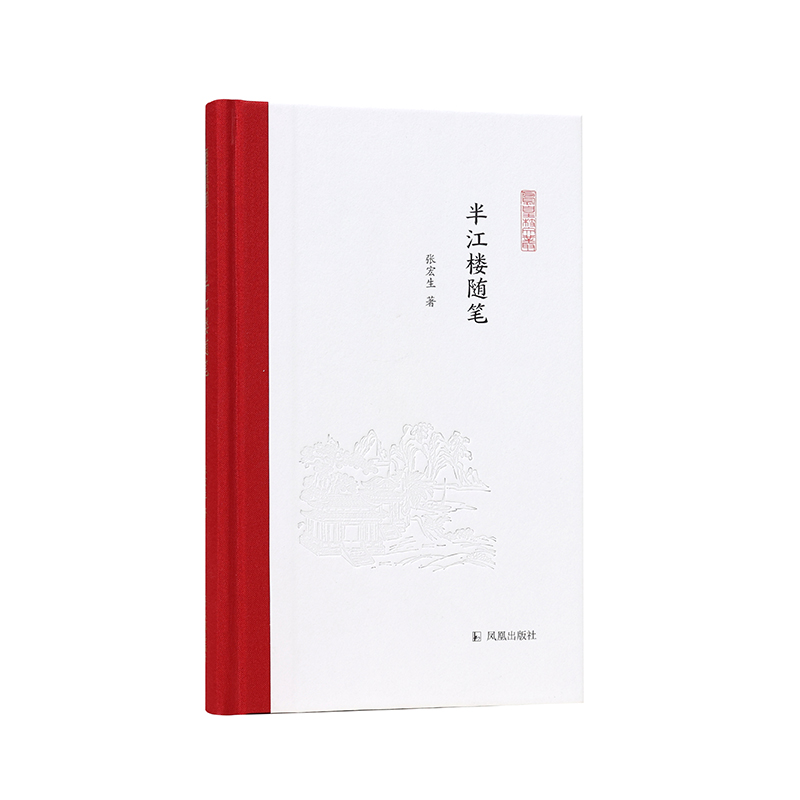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半江楼随笔(凤凰枝文丛)
ISBN: 9787550637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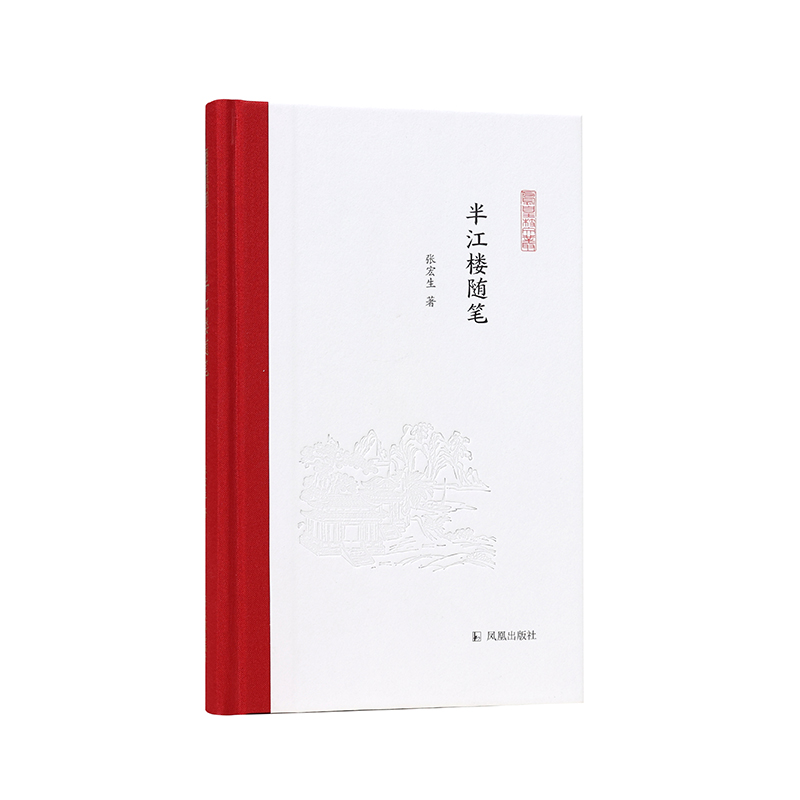
张宏生,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访问学人。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治学领域包括中国文学史、古籍整理、词学等。著有《江湖诗派研究》《宋诗:融通与开拓》《清代词学的建构》《清词探微》 《经典传承与体式流变:清词和清代词学研究》等专书十余种。主编《全清词》,先后出版《雍乾卷》和《嘉道卷》等。
大海与胸襟 ——说曹操《观沧海》 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之一。关于它的写作背景,历来研究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该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当时诸军阀逐鹿中原,辽西一带的乌桓亦强盛起来,往往伺机南下。建安十年,袁绍兵败,其子袁熙、袁尚逃到乌桓,曹操为避免受到南(控制荆襄的刘表、刘备)北夹击,乃有征乌桓之事。分歧在于,该诗是写于出征的途中,还是凯旋的路上。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影响对本诗的理解,因为无论是出征时对建功立业的期待,还是凯旋时对平定天下的向往,都能够借写大海表现出曹操的气度。 《观沧海》是《步出夏门行》的正曲第一章,全诗如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的脉络非常清晰。先写登上今河北昌黎县北的碣石山,眺望大海。其中写得又颇有层次。首先是写大海平静时的情形。“澹澹”,有人解作“摇荡”,尚比较含糊;有人解作“浩荡”,则值得斟酌。《说文》:“澹,水摇也。”联系其另外一个意思“静”(贾谊《 鸟赋》:“澹乎若深渊之静。”),“澹澹”实际上是说水波平静地摇漾。正因为如此,才能显示、衬托出“山岛竦峙”。这个“山岛”,应该是海里的岛或海边其他的岛,而不是脚下的碣石山。然后写大海汹涌时的情形。大海为什么汹涌?是由于刮起了猛烈的秋风,天时的变化,让大海完全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也因此才突出了大海的神秘、丰富和多样。接下来则又将眺望大海的时间流程总括起来写。日月的升沉和星汉的闪烁,固然与诗人往日的印象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即目所见的可能。以曹操登临望海的豪情,他在碣石山上久久驻足,饱览大自然的变化,也是符合当时情境的。最后两句,虽然是配乐的套语,却也恰如其分,因为曹操的《观沧海》,虽然字面上没有明说,实际上确实是“歌以咏志”的。曹操借大海的吞吐宇宙,也写出了自己统一天下,澄清寰宇的雄心壮志。 《观沧海》一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提出来。 首先是真正开启了以诗写海的传统。广义地看,曹操这首诗应该归入山水诗的系列,而且是山水诗的先驱。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考虑到中国的山水诗成熟在晋代,则曹操这篇作品应该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不过,作为山水诗,这篇作品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将大海引入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内陆民族,尽管不少人对大海并不陌生,但由于距离,很少会将海与自己的生活或感情结合在一起,在诗歌中出现的,更多是黄河和长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山水诗在题材上的一个欠缺。曹操的这个记录保持了很多年,一直要到很晚才得到响应。这就不仅是题材的问题,更是视野的问题。其次是探讨了描写大海的方式。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殿堂里,各个部类往往是相通的。对于水的描写,以往的理论家已经总结出一定的规范,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当写到水的时候,都要求不能局限在水本身,而要以衬托的形式写水。因此,倘若表现水的浩渺,则要结合与水发生关系的其他景物。此即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当言水之前后左右”(王又华《古今词论》引,见唐圭璋《词话丛编》)。曹操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篇作品里,他特别写到海里的山以及山上的树木,这样,就将大海的层次突显出来,增添了大海的气势和生机。而且,为了表现海的博大,更将日月星辰吐纳其中,这当然是出于想象,可是海的尽头,天水相连,也可以作为真实的错觉。调动地上之物和天空之物来写海,将天、地、水结合在一起,表现大海的壮阔和浩渺,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也暗合中国传统的写水之法,虽然可能是无心插柳,却创造了典范。复次是将情与景紧密交融。中国的诗歌创作一向强调情景交融,选取的意象不应是平泛之物,应该能够表达或象征作者的心志或情思,正如《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应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这首诗里,除了最后两句套语出现了“咏志”,可以忽略不计外,通篇都是在写景,特别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四句,更是写出了大海的广阔无边、吞纳宇宙。这既有大海本身的规模作为基础,又有诗人的胸怀作为补充。联想当时的创作背景,作为一个立志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英雄,曹操的心志在这样的景物描写中显露无遗,正是情景交融的最好范例。读这首以写景为主的诗,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情,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不妨参照曹操其他的诗。如《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是写征战之事。《短歌行》二首之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写招贤之心。《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写进取之志。《对酒》:“对酒歌,太平时,……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是写政治理想。通过“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可以看出,正因为其志不小,所以面对大海,他才能写出其壮阔。情景交融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特色,原不必特别提出,但是就具体作品而言,其中也有优劣高低之分,因为面对着同样的景,描写的才能固然各有不同,所引发的情怀也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谈到这一命题,不宜泛泛而论。 但是,关于这首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认识,特别是和文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来思考。 上文说到,曹操的这首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创举,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却并不是第一篇出现海的作品。早在《诗经》里,就已经写到了海,如《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先秦子书中,也多次提到海,如《庄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不过还都太过简略,特别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审美的情境。只有在赋的领域中,海才真正成为文学的题材。 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海赋是东汉班彪的《览海赋》。这篇赋是这样写的: 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驰鸿濑以漂骛,翼飞风而回翔。顾百川之分流,焕烂熳以成章。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蓂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勿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阍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余。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 全篇可以分为四层。第一层是前六句,写自己之所以要览海,乃是由于来到海边,想起当年孔子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就迫不及待地要奔向大海,看个究竟。第二层是“顾百川”以下六句,描写大海的壮阔。这个百川汇聚之处,光彩夺目,波涛汹涌,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日月升起的地方。那个神秘的地方,有缥缈仙山,如方丈、瀛洲、壶梁,隐于其间。于是,自然引起第三层,即“曜金”以下十句,写神仙居住的世界,这里有金阙琼楼,仙草甘泉,明珠灿烂,满目生辉,还有仙人赤松子、王子乔、西王母、韩众(终)、岐伯,相与游处,于是无限向往,而写下了“愿结旅”以下十四句。作者驾飞龙,乘长风,披云霓,精骛八极,神游万仞,天阍为他打开天门,乃得以拜见天帝,接受教诲。 《览海赋》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该篇之后,至梁代之前,就先后出现了曹丕《沧海赋》、王粲《游海赋》(以上三国魏),潘岳《沧海赋》、木华《海赋》、庾阐《海赋》、孙绰《望海赋》(以上晋),张融《海赋》(南朝齐)、萧纲《海赋》(南朝梁)等。所以,梁朝的萧统在其《文选》中,就将此种作品与其他江河赋合称,立为“江海”一类。 诗与赋的关系非常密切。《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还主要是谈赋与以《诗经》为代表的诗的关系。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熙载《艺概·赋概》:“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对赋进行文体意义上的辨体,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在汉人心目中,既然诗赋同源,当然就可以并为一体。所以刘歆《七略》立《诗赋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沿之,都认为诗赋是一类。直到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仍然继承这一传统,将诗赋并称,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我们现在讨论曹操这首诗,也可以纳入这个背景中来思考。 谈诗论词,品评小说,带你领略古典文学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