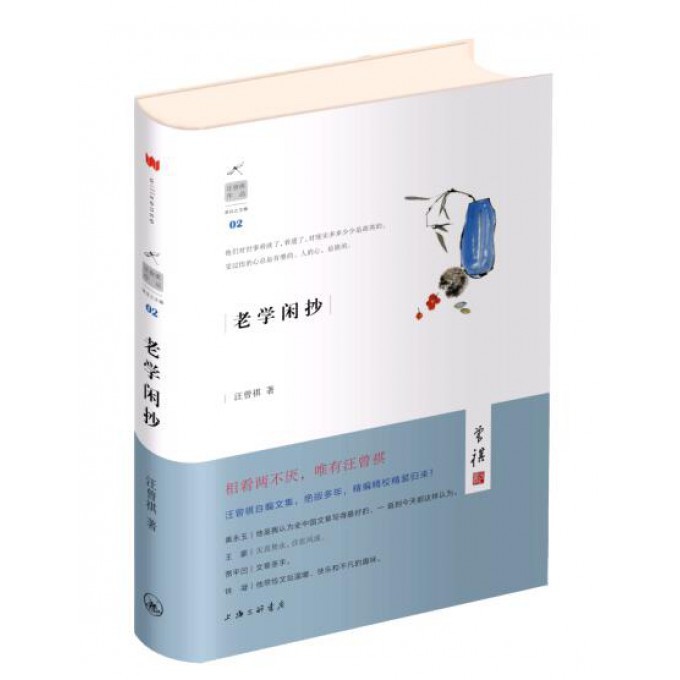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8.90
折扣购买: 老学闲抄(精)/汪曾祺作品
ISBN: 9787542655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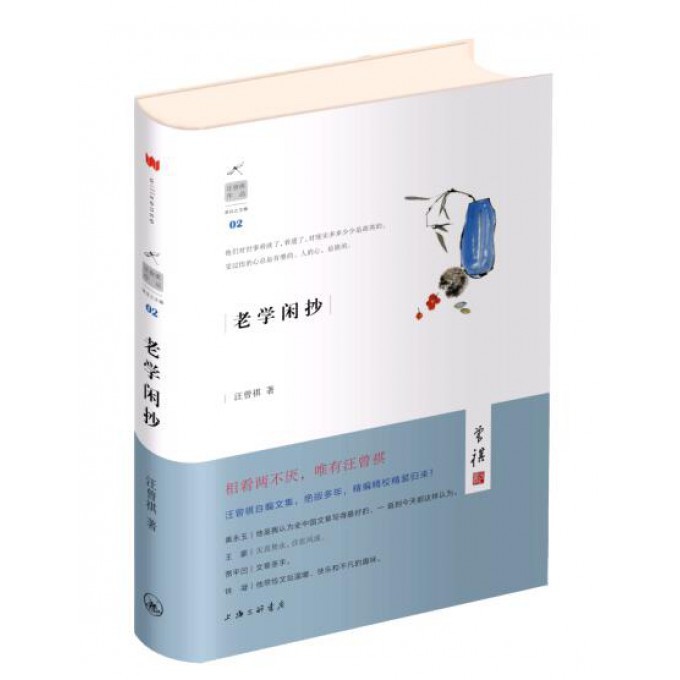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 、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 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 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 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 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 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 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 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贴切。 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 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 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华山南道、正义 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 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 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 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 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 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 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 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 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 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 湖每天每*,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 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 满感激。 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 。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 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 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 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 得好像要滴下来。湖水极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 蚊子。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中 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水常年盈满。我在昆 明住了七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偶尔接连 下了几天大雨,湖水涨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没,不 能通过了。但这样的时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浅处 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因此没有人到这里来**。 我们有一个广东籍的同学,因为失恋,曾投过翠湖。 但是他下湖在水里走了一截,又爬上来了。因为他大 概还不太想死,而且翠湖里也淹不死人。翠湖不种荷 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 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我是在 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植物的。我以后再也没看到过这 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 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声脚步,见人不惊,整天 只是安安静静地,悠然地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 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拨刺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 的大鱼,吓你一跳。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 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来考大学,寄住在 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到翠湖。 学校已经发了榜,还没有开学,我们除了骑马到黑龙 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就是到翠湖图书馆去看书 。这是我这一生去过次数*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 象**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 个道观。**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 盆白茶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 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 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 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 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 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八点,这就 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 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 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 单叫作“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作” 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 ”,——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 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 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 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 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 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 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 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 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 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一点安静。我 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 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 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 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 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这个人物 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