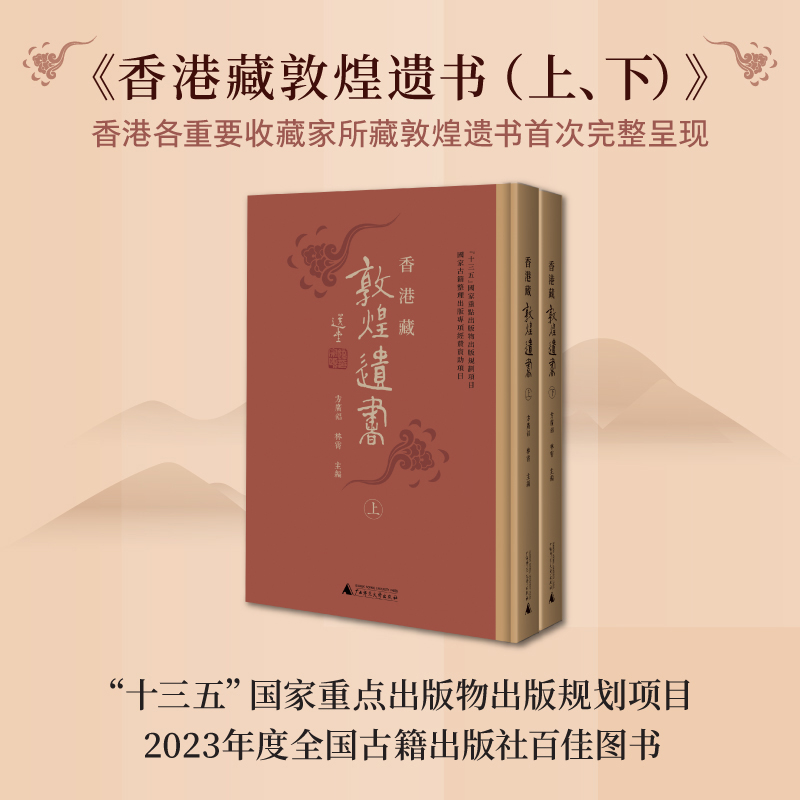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2680.00
折扣价: 2144.00
折扣购买: 香港藏敦煌遗书(上、下)
ISBN: 9787559831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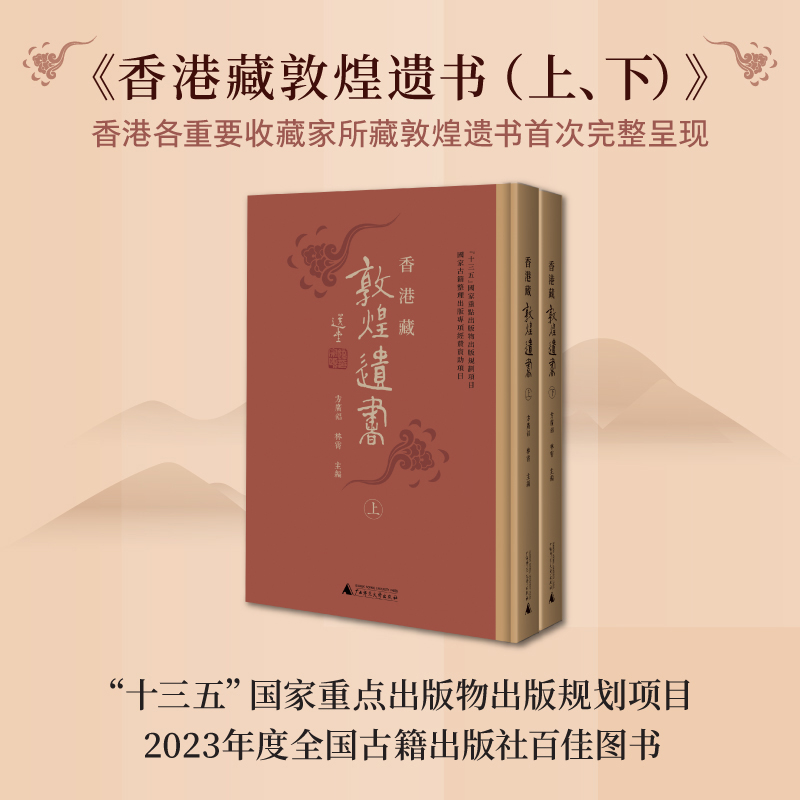
方广锠,江苏邗江人,1948年生于上海,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在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南亚所、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学习和工作。独著、合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馆藏目录卷》等20余部。主编、合编《藏外佛教文献》《中华大典·哲学典·佛道诸教分典》《中国思想宝库》《开宝遗珍》等10余种,各类敦煌遗书图录200余册。发表论文两百余篇。目前,他正在编纂世界汉文敦煌遗书总目录及从事佛教文献数字化工作。 林霄,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倾力收藏二十多年,涉及西洋油画、古代书画、玺印、青铜器领域,尤其在明代书法领域已成令人瞩目的体系。收藏之余,潜心中国书法史研究,先后发表《以笔迹学方法重鉴祝允明》《王翚晚年的艺术赞助者蔡琦考》《王宠陈淳师承祝允明新证据》《宋克未解之谜》《宋克四体陶诗双胞案新辨》《论功甫帖正是安岐着録本》《答王朴仁关于功甫帖的科学辨证》《功甫帖纸张检测报告的说明》《徐有贞自用印真伪考辨》《米万钟卒年新考》《发现邵珪》等研究论文。
序言 方广锠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居住於甘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園禄在一個通往某大型洞窟的甬道墻壁上,發現一個被古人掩藏的收納着各種文物的耳窟。那個大型洞窟,原爲敦煌歸義軍時期吴氏家族開鑿,現被敦煌研究院編爲第十六號窟。而被王道士發現的那個耳窟,亦即日後大名鼎鼎的敦煌藏經洞,今被敦煌研究院編爲第十七號窟。百年來,關於王園禄發現藏經洞的具體經過,流傳着種種傳説,近年又出現一些新的傳説,本文限於篇幅,暫置不論。關於藏經洞的封閉原因,也流傳着種種不同的説法,本文也暫置不論。藏經洞收納了數萬件大小不等的各種文字的古代遺書及相當數量的絹畫、紙本畫、塑像等各種文物。其文化内涵,涉及古中國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伊朗文化、以古希臘文化爲基礎發展起來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以及佛教、儒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是研究古代世界這四大文化、六大宗教及其相互影響、匯流的重要資料。因此,藏經洞的發現在中國及世界文化史上的意義,是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的。正因爲如此,從二十世紀開始,一門以“敦煌學”命名的新學問 在世界範圍興起,並成爲陳寅恪先生所論斷的“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令人痛心的是,藏經洞中的各種文物,在其被發現後的若干年間流散世界各地。探討其所以流散的原因,可以歸諸當時中國的積貧積弱、官員的因循瀆職、王道士的愚昧無知、當時中國文人的學風,乃至當時中國缺乏必要的文物保護法規。但是,後人批評前人是容易的,後人是否接受了這些教訓呢?正如杜牧《阿房宫賦》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當然是另一個問題,本文也不打算討論。 就敦煌遺書而言,如果按照遺書的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則根據目前公布的資料可知,收藏量最多的依次爲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大阪杏雨書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五家。據説前幾年俄羅斯科學院又在庫房發現一批殘片,數量甚多,但至今尚未公布,故詳情不清。如正式公布,則上述排序或可能改變。此外,中國、日本、西歐、北美的不少單位亦有收藏,數量多寡不一。不少私人亦有收藏。特别是近些年來國内拍賣市場興起,敦煌遺書成爲拍賣市場中令人矚目的拍品,不少私人收藏家入手收藏。目前,部分收藏家收藏的數量已成規模。近代以來,香港不僅經濟發達,亦是人文薈萃之地。我最早知道香港收藏有敦煌遺書,是在一九八七年夏上海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在上海合辦的敦煌吐魯番文物展上,當時我參觀了這個展覽,並特意購買了展覽圖錄。那次展覽共展出文物三十七件,其中三十件爲上海博物館所藏,七件則爲香港公私所藏,包括香港藝術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劉氏虚白齋、北山堂等。但當時所得信息僅此而已,也没有機會去尋訪。其實,一九九三年因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十四届亞洲及北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一九九六年因赴台灣參加“二十一世紀的宗教研討會”返回時途經香港、二〇一二年因參加香港舉行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論壇”,我曾經三次到過香港,但一則兩眼一抹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尋訪;二則來去匆匆,没有時間去尋訪。所以,當二〇一三年看到林霄先生在博客中公布的敦煌遺書,不由得喜出望外,連忙與他聯繫。具體經過,林霄先生在本書的“後記”中已經詳細記敘,這裏不再饒舌。需要强調的是,如果不是林霄先生居中聯繫、溝通各收藏單位與收藏家,則這本《香港藏敦煌遺書》不可能出版。由於林霄先生的辛勞,由於各收藏單位及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也由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及國家古籍小組的大力支持,本書終於得以送到讀者手中,在此特向林霄先生、諸位收藏家、諸收藏單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居中協調的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在此還要特别感謝饒宗頤先生。饒先生是敦煌學界的前輩、泰斗。前此在舉行的敦煌學會議上拜識。其後他曾到中國國家圖書館查閲敦煌遺書,由我接待。二〇一三年七月我第一次到香港考察敦煌遺書時,曾特意到饒府向先生請安。我奉上《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及當年四月剛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新舊編號對照卷》,並請饒先生爲計劃中的《香港藏敦煌遺書》題簽,先生慨然答應。記得那天在饒府,先生興致很高,特意向我演示他自創的養生法:躺在床上凌空寫字等各種肢體運動。我用照相機把這一珍貴場景拍攝下來。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找出當年的照片,看着先生的音容笑貌,無限感慨。 本書共收入香港公私收藏的古寫經二百五十一件。我從來主張應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來考察敦煌遺書的研究價值。本文亦從上述三個視點來評價香港所藏的這批敦煌遺書。 文物研究價值,首先應考察文物的年代。根據目前調查所得,敦煌遺書中年代最早者爲東晋寫本。目前社會上流傳若干件帶有年款,號稱西晋、三國時期書寫的敦煌遺書,凡是已經我目鑒過的,全部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僞造的贗品。根據現在已經收集到的諸多綫索,我們甚至可以推知僞造這批贗品的那個集團及其核心人物。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不贅。 根據目前調查所得,在全部六萬餘號漢文敦煌遺書中,原卷有年款或無年款,但可確定爲東晋寫本者,共約八十餘號;原卷無年款,書寫年代或爲東晋晚期,或爲南北朝早期者(凡屬這種情况,編目時一般表述爲“東晋南北朝寫本”)共約五十餘號。而在香港藏的這二百五十一件敦煌遺書中,屬於東晋寫本者有十號,屬於東晋南北朝寫本者有二號,則香港藏敦煌遺書中高古遺書的比例顯然較大。 講文物研究價值,必須涉及文物的品相,以及是否完整。絶大部分敦煌遺書均爲卷軸裝。嚴格地講,一個完整的卷軸裝,前部應該包括護首、天竿、縹帶,後部應該包括尾軸。但由於敦煌遺書爲古代佛教寺院的廢棄品,故此種完整的卷軸裝極其罕見,數萬號敦煌遺書中,此種寫卷僅爲個位數。這次發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敦煌遺書中藏有港中大10號一件,遺憾的是該件在戰爭年代曾遭火災,現縹帶僅剩殘根,尾軸上端火燒已殘,通卷有等距離火燒殘缺。雖則如此,依然屬於敦煌遺書中少有的珍品。 此外,還必須涉及寫本的裝幀。從事敦煌遺書研究以來,一個意念越來越清晰地在我心中浮現出來,就是敦煌遺書足以支撑我們在傳統的版本學之外,建立起與版本學並立的“寫本學”。就香港藏的敦煌遺書而言,除了傳統的卷軸裝之外,在翰墨軒藏品中出現一件原件多達一百九十六葉的梵夾裝,惜前九十七葉已失。令人感到頗有興味的是翰墨軒此件梵夾裝所抄爲《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一到卷四齊全。而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称“國圖”)亦收藏一件梵夾裝,現存一百一十二葉,同樣抄寫《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一到卷四齊全。不僅如此,國圖那件梵夾在《思益梵天所問經》之後又抄寫了《大乘入楞伽經》,而翰墨軒此件,從梵夾上部的編號推測,在《思益梵天所問經》之前,也抄寫了另外一部經典,可惜由於前部九十七葉全部遺失,我們現在無法得知所抄經典的内容。不管怎樣,這爲我們研究稀見的梵夾裝、研究當時佛典抄寫及佛典組織方式,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講文獻研究價值,由於敦煌遺書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爲佛教文獻,故非佛教文獻就顯得格外珍貴。此次二百五十一件遺書中有四件道教遺書,原爲松雲堂、現爲華萼交輝樓所藏。其中一件係《無上秘要》卷五。《無上秘要》爲現知最早的道教類書,早已殘缺, 前些年編纂出版的《中華道藏》將該《無上秘要》據各傳世本及敦煌遺書本整理收入。此次發現的《無上秘要》雖僅一紙四行,但文字與《中華道藏》本有不同,可供校勘。兩件爲《老子想爾注》,雖均爲殘片,但可以綴接。該《老子想爾注》似未爲歷代道藏所收,目前正由道教研究者進行研究。第四件爲《太上洞玄靈寳衆篇序經》。至於佛教遺書,則頗有歷代大藏經未收者,其中還包括若干法事文書,反映了敦煌當時實際的佛教法事活動,彌足珍貴。有些雖爲歷代大藏經所收,但此次發現的文本與歷代大藏經所收或分卷不同,或文字有歧異,可供校勘。這裏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近墨堂39 號,爲《增一阿含經(異本)·比丘尼品》(擬),但經台灣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釋長叡研究,近墨堂本此件可與日本杏雨書屋羽619號綴接,且與歷代大藏經所收本文字有歧異,屬於異本。釋長叡將這一成果寫成他的碩士論文《“杏雨書屋”所藏敦煌寫卷“羽619”與“阿含部類”的關係研究》(法鼓文理學院,二〇一五年),有興趣者可以參看。此次在李嘉誠基金會的藏品中意外地發現《金藏論》(擬)殘片兩塊,爲研究與輯校《金藏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講文字研究價值,這二百五十一件遺書時代跨度爲東晋到北宋約七八百年,字體包括隸書、行書、楷書、草書,以及兼有兩種書體的文字,如隸楷、行楷等。可供人們對中國上述七八百年的文字演變進行研究與欣賞。當然,必須説明的是:限於種種原因,本人對書法缺乏研究,故對上述遺書中書體的判定自己也不敢説無誤,敬祈諸位方家指教。就敦煌遺書的流散方式而言,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從敦煌莫高窟運出以後,未經過中間環節,直接被收藏單位收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四大單位的收藏,絶大部分屬於此類。當然,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的主體部分雖爲一九一〇年从甘肅直接押京而來,但其後幾十年中通過國家調撥、個人捐贈、市場購買等各種途徑亦入藏千餘號,這些後來入藏的部分,即下文所説的第二類。第二類是經過一個或若干個中間環節,最終被某些收藏單位或收藏家所收藏。如日本大阪杏雨書屋收藏的敦煌遺書的主體,原爲李盛鐸所得。日本東京三井文庫收藏的敦煌遺書,大多原爲張廣建所得。安徽博物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不少來自曾經宦游甘肅的許承堯。可以説,除了前述四大單位外,其餘敦煌遺書,均經過後一種方式,最終被諸收藏單位或收藏家收藏。此類遺書由於曾經過各中間環節由私人收藏,在當時,能夠收藏敦煌遺書的都屬於士大夫階層,而中國的士大夫從來又有賞玩文物的傳統,因此,不少人在自己收藏的敦煌遺書上鈐有名章或寫有題跋。亦往往召集親朋好友共同觀賞,並邀請書寫題跋。此類題跋往往出於名家名人,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與治學風格,題跋中反映的他們對敦煌遺書的態度,也成爲我們今天研究敦煌遺書何以流散、中國的敦煌學發展歷史的寶貴資料。此類題跋,偶爾也會提供一些出乎意料的信息,如近墨堂01號爲一由三十七塊殘片裝裱的册頁,第一葉有兩條題跋,第一條題跋三行,文爲:“丁巳(一九一七)六月,寓五弟南半截衖齋中,王跛持此册來,言是圖書館某君所綴輯,蓋自甘肅解館時竹頭、木屑也。”初次見到此題跋,不禁愕然。 關於本書,有幾點需要説明: 一、目前世界各地散藏的敦煌遺書中,往往可見夾雜若干日本古寫經、中國其他地方出土的古寫經等,香港也不例外。考慮到這些古寫經雖然並非出於敦煌,但也有它們獨特的價值,故一般均予收入。具體情况,可參見本書相關的條記目錄。但由於諸種原因,亦有幾件非敦煌傳世古寫經此次未能收入本書,特此説明。 二、松雲堂所藏敦煌遺書,除卷軸裝五件外,尚有殘片一百一十件,裝裱在由中村不折題耑的册頁中。後松雲堂黄先生將此册頁轉贈華萼交輝樓。但由於圖錄的前期編輯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且本書的出版時間有限定要求,未及將該册頁所收敦煌遺書的收藏編號由“松雲堂”改爲“華萼交輝樓”。故本圖錄的“松雲堂006號”到“松雲堂115號”現實爲華萼交輝樓所藏。在此特向讀者説明,並向松雲堂及華萼交輝樓致歉。 三、圖錄編號“松雲堂046號”至“松雲堂051號”爲回鶻文殘片六塊。因本人不通回鶻文,故僅著錄尺寸及外觀,至於對内容的研究,敬待能者。 在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除了感謝香港諸收藏單位及收藏家之外,我還想特别對曾供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李志綱先生、攝影師鄧明亮先生,香港藝術館的司徒元傑館長,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馮平山博物館)的何懿行助理,曾供職於近墨堂基金會的龍德俊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謝謝你們對我多次考察的支持及對出版本圖錄的諸多支持。此外,感謝山東大學張鵬先生協助考訂兩件《老子想爾注》殘片。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七日於海 《香港藏敦煌遗书》是首次对香港地区的敦煌遗书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并予刊布的重要成果。本书将这些散落在香港各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收集整理并编辑成册,为学术界了解、研究、鉴赏这批遗书提供了便利,本书的出版,具有填补敦煌遗书编目地图上最后一块拼图的重要意义,对敦煌遗书的抢救和保护,以及敦煌学的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这批遗书,内容丰富,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其中部分遗书还是第一次公布,不仅为佛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其中所含的道教类书也是未为历代道藏所收的珍稀文献,那些出自东晋到北宋经生之手的写本也是研究汉字流变、书法嬗变的珍贵资料。本书所收遗书都经过敦煌学研究专家方广锠教授亲自鉴定,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条记目录”,更是凝聚和体现了方教授丰厚的敦煌学和写本学学养,对每一件写卷的定名、内容、价值和年代判定等,都堪称目前最为专业和精到的学术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