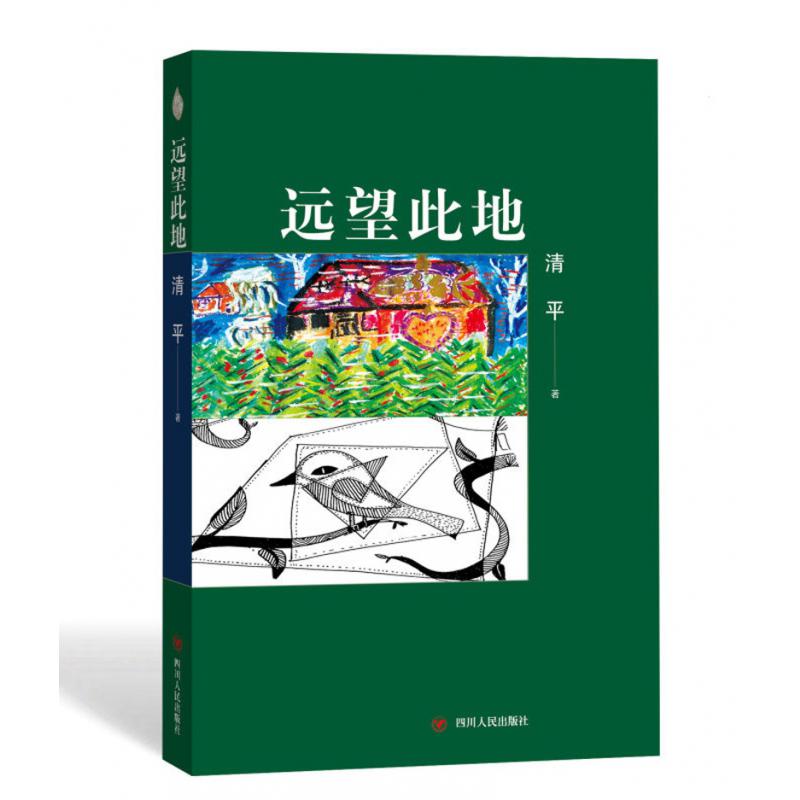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18.90
折扣购买: 远望此地
ISBN: 9787220108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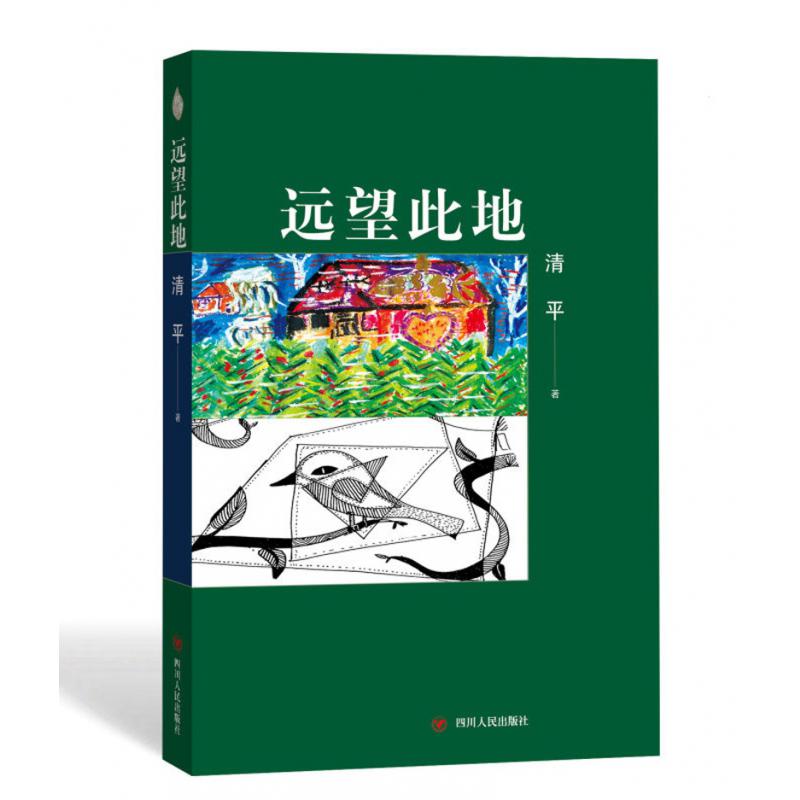
清平:本名王清平,1962年生于苏州。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1987年至今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1996年获刘丽安诗歌奖。200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类人》,2013年出版第二本诗集《我写我不写》。2011年中文主编由美国铜峡谷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诗选集《推开窗》。
"远望此地 很难说,人类何时养成远望的习惯或癖好。像所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一个偶然的小故事:某人在某时某地,意外发现,或突然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登高远望——毫无预见地,或充满先决地,开启了他后代的一个行为模型。他是激动或沮丧的,充满领悟或全然懵懂的,今天的我们唯有少量的好奇与想象,因为这是历史中最为真实的个别性,任何虚妄的对所谓真相的严肃探究都是对它无礼的冒犯。然而,远望,这个行为,必定有某个人在某种我们永不可知的情形下第一次做出了,这是无比真实的推理——虽然它来自人类自以为是的逻辑,但直到此刻,我们仍幸运地,或可悲地无法证实这种逻辑的愚蠢所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表达了我对远望,和第一个远望者的双重敬意。此刻我站在二道沟朝西的窗口,远望夜色中的灯火,我的视线被几幢高楼和夜色本身所阻隔,所谓远望,顶多 几公里。那么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么?这里似乎包含了今不如昔的种种感慨,和这两句古诗内涵的某种超越性,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远望,或者说我手里的远望,和文明的进化、道德的启发没什么关系,和高低远近的物理事实也相关不大。对我来说,远望就是朝远望去——或者朝向身影模糊的少年之我、暮年之我,或者朝向时光无尽处——而当我远望的时候,无论我站在何处,此地必定就是远方,必定是某个他者(自然包括另一时间中的我)的夜色,或是另一他者的发现和惋惜。所以,远望实际上是远望此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地也只有在远望中才有意义。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比如2017年——总有不止一个远望要来到不止一个人类群体面前,因为各种人类群体(诗歌群体、科学群体、体育群体、政治群体等等)虽然不靠远望活着,却需要用远望来疏浚和时空的关系,获得某些相对稳定的,在时空中意义存在的指认。“新诗百年”自然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冒出来的众多远望中的一个,对于作为群体的中国诗歌和它们的读者、研究者来说,它也可能是此一时间点上唯一重要的远望,有着十分广阔而清晰的公共意义空间。然而就像时间点本身有大有小一样,远望的本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诗人来说,“新诗百年”这个远望伸缩性很大,有的诗人甚至可以不去远望,或对别人的此种远望嗤之以鼻,有的诗人对这远望投入大规模的精神,以或正或反的热情“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更多的诗人则可能三五成群地同其同,异其异,友情超乎舆情,清谈之趣甚于实证之苦。实际上任何以重大话题导引的远望情形都差不多,不惟“新诗百年”特异,但在诗歌群体中的确有着别的群体较难比拟,也较难被描述的,巨大规模的公共热情和极小范围的真知灼见之间的,貌似紊乱不谐而实则微妙的结构平衡。就远望的终极意义——假设其有的话——而言,这种结构平衡比远望本身所获取的真知灼见更有启发性,因为远望几乎不具备方法论意义,而仅在一个逻辑的虚壳中纵情于混沌的想象,此种想象天然地趋向结构秘密,和它所可能的被发现能力。 重大的远望几乎都是无限的。无论“新诗百年”还是“五千年文明”,它们映照的都是人类公共时间的无限延续——尽管其意义或启发是相对有限的“远望此地”。然而也有一些并"远望此地 很难说,人类何时养成远望的习惯或癖好。像所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一个偶然的小故事:某人在某时某地,意外发现,或突然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登高远望——毫无预见地,或充满先决地,开启了他后代的一个行为模型。他是激动或沮丧的,充满领悟或全然懵懂的,今天的我们唯有少量的好奇与想象,因为这是历史中最为真实的个别性,任何虚妄的对所谓真相的严肃探究都是对它无礼的冒犯。然而,远望,这个行为,必定有某个人在某种我们永不可知的情形下第一次做出了,这是无比真实的推理——虽然它来自人类自以为是的逻辑,但直到此刻,我们仍幸运地,或可悲地无法证实这种逻辑的愚蠢所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表达了我对远望,和第一个远望者的双重敬意。此刻我站在二道沟朝西的窗口,远望夜色中的灯火,我的视线被几幢高楼和夜色本身所阻隔,所谓远望,顶多 几公里。那么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么?这里似乎包含了今不如昔的种种感慨,和这两句古诗内涵的某种超越性,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远望,或者说我手里的远望,和文明的进化、道德的启发没什么关系,和高低远近的物理事实也相关不大。对我来说,远望就是朝远望去——或者朝向身影模糊的少年之我、暮年之我,或者朝向时光无尽处——而当我远望的时候,无论我站在何处,此地必定就是远方,必定是某个他者(自然包括另一时间中的我)的夜色,或是另一他者的发现和惋惜。所以,远望实际上是远望此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地也只有在远望中才有意义。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比如2017年——总有不止一个远望要来到不止一个人类群体面前,因为各种人类群体(诗歌群体、科学群体、体育群体、政治群体等等)虽然不靠远望活着,却需要用远望来疏浚和时空的关系,获得某些相对稳定的,在时空中意义存在的指认。“新诗百年”自然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冒出来的众多远望中的一个,对于作为群体的中国诗歌和它们的读者、研究者来说,它也可能是此一时间点上唯一重要的远望,有着十分广阔而清晰的公共意义空间。然而就像时间点本身有大有小一样,远望的本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诗人来说,“新诗百年”这个远望伸缩性很大,有的诗人甚至可以不去远望,或对别人的此种远望嗤之以鼻,有的诗人对这远望投入大规模的精神,以或正或反的热情“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更多的诗人则可能三五成群地同其同,异其异,友情超乎舆情,清谈之趣甚于实证之苦。实际上任何以重大话题导引的远望情形都差不多,不惟“新诗百年”特异,但在诗歌群体中的确有着别的群体较难比拟,也较难被描述的,巨大规模的公共热情和极小范围的真知灼见之间的,貌似紊乱不谐而实则微妙的结构平衡。就远望的终极意义——假设其有的话——而言,这种结构平衡比远望本身所获取的真知灼见更有启发性,因为远望几乎不具备方法论意义,而仅在一个逻辑的虚壳中纵情于混沌的想象,此种想象天然地趋向结构秘密,和它所可能的被发现能力。 重大的远望几乎都是无限的。无论“新诗百年”还是“五千年文明”,它们映照的都是人类公共时间的无限延续——尽管其意义或启发是相对有限的“远望此地”。然而也有一些并"远望此地 很难说,人类何时养成远望的习惯或癖好。像所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一个偶然的小故事:某人在某时某地,意外发现,或突然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登高远望——毫无预见地,或充满先决地,开启了他后代的一个行为模型。他是激动或沮丧的,充满领悟或全然懵懂的,今天的我们唯有少量的好奇与想象,因为这是历史中最为真实的个别性,任何虚妄的对所谓真相的严肃探究都是对它无礼的冒犯。然而,远望,这个行为,必定有某个人在某种我们永不可知的情形下第一次做出了,这是无比真实的推理——虽然它来自人类自以为是的逻辑,但直到此刻,我们仍幸运地,或可悲地无法证实这种逻辑的愚蠢所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表达了我对远望,和第一个远望者的双重敬意。此刻我站在二道沟朝西的窗口,远望夜色中的灯火,我的视线被几幢高楼和夜色本身所阻隔,所谓远望,顶多 几公里。那么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么?这里似乎包含了今不如昔的种种感慨,和这两句古诗内涵的某种超越性,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远望,或者说我手里的远望,和文明的进化、道德的启发没什么关系,和高低远近的物理事实也相关不大。对我来说,远望就是朝远望去——或者朝向身影模糊的少年之我、暮年之我,或者朝向时光无尽处——而当我远望的时候,无论我站在何处,此地必定就是远方,必定是某个他者(自然包括另一时间中的我)的夜色,或是另一他者的发现和惋惜。所以,远望实际上是远望此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地也只有在远望中才有意义。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比如2017年——总有不止一个远望要来到不止一个人类群体面前,因为各种人类群体(诗歌群体、科学群体、体育群体、政治群体等等)虽然不靠远望活着,却需要用远望来疏浚和时空的关系,获得某些相对稳定的,在时空中意义存在的指认。“新诗百年”自然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冒出来的众多远望中的一个,对于作为群体的中国诗歌和它们的读者、研究者来说,它也可能是此一时间点上唯一重要的远望,有着十分广阔而清晰的公共意义空间。然而就像时间点本身有大有小一样,远望的本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诗人来说,“新诗百年”这个远望伸缩性很大,有的诗人甚至可以不去远望,或对别人的此种远望嗤之以鼻,有的诗人对这远望投入大规模的精神,以或正或反的热情“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更多的诗人则可能三五成群地同其同,异其异,友情超乎舆情,清谈之趣甚于实证之苦。实际上任何以重大话题导引的远望情形都差不多,不惟“新诗百年”特异,但在诗歌群体中的确有着别的群体较难比拟,也较难被描述的,巨大规模的公共热情和极小范围的真知灼见之间的,貌似紊乱不谐而实则微妙的结构平衡。就远望的终极意义——假设其有的话——而言,这种结构平衡比远望本身所获取的真知灼见更有启发性,因为远望几乎不具备方法论意义,而仅在一个逻辑的虚壳中纵情于混沌的想象,此种想象天然地趋向结构秘密,和它所可能的被发现能力。 重大的远望几乎都是无限的。无论“新诗百年”还是“五千年文明”,它们映照的都是人类公共时间的无限延续——尽管其意义或启发是相对有限的“远望此地”。然而也有一些并"远望此地 很难说,人类何时养成远望的习惯或癖好。像所有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样,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一个偶然的小故事:某人在某时某地,意外发现,或突然做出了某个行为——比如登高远望——毫无预见地,或充满先决地,开启了他后代的一个行为模型。他是激动或沮丧的,充满领悟或全然懵懂的,今天的我们唯有少量的好奇与想象,因为这是历史中最为真实的个别性,任何虚妄的对所谓真相的严肃探究都是对它无礼的冒犯。然而,远望,这个行为,必定有某个人在某种我们永不可知的情形下第一次做出了,这是无比真实的推理——虽然它来自人类自以为是的逻辑,但直到此刻,我们仍幸运地,或可悲地无法证实这种逻辑的愚蠢所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表达了我对远望,和第一个远望者的双重敬意。此刻我站在二道沟朝西的窗口,远望夜色中的灯火,我的视线被几幢高楼和夜色本身所阻隔,所谓远望,顶多 几公里。那么真的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么?这里似乎包含了今不如昔的种种感慨,和这两句古诗内涵的某种超越性,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远望,或者说我手里的远望,和文明的进化、道德的启发没什么关系,和高低远近的物理事实也相关不大。对我来说,远望就是朝远望去——或者朝向身影模糊的少年之我、暮年之我,或者朝向时光无尽处——而当我远望的时候,无论我站在何处,此地必定就是远方,必定是某个他者(自然包括另一时间中的我)的夜色,或是另一他者的发现和惋惜。所以,远望实际上是远望此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此地也只有在远望中才有意义。 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比如2017年——总有不止一个远望要来到不止一个人类群体面前,因为各种人类群体(诗歌群体、科学群体、体育群体、政治群体等等)虽然不靠远望活着,却需要用远望来疏浚和时空的关系,获得某些相对稳定的,在时空中意义存在的指认。“新诗百年”自然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冒出来的众多远望中的一个,对于作为群体的中国诗歌和它们的读者、研究者来说,它也可能是此一时间点上唯一重要的远望,有着十分广阔而清晰的公共意义空间。然而就像时间点本身有大有小一样,远望的本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作为个体的中国诗人来说,“新诗百年”这个远望伸缩性很大,有的诗人甚至可以不去远望,或对别人的此种远望嗤之以鼻,有的诗人对这远望投入大规模的精神,以或正或反的热情“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更多的诗人则可能三五成群地同其同,异其异,友情超乎舆情,清谈之趣甚于实证之苦。实际上任何以重大话题导引的远望情形都差不多,不惟“新诗百年”特异,但在诗歌群体中的确有着别的群体较难比拟,也较难被描述的,巨大规模的公共热情和极小范围的真知灼见之间的,貌似紊乱不谐而实则微妙的结构平衡。就远望的终极意义——假设其有的话——而言,这种结构平衡比远望本身所获取的真知灼见更有启发性,因为远望几乎不具备方法论意义,而仅在一个逻辑的虚壳中纵情于混沌的想象,此种想象天然地趋向结构秘密,和它所可能的被发现能力。 重大的远望几乎都是无限的。无论“新诗百年”还是“五千年文明”,它们映照的都是人类公共时间的无限延续——尽管其意义或启发是相对有限的“远望此地”。然而也有一些并非重大的远望,因为其私人性质而不得不局促于有限中,比如失恋者、复仇者的回忆与遐想,或如一位诗人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具体到“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远望此地”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假设性质,而不必顾及公共逻辑表面的现实缜密性。简单来说,一位诗人有限的远望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假设他人对此地的远望,假设自己在未来(比如十年后)对此地的远望。前一部分通常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位“他人”都可以被假设为最苛刻、最恶毒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最内行的诗坛翘楚,假设他们对此地的远望,远比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相要容易得多;后一部分,从某个角度看,则几乎完全由想象构成:那个十年二十年后的自我约等于你推窗望见的任何一位路人,而你的骄傲和雄心又必定要你将他区别于任何一位路人和熟人——包括此刻的你自己。由这样一个未来的自我回望此地,其想象力犹如杠杆一样在你既有的智力坡度和精神速率构成的不定式两边增减着势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远望绝大部分是由这更加模糊的另一个自我构成的,他的想象图景的游移提供的恰恰是最明确的远望的意义:作为源码的此地,实际上不得不生长于遥远的彼时,或者说,它的创造者不是往昔、现在,而是未来。事实上,也只有未来才有能力对“此地”有所发现,有所惋惜。 发现是乐趣,惋惜是纯正的营养。当我们远望此地,我们会感到一首诗,或一些诗,其既有的成败,是如此微不足道。 2017.7.19 一个迷局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伦理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非重大的远望,因为其私人性质而不得不局促于有限中,比如失恋者、复仇者的回忆与遐想,或如一位诗人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具体到“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远望此地”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假设性质,而不必顾及公共逻辑表面的现实缜密性。简单来说,一位诗人有限的远望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假设他人对此地的远望,假设自己在未来(比如十年后)对此地的远望。前一部分通常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位“他人”都可以被假设为最苛刻、最恶毒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最内行的诗坛翘楚,假设他们对此地的远望,远比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相要容易得多;后一部分,从某个角度看,则几乎完全由想象构成:那个十年二十年后的自我约等于你推窗望见的任何一位路人,而你的骄傲和雄心又必定要你将他区别于任何一位路人和熟人——包括此刻的你自己。由这样一个未来的自我回望此地,其想象力犹如杠杆一样在你既有的智力坡度和精神速率构成的不定式两边增减着势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远望绝大部分是由这更加模糊的另一个自我构成的,他的想象图景的游移提供的恰恰是最明确的远望的意义:作为源码的此地,实际上不得不生长于遥远的彼时,或者说,它的创造者不是往昔、现在,而是未来。事实上,也只有未来才有能力对“此地”有所发现,有所惋惜。 发现是乐趣,惋惜是纯正的营养。当我们远望此地,我们会感到一首诗,或一些诗,其既有的成败,是如此微不足道。 2017.7.19 一个迷局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伦理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非重大的远望,因为其私人性质而不得不局促于有限中,比如失恋者、复仇者的回忆与遐想,或如一位诗人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具体到“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远望此地”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假设性质,而不必顾及公共逻辑表面的现实缜密性。简单来说,一位诗人有限的远望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假设他人对此地的远望,假设自己在未来(比如十年后)对此地的远望。前一部分通常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位“他人”都可以被假设为最苛刻、最恶毒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最内行的诗坛翘楚,假设他们对此地的远望,远比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相要容易得多;后一部分,从某个角度看,则几乎完全由想象构成:那个十年二十年后的自我约等于你推窗望见的任何一位路人,而你的骄傲和雄心又必定要你将他区别于任何一位路人和熟人——包括此刻的你自己。由这样一个未来的自我回望此地,其想象力犹如杠杆一样在你既有的智力坡度和精神速率构成的不定式两边增减着势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远望绝大部分是由这更加模糊的另一个自我构成的,他的想象图景的游移提供的恰恰是最明确的远望的意义:作为源码的此地,实际上不得不生长于遥远的彼时,或者说,它的创造者不是往昔、现在,而是未来。事实上,也只有未来才有能力对“此地”有所发现,有所惋惜。 发现是乐趣,惋惜是纯正的营养。当我们远望此地,我们会感到一首诗,或一些诗,其既有的成败,是如此微不足道。 2017.7.19 一个迷局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伦理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非重大的远望,因为其私人性质而不得不局促于有限中,比如失恋者、复仇者的回忆与遐想,或如一位诗人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具体到“对其个人写作的发现与惋惜”,“远望此地”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假设性质,而不必顾及公共逻辑表面的现实缜密性。简单来说,一位诗人有限的远望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假设他人对此地的远望,假设自己在未来(比如十年后)对此地的远望。前一部分通常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因为每一位“他人”都可以被假设为最苛刻、最恶毒的批评者,同时又是最内行的诗坛翘楚,假设他们对此地的远望,远比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相要容易得多;后一部分,从某个角度看,则几乎完全由想象构成:那个十年二十年后的自我约等于你推窗望见的任何一位路人,而你的骄傲和雄心又必定要你将他区别于任何一位路人和熟人——包括此刻的你自己。由这样一个未来的自我回望此地,其想象力犹如杠杆一样在你既有的智力坡度和精神速率构成的不定式两边增减着势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远望绝大部分是由这更加模糊的另一个自我构成的,他的想象图景的游移提供的恰恰是最明确的远望的意义:作为源码的此地,实际上不得不生长于遥远的彼时,或者说,它的创造者不是往昔、现在,而是未来。事实上,也只有未来才有能力对“此地”有所发现,有所惋惜。 发现是乐趣,惋惜是纯正的营养。当我们远望此地,我们会感到一首诗,或一些诗,其既有的成败,是如此微不足道。 2017.7.19 一个迷局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伦理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并非真实的学三的场景),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并非真实的学三的场景),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并非真实的学三的场景),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并非真实的学三的场景),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 "这是一本对写作、人生、世界的时空存在不确定性均具细致分析、高远领悟的随笔诗论集,是当前同类书籍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极富启发性的珍贵文本。作者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最隐逸的杰出诗人、思辨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