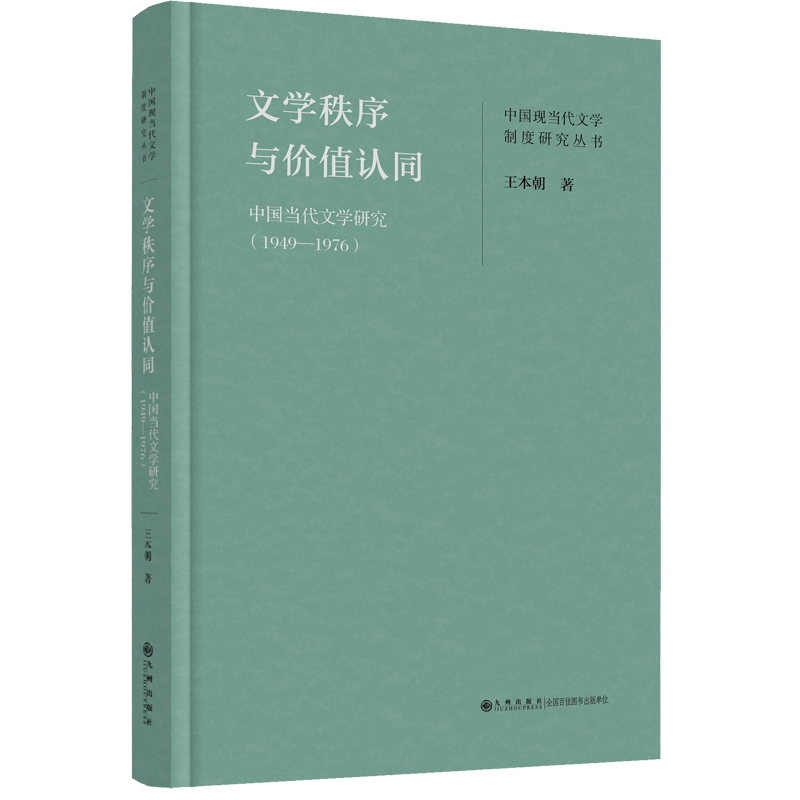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96.00
折扣价: 61.50
折扣购买: 文学秩序与价值认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
ISBN: 9787522522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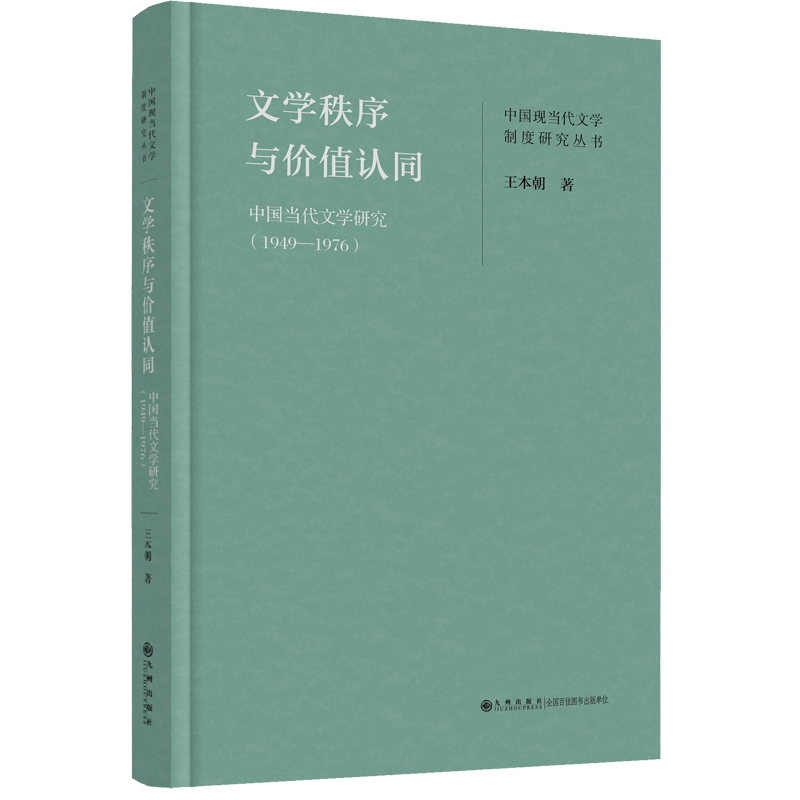
王本朝,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回到语言:重读经典》等10余种。
老舍1949年12月才从美国回到国内,1954年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陆续写作了《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和《全家福》等14部戏剧,实现了华丽转身,如鱼得水,成了社会现实的“歌德派”。1957年3月18日,他却发表了《论悲剧》一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讽刺剧”的境遇虽说不被待见,但“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运气总算不错”。相比而言,悲剧“可真有点可悲”,既“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不可以写”。于是,提出了悲剧的“写”和“说”的问题。 在老舍看来,因为现实里没人去写悲剧,自然也就谈不上写得怎么样了,要讨论的只有“可不可以写”了。古老的“命运悲剧”因为不再相信“宿命论”,也就不用照着“老调儿”去写了,后来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不可免地成悲剧”,也就是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也“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他反问是不是人们以为当时社会“没有了悲剧现实”,“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他的感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是不是人们不喜欢悲剧呢?因为没有新的悲剧出现,也就无从“知道了”。他还认为,《刘胡兰》和《董存瑞》“不能算作悲剧”,它们所“歌颂”的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虽牺牲了生命,却“死得光荣”。如果这也算作悲剧,悲剧的范围就要扩大。当然,老舍所持的标准主要是西方的悲剧传统,虽然“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如“先悲后喜”的传统大团圆,但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面对悲剧被遮蔽或者说被冷淡,老舍发出了“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的疑问。老舍也有自己的顾虑,于是有了声明式的表态,他并不想提倡悲剧,实际上也用不着他去提倡,因为“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他只是“因看不见而有些不安”,感到“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他自己“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写悲剧”,也不是出于文体保存的愿望,“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之所以重提悲剧,是因为“悲剧”是“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取用悲剧形式是为加强说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显然,老舍有意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审美立场,将倡导悲剧的意图落在了实现文学的教育作用、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上面,不免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当然,他的遮遮掩掩也是情有可原。在一个只需要歌功颂德的时代却去呼唤悲剧的写作,如仗马发出嘶鸣之声,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老舍以“设问”方式,分别从悲剧文体、悲剧现实、社会读者以及悲剧价值等方面指出了悲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许他预感到问题的敏感和现实的复杂,为了规避或者说降低难以预料的风险,他自己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又尝试解决问题。表面上是对文学悲剧形式的追问,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的质询和反思。悲剧现实虽然存在,但人们并不关注悲剧的写作。老舍的质问既是对作家责任的拷问,也是对文学价值的反思。重提悲剧问题,其用意是为了重建文学的价值和力量。老舍认为悲剧“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表现社会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命运等说法,并没有多少理论的深度和高度,也缺乏理论的原创性和系统性,他对悲剧的理解不过是如同鲁迅强调文学应“直面人生”,以及《摩罗诗力说》所说的“撄人心”而已,特别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力量。 继老舍文章之后,就有人做了呼应。彭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悲剧的现实,悲剧乃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所造成的,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将存在,所以,社会主义当然还有悲剧。胡铸在《悲和悲剧》一文里,对悲剧的有关理论,特别是悲剧根源、悲剧冲突、悲剧主人公和悲剧效果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认为,悲剧并非阶级的产物,社会主义依然还有悲剧,“当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受制于它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仍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还未随其阶级而走向灭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悲剧根源仍然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悲剧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只要有社会,有人,就免不了要有矛盾、斗争,也就有失败的痛苦,因此也就有悲剧”。老舍重提悲剧虽没有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共鸣和兴趣,风生水起,却如不竭的溪流时断时续。 60年代初,悲剧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1961年,王西彦以“细言”为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悲剧》,认为悲剧已经消失了,“在这个唱赞歌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歌颂的事物是太多了,即使也有应该揭露、批评的现象,也不能把它作悲剧来处理。悲剧这种样式,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园地里,应该是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的东西”。1961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陈毅也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戏剧要给人“愉快”,给人“艺术上的满足”,“不是作为政治课来上”,“即使是悲剧,也给人以艺术上的满足”。所以,“悲剧还是要提倡”,“悲剧对我们青年人很有教育意义”,但“不要搞成团圆主义”,因为“实际生活中也不都是完满的结局”,“也并不都是美满的”。一年以后,陈毅指出:“我们总是不愿意写悲剧,说是我们这个新社会,没有悲剧。我看呐,我们有很多同志天天在那儿造悲剧,天天在那儿演悲剧。”于是,他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悲剧呢?”“悲剧的效果往往比喜剧大,看悲剧最沉痛。沉痛的喜悦,是比一般的喜悦更高的喜悦。”这里,陈毅所说的主要是作为戏剧样式的悲剧对当代社会的艺术效果和教育意义。老舍、胡铸和陈毅都谈到了悲剧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自然也就引出了社会主义的悲剧问题。悲剧之于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但文学是否敢于涉足和表达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现实呢?这却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注释省略) 本书在占有翔实丰富扎实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大历史观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新理念,重构当代文学秩序,理性、客观地评价并确立当代文学独特又丰富的价值体系,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