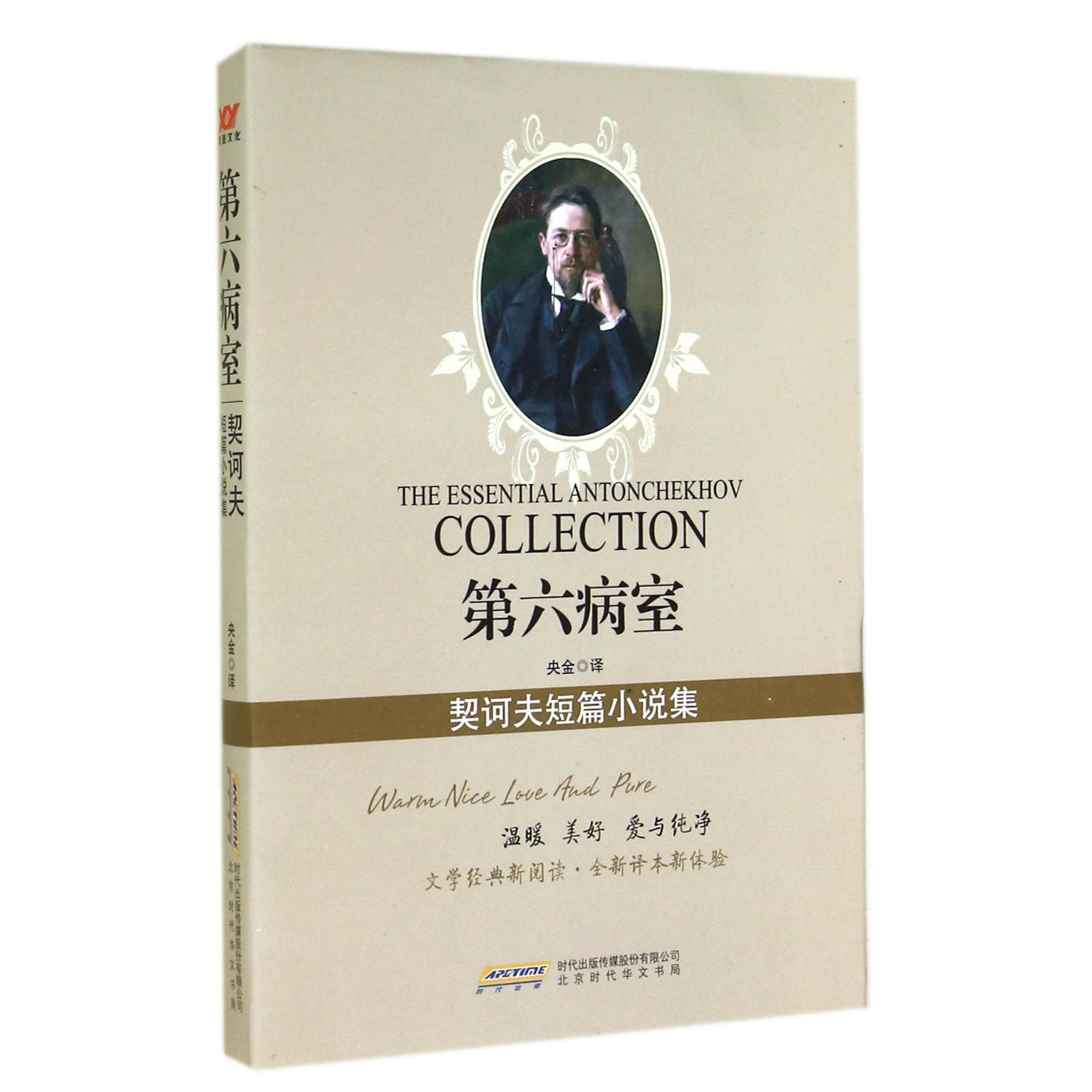
出版社: 时代华文书局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807698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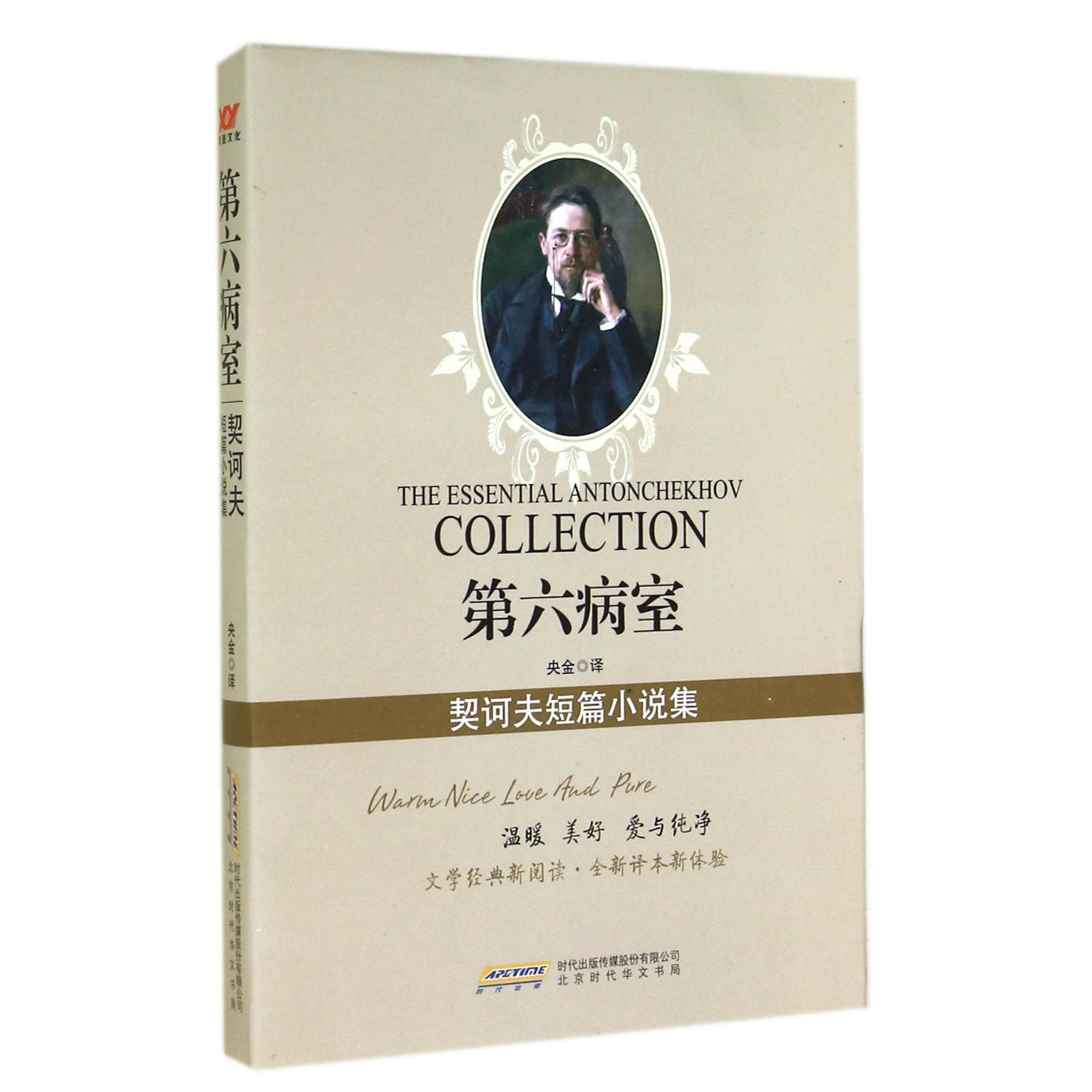
央金,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精通英语、法语,对文学作品有着独到的见解。曾就职于机关单位,现专职写作、翻译。 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著名剧作家、短篇小说大师,被誉为“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第六病室》《凡卡》,戏剧《海鸥》《三姐妹》《樱桃园》《万尼亚舅舅》等。 童道明(1937—),中国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上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开始研究契诃夫,几十年浸淫其中,是中国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戏剧笔记》《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我知道光在哪里》(与濮存昕合著)《阅读俄罗斯》《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等。
第六病室 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 和野生的大麻,几乎将院子里那座小偏屋遮掩住。偏 屋的铁皮屋顶早已锈迹斑斑,烟囱也塌得只剩半截, 门前的台阶长满了杂草,墙上斑驳的灰浆更显出屋子 的破旧。偏屋面向医院,背后本来是田野,可被一道 带钉子的灰色围墙隔开了。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暗 淡的围墙和破旧的偏屋,都给人以医院和监狱那种阴 森可怕的感觉。 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偏屋,如果你不怕路旁蜇 人的蓖麻,我们就前去看一看偏屋里面的情景。打开 门,我们来到了外室,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堆堆医 院里的破烂:床垫、破旧的病人服、长裤、蓝白条纹 的衬衫、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 ,胡乱堆放在墙下和炉子旁边,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 霉烂物特有的臭味。 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嘴里咬着烟斗的人 ,是看守人尼基塔。他身上那身红领章褪色成棕黄色 的旧军装,表明他是个退伍的老兵。他表情严肃、神 情憔悴,两道眉毛往下垂,鼻子通红,看起来,就像 一只草原牧羊犬。他个子不高,又很瘦,可是神态威 严,手上青筋暴突,但拳头粗大。看到他,人们会在 脑海中浮现这些词语: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 守、愚钝固执的人。在这种人眼里,秩序高于一切, 因而他深信不打他们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因此他 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 再往里走,您将看到宽敞的大房间,大得几乎占 去了整个偏屋,如果不算外室的话。房间的墙壁涂成 暗蓝色,天花板被熏黑了,因为房间没有烟囱,冬天 取暖用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户都被难看的 铁栅栏封着,粗劣的地板很灰暗。房间里的气味十分 浑浊,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混 杂在一起,仿佛让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都死死地钉死在了地板 上。每张床上都坐着或躺着人,他们都穿着蓝色病人 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房间里一共五个人,一个人是贵族出身,其余四 个人都是小市民。在靠门边的那张床上,一个又高又 瘦的人托着头坐着,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 糊呆呆地望着一处地方。他成天愁眉苦脸,只知道摇 头、叹气、苦笑。他不怎么和别人说话,也不搭理别 人的问话。给他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 他骨瘦如柴的模样、发红的脸颊,以及剧烈而痛苦的 咳嗽,都表明他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 在他后面那张床上的人,是个矮小、活泼好动的 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 人似的。白天他不是在房间里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走 来走去,就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床上,嘴上也 不闲着: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小声唱歌,嘿嘿窃 笑。他不仅白天这么活泼好动、孩子气,在夜里也有 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 门缝,这是他在向上帝祷告。这个老头是犹太人莫谢 伊卡,大约二十年前,帽子作坊的一场大火,弄得他 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这个房间被称为第六病室,这里的病人,只有莫 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被允许到医院外面的大 街上去活动。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原因可 能是他是医院的老住户,他从不伤害人,还可以成为 人们逗乐的对象。只要他一出现,立即吸引来一大群 孩子和狗,人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他穿着难看的 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或是光着脚 ,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 门口站住,向人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 点面包,还有人给他几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 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落入 了尼基塔的口袋。这个老兵总是毫不客气地、粗鲁地 、气急败坏地翻遍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嘴里喊着“ 我最恨不守秩序的人,上帝作证,我再也不放犹太人 上街”之类的话。” 莫谢伊卡乐于助人。他端水给同伴,替睡着的他 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上街回来给每人一个小钱,并 且给每人缝了一顶新帽子。他左边的邻居瘫痪在床, 他还用勺子喂他饭吃。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怜悯他们, 也不是信奉什么人道主义,他只是在模仿他右边的邻 居格罗莫夫的行为。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就是那个贵族出 身的人,三十三岁,做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 文官,他是因为患被害妄想症(一种精神疾患,自以 为受人迫害)进来的。他很少坐着,不是躺在床上缩 成一团,就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 骨。他似乎在惊慌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总是一副十分 兴奋、急躁、紧张的样子。只要外屋出现一点动静, 或是院子里有人说话,他就会立即竖起耳朵听着,想 是不是有人找他?要把他抓走?这些念头让他的神色 变得极其惊慌和厌恶。 我喜欢他那张脸,那是一张方脸,颧骨突出,脸 色苍白,神情悲伤,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出他那饱 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深沉而真诚的痛苦,造就 了他奇特的、病态的脸相,但他那清秀的面容,温暖 的眼神,又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 我也喜欢他本人,他总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 有的人都十分客气,除了尼基塔。每当有人掉了扣子 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跳下床,拾起那件东西,递给 对方。每天早晨他的同伴们都能听到他问候早安,晚 上睡觉时又听他祝福晚安。 当然,他的疯病不会只表现在他惊慌的神态和病 态的脸上,还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上:有时在傍晚,他 会表现得像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紧紧裹着那件破旧 的病人服,全身哆嗦,牙齿打颤,在墙角之间、病床 之间飞快地来回走动。有时他突然停住,站在那里看 看他的同伴们,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一会 儿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不停地走动,好像是他考 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 他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可不一会儿,这些顾虑就被说 话的欲望压倒了,他就开始做一番热烈、激昂的演讲 。他说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呓,有时急促 得让人听不明白,但他的言谈、声调给人的感觉十分 美好。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又像疯子,又像正常人 。他的疯话是无法述诸笔端的。他述说人的卑鄙,述 说践踏真理的暴力,述说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述说 这些铁窗总是让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他的话 就像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虽是老调重弹,却似乎 永远也唱不完。P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