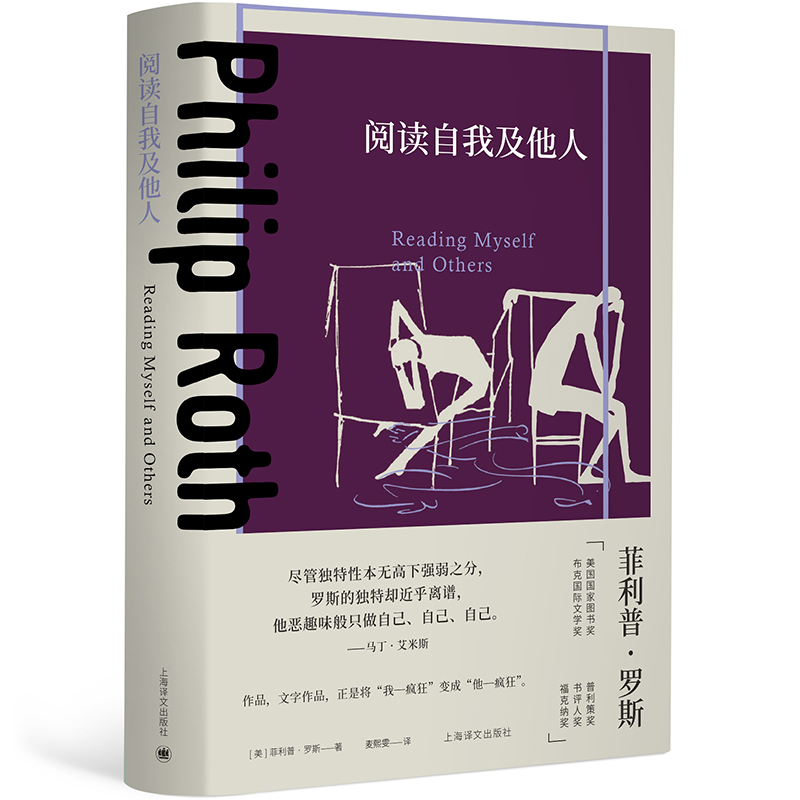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0.70
折扣购买: 阅读自我及他人(菲利普·罗斯全集)
ISBN: 9787532791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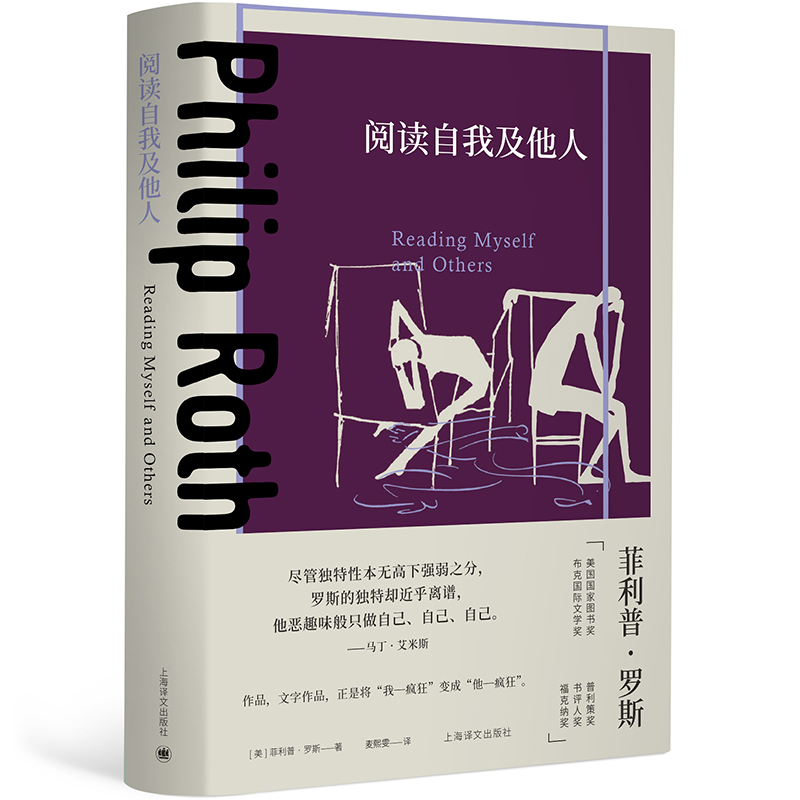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菲利普?罗斯(1933-2018)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1959年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受到瞩目,此后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2012年宣布封笔,一生共创作29部小说,代表作有《波特诺伊的怨诉》《鬼作家》《萨巴斯剧院》《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等。 "
"【精彩书摘】: 谈成名、争议、反犹指控: “名声,”里尔克曾写道,“不过是所有围绕刚刚崭露头角的名字的误解之总和。” 成为名人就是成为品牌。我们有“象牙香皂”“香脆麦米片”“菲利普?罗斯”。“象牙香皂”是能浮在水上的香皂,“香脆麦米片”是能在嘴里发出脆响的早餐麦片,“菲利普?罗斯”是用一片肝脏自慰的犹太人,还从中赚了一百万。出名就是这么回事,半个小时以后就不会更有趣、更有用或更好玩了。人们以为出了名能给作家带来更多的读者,但其实名气只会给多数读者带来障碍,读者必须越过这个障碍才能直接感知作品。 媒体篡夺了文学的审视作用,篡夺并将其庸俗化。美国媒体当前的趋势是将一切庸俗化。将一切庸俗化对美国人的重要性不亚于镇压对东欧人的重要性,而如果说则会个问题在国际笔会还没有变得像政治镇压那样臭名昭著,那是因为它脱胎于政治自由的世界。美国文明受到的威胁不是某些非典型的学区审查这本或那本书,也不是政府试图封杀这条或那条消息,而是信息泛滥,渠道超载,是对各种事物的不加审查。而将一切庸俗化恰恰源于东欧或苏联所没有的,即说任何话和卖任何东西的自由。 我从反对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是他们将尖叫着的我拖出英文系。他们是被我的作品所激怒的真实的人,不会为读过的作品写论文。他们只是气愤。这真让人惊喜。 生为犹太人是一种异常复杂、有趣、道德要求严苛无比,又非常独特的经历,我喜欢这种经历。我看到自己作为犹太人而身处历史性的困境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谈艺术与生活: 纪德说:“艺术是一种被夸大的想法。” 采访之前,我读了《鬼作家》,我想当然地认为你就曾是那个年轻作家内森?祖克曼,而洛诺夫——祖克曼非常钦佩的一位严肃的苦行僧式的老作家——是马拉默德和辛格的结合体。但现在我认为,你在新英格兰过着半隐居生活,和洛诺夫不无相似;你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写作,换句话说,就是洛诺夫所谓的,全部生活几乎就在“将句子颠过来倒过去”。你是洛诺夫吗?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是否认同作家作为隐士的理想,即作家为了艺术而必须做一个远离生活的自我任命的僧侣? 艺术也是生活,你知道的。独处是生活,冥想是生活,伪装是生活,想象是生活,沉思是生活,语言也是生活。将句子颠过来倒过去难道就比制造汽车少些生活吗?阅读《到灯塔去》难道就比给挤牛奶或者扔手榴弹少些生活吗?文学事业的与世隔离——不仅仅是清醒着的大部分时间独自坐在屋里——和在巨大的喧嚣中日益增多的轰动一时的人或事或跨国公司一样,也与生活息息相关。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艺术,我才有机会至少是我自己的生命的核心。 我是洛诺夫吗?我是祖克曼吗?我是波特诺伊吗?我猜,也许吧。很可能是。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像书里的人物那样被如此清晰的描绘出来。我仍然是无定形的罗斯。 讽刺艺术最彻底地升华了,或者说社会化了,这样一种情感转变:起初渴望用拳头杀死你的敌人,然后(多半因为惧怕随之而来的后果)转变为试图通过谩骂和侮辱杀死他。这是痛揍某人的原始冲动在想象层面的开花结果。 谈阅读、写作、作家: 我读小说是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狭隘人生观,让自己被引诱到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中,它有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完整的叙事视角。我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从事写作的。 读小说是一种深层的独一无二的快乐,是一种让参与者全情投入的神秘的人类活动,不需要任何附加的精神或政治理由,就跟做爱一样。 我想要的是读者在读我的小说时完全沉浸其中——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一种跟其他作家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沉浸其中,然后再让他们按原样回到那个所有人都忙着改变、说服、诱惑、控制其他人的世界中。最好的读者来到小说中是为了远离那些喧嚣,为了给那个被小说以外的所有东西所塑造和约束的意识松松绑。 我不会为了赢得一场战斗而去写一本书,我宁愿跟索尼?利斯顿打上十五个回合。那样至少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就可以去睡觉了。而写完一本书,幸运的话,也要花上两年时间。一天八小时,一周七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笔耕不辍,这是我知道怎么做的唯一方法。你不得不独自坐在屋子里,只有窗外的一棵树跟你交谈。你不得不坐在那儿,一稿接一稿地产出大量的垃圾,像一个被忽视的婴儿等待一滴母乳。 对我来说,作品,文字作品,正是将“我—疯狂”变成“他—疯狂”。 文学不是心灵美的选美大赛。文学的力量源自你在扮演另一个角色时的说服力和冒险精神,看的人相信与否才是评判的标准。 写作对我而言并不像鱼会游、鸟会飞那样是自然而然就完成的事情。它在某种刺激之下发生,有种特殊的紧迫感。通过反复的角色扮演,私人的危机转化为一种公开的“act”——这个词既指一个行为,也指一种表演。将你生命中那些与你的道德感相抵触的特质像虹吸一样抽取出来,对你和你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非常艰难的精神训练。你可能感觉自己表演的不再是腹语或者模仿,而是吞剑。有时候,你会太过为难自己,因为你真的是在伸手抓那些你触不到的,或者说你生命之外的东西。普通人都有该呈现什么、隐藏什么的本能,但是伪装者是不能放任自己去听从这些本能的。 阅读的东西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我工作期间也一直在读书,通常都是晚上读。这是保持“电路”畅通的一种办法,也让我在思考我所从事的行当的同时,能从手头的工作中抽身休息片刻。它给我的帮助是至少能为我完全沉溺其中增添燃料。 继续写小说的一个动力是对“立场”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包括我自己的立场在内。这并不是说你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就把所有思想上的包袱都留在门外,也不是说在小说里你会发现你所想的和你告诉读者的其实背道而驰——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说明你可能太糊涂了,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我想说的只是,我通常并不清楚自己在谈什么,只有在我停止谈论一件事,把它送到小说制造机锋利的刀口下,把它打磨成其他什么东西,不管它什么,反正不是什么“立场”,它能让我在完成以后说:“好吧,尽管这其实也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但已经比较接近了。”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清楚自己在谈什么。 纯粹的游戏态度和致命的严肃关怀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一天结束的时候,是它们陪伴我在乡间漫步。还有“致命的游戏态度”“游戏的游戏态度”“严肃的游戏态度”“严肃的严肃关怀”以及“纯粹的纯粹性质”,我也和它们交好,但从最后那个家伙身上毫无所得;他只会拧绞我的心脏,让我无话可说。 想想腹语者吧,他说话的方式让人觉得他的声音来自一个离他有段距离的人。但如果他不在你的视线之内,他的艺术就不能带给你任何愉悦。他的艺术是既在场又缺席;他在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同时,最贴近真实的自己,其实幕布降下来后,他两者都不是。作为作家,你不一定要将自己的真实过往全部丢弃,才能扮演别人,保留一些有时更吸引人。你歪曲、夸大、戏仿、变形、颠覆、利用你的人生,让你的过往增添一个新的层面,去刺激你的文字活力。当然,成千上万的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没有文学创作这个借口。他们并不把这当成表演。在他们真实脸孔这张面具后面,人们能长久经营的谎言是让人惊叹的。想想那些出轨的人技艺多么高超吧:平凡的丈夫妻子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被发现的危险,虽然上台会紧张得动弹不得,但在家庭这个剧场里,面对着已经遭到背叛的配偶,以无可挑剔的戏剧技巧演出清白和忠贞。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表演,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都洋溢着才华,一丝不苟地自然表演,这些人全都是彻头彻尾的业余演员。人们都在完美地演出着“自我”。 谈厌女: 我只能告诉你,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问世几年之后,一篇女性活动家的头版文章出现在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曼哈顿周刊《村声》上,文章用了《为什么这些男人仇恨女人?》这样强有力的标题,标题下面是索尔?贝娄、诺曼?梅勒、亨利?米勒和我的照片。《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就成了指控我的最具破坏性的证据。 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九七四年,世界才刚刚发现女人是好人,且只有好女人;她们受到迫害,且只有受到迫害。但我写了一个坏女人,她迫害、利用他人,这可就坏事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滥用一切权力,睚眦必报,无比狡猾和狂野,不分对象地仇恨和愤怒。写这样一个女人是违反新伦理的,也和拥护它的革命相悖,是反革命的,站错了立场,触犯了禁忌。 谈美国: 美国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去从事我的职业。美国有我想象中唯一对我的小说有持续热情的文学读者群。美国是我在世界上最了解的地方,也是我唯一了解的地方。我的意识和语言由美国塑造。我是一个美国作家,跟水管工不是美国水管工,矿工不是美国矿工,心脏病医生不是美国心脏病医生一样。美国之于我,就像心脏之于心脏病医生、煤炭之于矿工、厨房水槽之于水管工。 谈《我作为男人的一生》: 即使仅仅为了去写如何做一个病人,你也必须能够成为你的医生的医生,而这基本上是《我作为男人的一生》部分的主题。之所以我会对病人感兴趣——在我接受分析之前四五年写《放手》的时候就有兴趣——是因为有那么多开明智慧的当代人士接受了自己是病人,并接受了“心理疾病”“治疗”“恢复”那些概念。你刚刚是问我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吧?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精神分析需要的八百个小时和看完《波特诺伊的怨诉》所用的大概八个小时之间的关系。人生很长,而艺术更短。 谈自己: 我是一个干劲十足地努力要把自己从自己变成那些生生不息、不断变换自己的主人公的人。我也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写作的人。 " "【编辑推荐】: 这些精彩的访谈、随笔和文章,出自普利策奖获奖作家、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菲利普·罗斯之手,它们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聚焦写作、棒球、美国小说和美国犹太人,等等。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读到罗斯如何看待自己、他的作品及其所引发的争议,而且可以读到罗斯与同时代东欧作家的交往,他对他们作品的引介和推崇。而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罗斯对卡夫卡,这个他终其一生仰视的文学偶像别具一格的致敬:他设想了一种“如果”——卡夫卡成功移民美国,以一个普通犹太裔美国人身份走进了犹太小子菲利普·罗斯的生活,在掀起一场家庭风暴后又黯然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