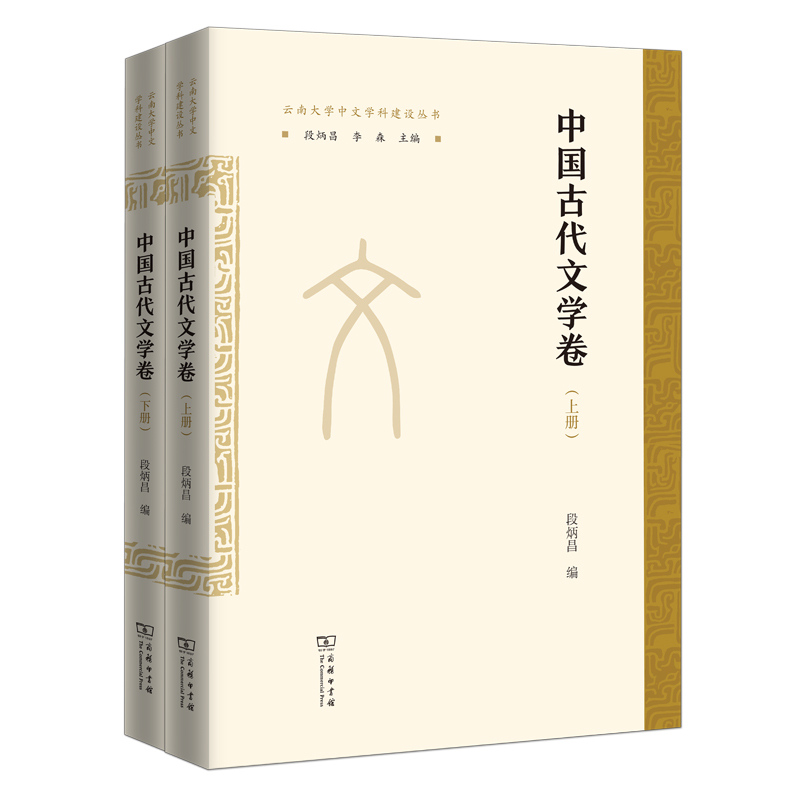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205.35
折扣购买: 中国古代文学卷(全两册)/云南大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ISBN: 9787100215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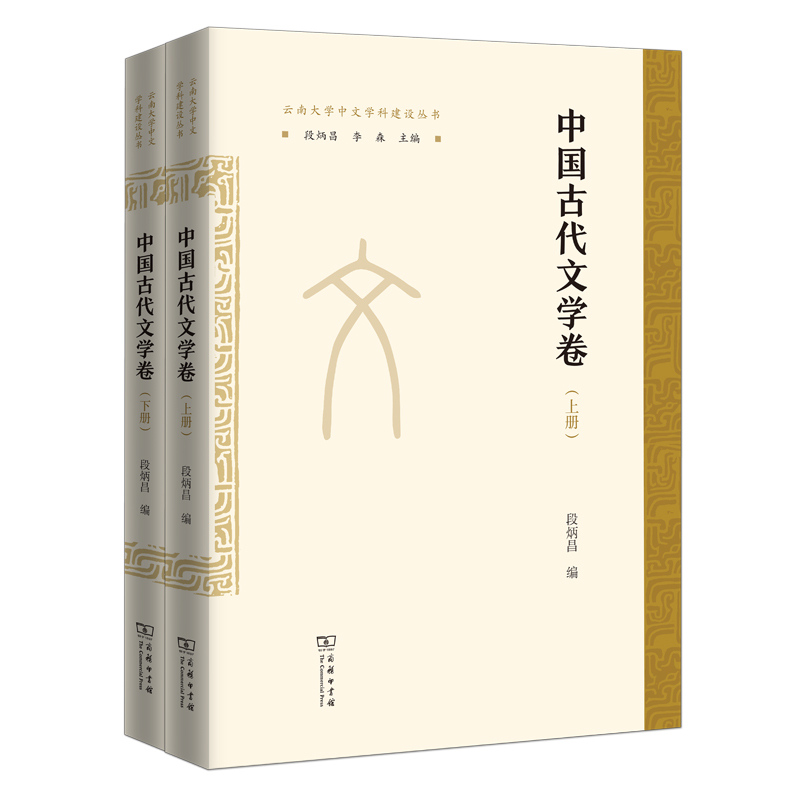
段炳昌,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地方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出版著作(含合著)16种,发表论文60余篇。
如果说,诗人因秋天的草木摇落而产生了“悲哉”之情,那么按逻辑应写作 “草木摇落而变衰,萧瑟兮;秋之为气也,悲哉!”因为以物起兴,应该是客观世界的变化———春天的妩媚和夏天的繁茂都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草木摇落”的秋天的萧瑟。正因为有了客观的“秋之为气”,方能使人的情绪受到感发,才有所谓“悲哉”的感情的波动。正如杜甫说的“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是先“摇落”而后知“悲”也。然而宋玉却先写“悲哉”,而后述“摇落”,这绝非思维逻辑的颠倒。谁也不会赞成把宋玉的诗倒过来读的。 秋天草木的摇落,是乃大自然的规律之使然,古往今来,年年如是。科学家视寒来暑往为自然的物候,岂必动情;哲学家识新陈代谢之哲理,应无伤感。人生百年,岁岁经秋,世间苦乐,因人而殊,未必个个伤悲,处处萧瑟的。就是诗人,吟到秋风的也并非个个一般情怀。李白有诗曰:“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与宋玉之诗恰好反其意而用之,秋天倒增加了这位豪情跌宕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飘逸之兴, 他竟至视别人之“悲秋”为无谓了。杜牧诗有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这不是悲秋,简直是爱秋了,火红的枫叶秋色在这位晚唐诗人的笔下,仿佛比春天更富于诗意,更令人神往。可见宋玉写《九辩》时的“悲哉”之情,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他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心境的一种反映,是他彼时彼地的主观思想感情的流露。 应该说,诗人内心先有了悲伤之情,所以才会落叶伤秋,飞花惜春。情生意象,景因情异,所以不同的诗人和不同的诗作有不同的意境。宋玉正因为心中早有“悲哉”的情绪,才会有感于“秋之为气也”,萧瑟之感,出自内心, 寄托于客观世界的物候变幻,遂因草木摇落和自然衰朽而动容。有人说,文学艺术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的产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大自然的影象来。 我以为这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只限于对客观世界的纯粹的描摹,而没有人的思想情感的移入融汇,哪里还有什么意境,又哪里还有真正的诗!古人说“言为心声”,信有以也。梁任公有言:“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为真实。”(《饮冰室专集》:《自由书·惟心》)如果从强调诗境中必不可少的主观情感的作用而言,这说法是对的。 不能把“惟心所造”理解为唯心主义(这里且不探讨哲学概念)。任公所言“心造”者,诗境也,也就是诗学中常说的“意境”。仅有客观存在的亘古不易的“物境”,未必有意境,亦未必有诗。故必先有“心造”之境,方能寄情于物,托辞悲秋。刘勰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诗品序》)可见心之悲也,才会有感于“物色之动”,才会感发于秋气,才会有千古悲秋之句,才会有耐人玩味的“境界”。否则,物色永远在动,悲喜哀乐又为何因人而异呢?此之谓 “心造之境”。 见证文脉传承,一览云南大学身后的古典文学研究风貌和云南一地的文学研究状况 。1.本书的出版,完善了此丛书,更有利于读者系统了解云大中文系的发展历程。 2.所选文字均为在云南一地待过或者教研过的学者,选其代表性文章,展示文脉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