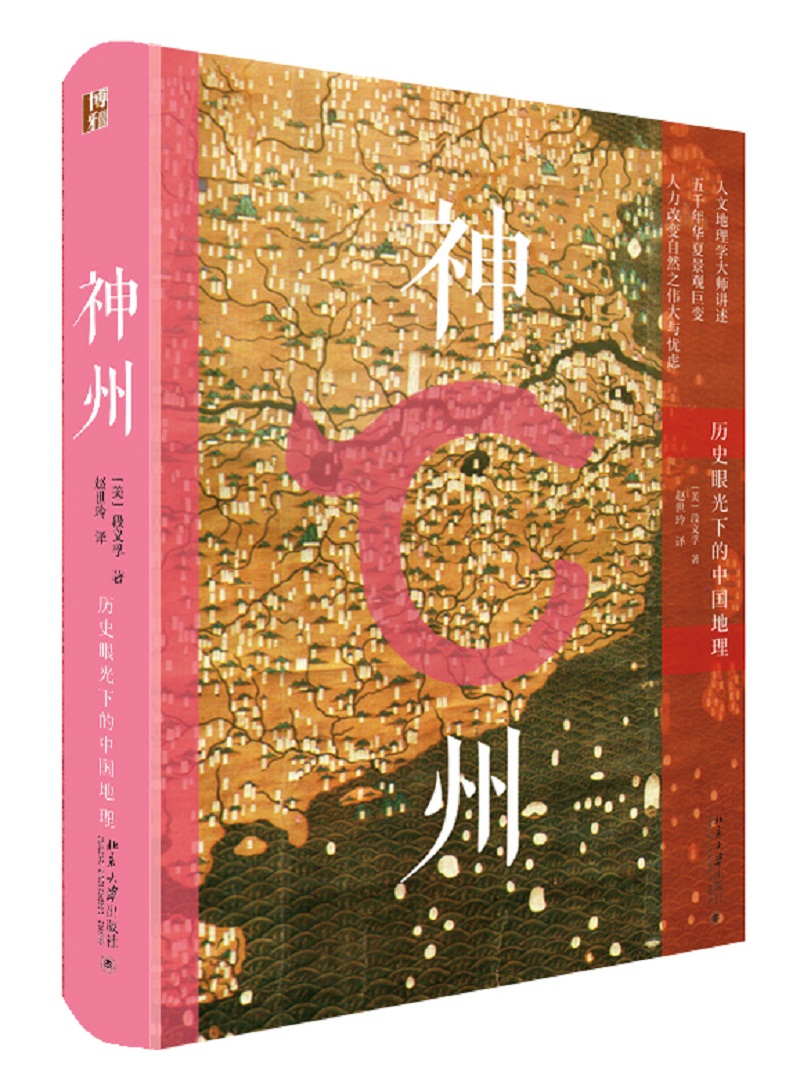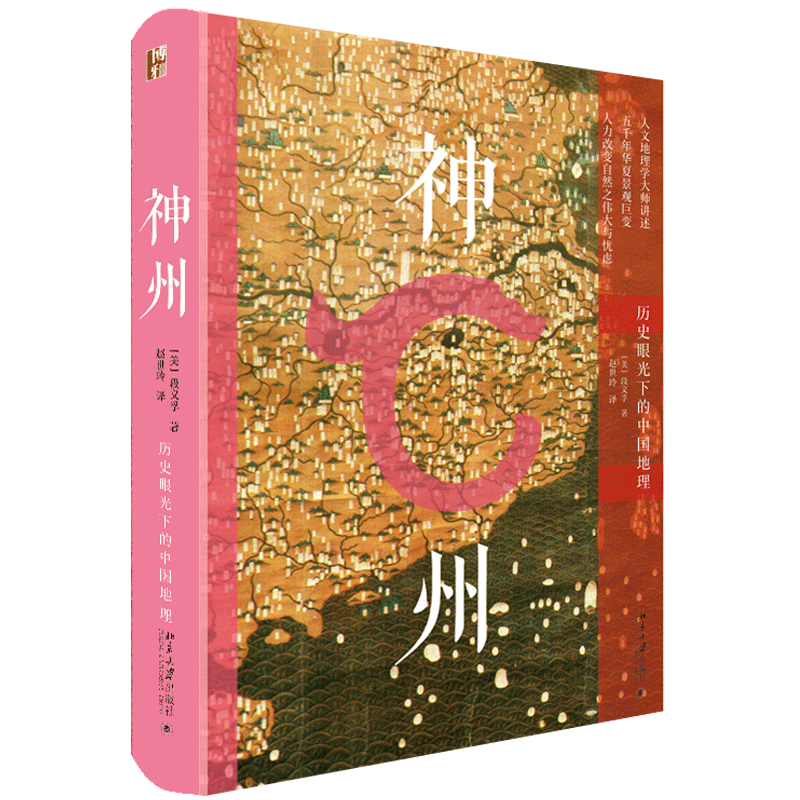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ISBN: 9787301293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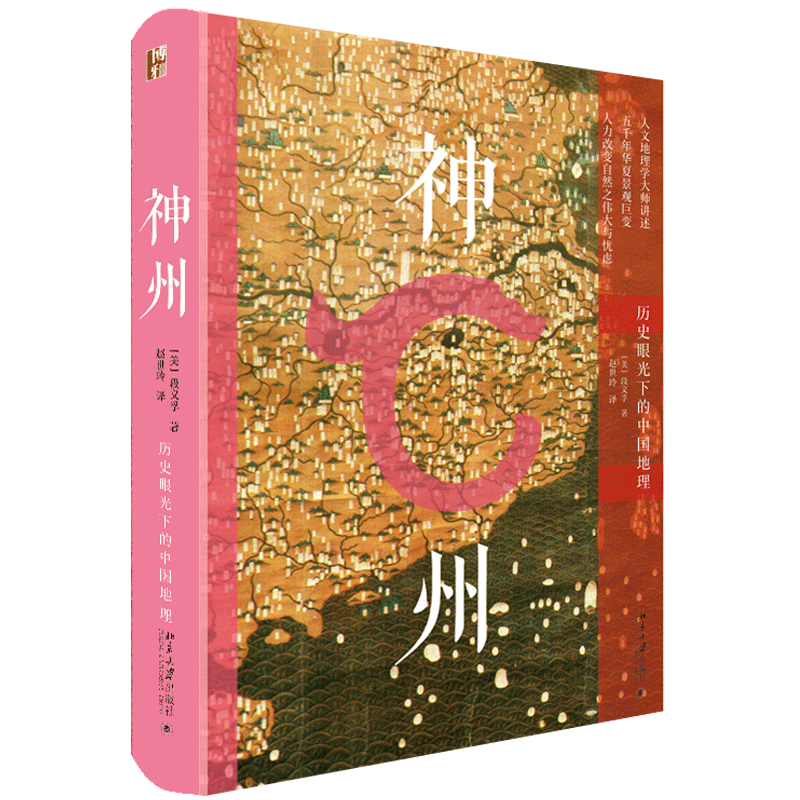
" 段义孚(Yi-Fu Tuan),1930年生于天津,后移民澳大利亚,先进入牛津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 段义孚是公认的当代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尤其是作为 humanistic geography的大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并对西方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华裔学者中很少见的。 译者简介 赵世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居加拿大。 "
第三部分 中华帝国时期的景观和生活 第五章 秦朝至唐朝 五 东汉帝国:人口的骤减与南迁 如果说公元2 年时汉帝国的人口是5800 万,到公元57 年,据报告说下降至2100 万。毫无疑问这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在那时东汉帝国的人口似乎不可能少于4000 万或4500 万。[25] 当然,人口无疑是下降了,但不可能下降的那么多。在这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帝国内部发生了内部战乱、农民起义(赤眉军)、对匈奴及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洪水、饥荒、瘟疫,等等。 大自然所造成的洪水泛滥加剧了内乱、人口迁徙、饥荒、死亡。在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 年—公元6 年),黄河泛滥淹没了部分大平原,在山东半岛的南部冲出一道支流汇入淮河。在公元11 年,黄河再度屡屡决口,原来向北的分支甩向东南方,离开了今天津附近古已有之的入海口。南分支涌入古老的汴渠 。汴渠流经大平原上一个低洼带。从那里通向海边的坡度非常平缓,所以洪水蔓延,淹没田地。直到公元70 年,淹没汴渠两岸的洪水才退去。[26] 洪泛使数百万人遭灾。在黄河改道之前,黄河以南的大平原养育着中国总人口的几乎一半。洪泛使众多人口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们主要向两个方向逃亡,一些人向东,进入仍旧被黄河两条河道环绕的山东半岛的高地。另一些人分三股向南迁移:一股进入长江三角洲,一股到鄱阳湖盆地,然后上溯至赣江;最后一股到了汉江流域, 进入洞庭湖盆地,然后上溯至湘江。 到公元40 年时,虽然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受黄河泛滥的困扰,但中国在东汉王朝统治下完成了政治统一。自那之后,人口逐步增加,在公元140年至160年间达到5000万至5500万的高峰。在公元140年,东汉帝国统治下的人口仍旧比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少大约800万,但是从国家今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口在地理分布上所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在公元2年,中国人口以压倒之优势集中在北方。到公元140年时,集中的程度已大大降低。在那个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渭河-汾河流域减少了大约650万人,华北大平原减少了1100万人。秦岭至长江三角洲一线以南地区则增加了900万人口。湖南、江西和广东的人口增加了4倍。[27] 西南部纳入中国统辖之下,自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建立起来。帝国的南部边陲实际上远至安南(越南北部)。 但是在中国南方,比如在东南沿海,还有长江中游大湖地区周围的沼泽地带,仍有大片地区人烟稀少。山岭上丛林密布,蛮荒一片,人迹罕至。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欣赏这样的景色。西汉时的一首诗表达了诗人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对峥嵘粗犷景色的恐惧,诗中说“桂树长的如此浓密”,它们的枝叉“纠结缭绕”: 山曲岪……虎豹穴…… 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 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 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 (《楚辞·招隐士》)[28] 六 豪门大族的庄园 汉朝时农民的生活极其艰辛。根据晁错的记载(公元前178年),“在夏日他们无法躲避炎热酷暑……在冬天他们必须承受严寒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能停工休息”。在东汉时期小农的生活仍旧很苦。 虽然理论上农民受到尊崇,实际上备受轻蔑,状如草木牲畜。小农的苦难来自何处呢?苦难根源显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战国时期。当封建制度崩溃之时,起初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成为自耕农。他所耕种的田地多少归他所有。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延续多久。大地主将封建诸侯取而代之,他们兼并土地,开垦荒地,大地主应付天灾人祸的能力远非一般小农可比。 在汉朝期间富有的地主权势日大。他们成为“豪门大族”,这些新贵取代了过去的封建王侯。豪门大族以一个扩大的父系家庭为中心,此外包括很多通过政治经济关系依附其下的家庭和个人。越来越多的农民不能靠自己田地所产度日,他们发现依附有财有势的豪门大族不失为便利之举。 在东汉时期,很多大庄园面积达数万亩之阔,它们展现出何样的景观风貌呢?首先,这些大地产资源充裕,不缺劳力、耕牛、一般牲畜、种子。在一个大地主的庄园上,除了像糯小米、普通小米、稻子和麦子,还栽种数十种其他作物,包括亚麻籽、葱、蒜、苜蓿、萝卜、各种甜瓜、倭瓜、芹菜、葵菜、豆、水蓼、芥末等。树木包括竹子、漆树、桐树、梓树、松树等。[29]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高度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除了庄稼,还栽种种类繁多的蔬菜、水果、观赏树木。 大地主可以实验新的耕作方法,例如赵过的代田法和氾胜之的区田法;他们也能够使用像水磨那样的新机械。大庄园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数百,肥田沃土连绵阡陌,奴仆成千上万,货物车运船拉,运往全国各地。他堆满的货栈遍及全城,巨大的房屋装不下珠宝财富,山谷中放牧不下他的马、牛、羊、猪。[30] 以上的段落引自当时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豪门大族不仅务农, 而且经商,并拥有成群结队的牲畜,数量之多,以致山谷中放牧不下。如果说的是欧洲,我们可能应设想一个豪华的乡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宫殿坐落在园林环绕的景观之中,周围环绕着农庄和务农的村落。但是这幅图景不适用于中国。以上所说的乡村宅邸可能阔大而兴旺,但是一般来说在建筑上却朴实无华。家族中胸少文墨,却野心勃勃的成员住在那里经营产业。那些饱读诗书,出相入仕的成员们则成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城中住宅可能雄伟壮观。还记得为了摧毁各地封建势力,秦始皇命令权贵们将府邸迁到京城中吗?汉朝延续了这个政策;不过只是豪门大族的家主们必须搬到京城之中,处于王朝的监视之下。京城毕竟是功名利禄发源之地,凡有雄心者都趋之若鹜。在城市府邸中饱读诗书的有钱士绅们可以悠闲地吟诗作画,但他们更常选择入朝做官,跻身于回报丰厚却危机四伏的政治角逐。如果不幸失去朝廷欢心,这位官员可以乞假还乡,不失体面地过着道家文人的日子。同样,当内乱发生,儒家官宦自然而然向往乡村中的道家风景。就此而言,仲长统(公元180 年—220 年)的白日梦并非绝无仅有: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林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31] 八 佛教对景观的贡献 大分裂时期也是文化创新的时代。内部纷争和五胡乱华震撼了儒学思想体系和帝国官僚机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新是佛教,佛教对华夏文化和景观的影响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记载说佛教僧众团体在长江入海口附近,时间是公元65年。最早关于佛寺和佛楼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90年。这片建筑包括一座两层的佛塔,上面立着的塔刹有9层青铜相轮,屋顶覆盖的长廊可以容纳3000人。[39] 在公元3世纪时佛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广得人心,在战乱割据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到4世纪初叶,西晋王朝的大城洛阳以拥有42座佛塔寺庙为荣。在突厥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统治下(386年—535年),佛教僧侣的数量在中国北方达到200万人。在中国南方,佛教传播可根据寺庙的增长略见一斑,以下是在迅速更迭的各朝各代寺庙的数目。[40] 朝代 寺庙数目 东晋 (317—420) 1768 刘宋 (420—479) 1913 齐 (479—502) 2015 梁 (502—557) 2846 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表明,一种新的外来宗教成功地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道传统之上。这一文化创新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华 夏景观增添了新鲜要素呢?数量可以说明程度。在中国南方梁朝的统治之下,总共2846 座寺庙中住着82700 名出家人。在北魏帝国,大约500 座庙宇散布在京城洛阳的城里城外,庙产达可利用土地的三分之二。[41] 佛教成为朝廷认可的宗教,佛教屋宇殿堂体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修起了围墙,建造了高大的门庭,辟出庭院 ,造起游廊和巨大的殿堂。到唐朝时(公元618 年—907 年),尤其是那些位于京城长安的一些寺庙宏伟巨大,修饰奢华。比如位于长安东门的章敬寺有庭院48 重,房屋4130 余间。于656 年完工的西明寺虽然只有10 个庭院, 4000 余个房间,却更加壮阔。“在寺庙之外,树林环绕为界,地上溪流纵横。在寺庙之内,亭台殿堂高耸入云,大柱上贴着耀人眼目的金箔。”[42] 唐代时,诸如寺庙、寄舍,或是一般修行之所这类佛教设施点缀着城外的景观。这些地方不仅常为游方和尚们提供膳宿,而且为旅行的官吏、军事统领和商人们服务。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宗教性的寄宿之地每隔5 至16 公里就有一处。其中有些十分宽大,因为有个寄舍为100 多旅人提供膳宿。一些奢华的寺庙坐落在山中或是山脚下广阔的寺庙地产中,庙产包括森林、灌木覆盖的丘陵坡地、草原、耕地。这些地方可被视为平安美丽之所,但是它们的存在却以宗教狂热、世俗财富和寺庙奴隶的汗水为基础。 我们的问题是,在何等程度上这些佛教设施在建筑上与众不同, 使我们可以谈论华夏景观中的佛教要素呢?我们的答案是,起初佛教寺庙几乎同所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建筑相差无几。正如前文提及, 对东汉时一个江苏寺院的描述提到一个独特的两层佛塔。其新颖之处是楼顶上的塔刹,装饰着一层层象征性的相轮。在佛教传播的后来阶段,寺庙越来越雄伟壮阔,其中最大的在规模上可以同朝廷的宫阙争奇斗胜。它们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几乎一切特色。不过一个 重要的例外是佛塔,这是一种多层建筑。洛阳市中心的永宁寺自公元516年开始兴建,“这是一座木结构的9层佛塔,高270米,塔顶的塔刹高30米。在京城方圆100里内清晰可见”。这段叙述可能有所夸张。塔大约实际只高出寺庙地面90或120米,但是其高度肯定足以引人注目。[43] 直至19世纪后期,当欧洲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沿海省份之前,佛塔是华夏景观中最与众不同的外国建筑。佛教虽然由印度传入,佛塔的建筑渊源却不太清楚。除了塔刹和上面的华盖装饰,中国木塔同印度石头修建的萃堵波并无相似之处。就其建筑要素来说,4世纪时的3层木塔似乎更像汉代的瞭望楼(台),如果再向古代回溯,似乎像周朝封建天子们用于取乐或狩猎的楼台。[44] 在另一方面,有记载说中国佛教采用塔为祭拜建筑是因为受到印度贵霜帝国(Kushan)佛教建筑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经塔里木盆地沙漠绿洲城市传至中原。[45] 木材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材料。但是早在公元6世纪,有些佛塔几乎成了实心砖柱。就其外观,就其使用砖石,尤其是就其装饰细节来说,这些佛塔反映出强烈的印度影响。 十 唐代:不断拓展的边疆 根据742年的人口普查,唐朝时中国人口是5150万。但是有人认为数字实际要高些,可能有7400万。隋朝609年普查以来的人口增长要归因于从640年延续到755年唐朝统治下的太平盛世。[51] 在唐朝的扩张阶段,帝国对西部和西北部的部落和国家大加征伐。到7世纪中叶,唐帝国击败了西突厥,再次将势力扩大到塔里木盆地以远地区。但是在751年,唐朝军队败于大食军队(阿拉伯人)。失败的间接后果是塔里木盆地绿洲一带永远改变的文化景观。 佛教建筑、寺庙和萃堵波被西方宗教,尤其是胜利的伊斯兰文化的建筑所取代。穆斯林圣地、寺庙、学校和集市保留至今,成为西域绿洲景观的特色。 唐帝国的失败和收缩使佛教从塔里木盆地退却,但在另一方面,唐朝则促使佛教在吐蕃(西藏)的传播。在公元641年,唐朝将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这位首次统一西藏的领袖。公主随身带去释迦牟尼的大尊佛像、几卷佛经和一些有关医药及占星术的典籍。[52]西藏独具特色的文化影响来自中国和印度,在二者中印度影响更为重要;这种双重来源的象征是西藏的统一者不仅迎娶了中国公主,而且还有一位尼泊尔公主。据悉在西藏至少有三座著名的寺庙可以回溯到这个最早的历史时期, 这是西藏文化中心雅隆河流域的昌珠寺(Trhan-tr’uk)、拉萨盆地的大昭寺(Trhul-nang)和小昭寺(Ra-mo-che)。修建拉萨的两座寺庙最初是为了供奉松赞干布两位妻室带进西藏的佛像。相传被 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今天香客们顶礼膜拜的中心。[53] 不论如何牵强附会,藏族传说急于将当地习俗归之于印度。传说藏人用大麦酿造啤酒,制作酥油和奶酪的技术起源于那个时代,这类食品属于印度或西南亚文化而非从中国传入,因为汉族人总的来说不习惯食用奶制品。不过在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松赞干布的孙子把茶从华夏大地传入西藏。[54] 茶成为藏族人的民族饮料,他们一天要喝30 至70 碗不等。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茶——酥油茶,是印度和中国影响的混合物。 在中原大地,唐朝时人们主要向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移民。到8 世纪中叶,总人口的几乎一半住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移民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战争、突厥人和吐蕃人的骚扰、饥荒、洪水以及诸如横征暴敛、强征民夫、日益扩展的佃农制度这类社会不公。换言之,同以前引起移民的原因大致相同。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即在秦始皇统治下,朝廷发布敕令向南方移民。在长江以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在唐朝时,东南沿海完全同华夏帝国融为一体。以长江支流赣江为中心的江西不再自成一统,到8 世纪中,江西人口首次超过湖南。 南方和东南沿海人口增加,日益繁荣,这得益于兴旺发达的商业。8 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们扩大了贸易活动,他们先在珠江三角洲, 后在福建和江苏建立商行。波斯和日本商人们也往返于东南沿海做生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活动中心是长江三角洲以北的扬州。760 年时扬州爆发了一场骚乱,导致数千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死亡,这个事实可以佐证这些外国商业社区的规模。 向南方殖民并不是朝廷刻意所为,而向北方边疆的移民确是朝廷政策使然。唐朝时朝廷占有大片土地,其产出的收益用于支付官吏薪俸、维护朝廷建筑以及饲养马匹。北方广阔地区被圈为草场,为国家放牧马匹。马对于帝国的安全举足轻重,所以需要大片草场放养。在7世纪中期,唐帝国饲养存储的马有70万匹之多,分布在渭河流域以北的8大牧场上。[55] 除了建牧场之外,朝廷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向佃户收取地租充实国库。 除了这些土地,朝廷对其他国有土地的开发具有更直接的考虑。其中一类成为屯田,即是由亦兵亦农的聚居地所开垦的土地。屯田制源于西汉,目的是占据并保护新近平定的西北部疆域。在唐代,殖民性屯田制度具有类似的功用,是为了保护疆域并建立村落,不过屯田数目远远超过汉代。到763年,在北方边境省份建立了超过900个军屯村落。这些屯田南起长城以南靠海的榆关,向西延伸到长城深入黄河大几字弯地区,并沿甘肃河西走廊的绿洲向西到达吐鲁番盆地;屯田也建在西藏边境的山谷中,位于青海湖以东。根据土壤的肥沃程度,也根据栽种旱地作物或是灌溉农业,屯田面积从2200亩至5600亩以上不等。大些的屯田可能驻扎着数百名农夫兼士兵。一些遥远地区的肥沃土地似乎缺乏劳力。比如河西走廊上的绿洲甘州就没有足够的人去定居。正如684年一份递交皇帝的奏折所说的, 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灌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工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石)不为难得。(《陈子昂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56] 十一 繁荣昌盛的经济和景观 唐初的数十年远非太平盛世。但是自从640年以后,直至755年到765年间的安史之乱,唐朝一片和平兴旺景象。唐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在玄宗统治的年代(715—756年)。年景富饶平安,物价低廉。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店铺货栈为旅行的商贾提供货物,商人们长途跋涉,不用担心盗匪。除了平坦安全的驿道,纵横交错的运河漕渠从中国南方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运到北方的京城。 最主要的必需品是粮食。正如《新唐书》所记:虽然关中(陕西)以膏腴之地而闻名,但这个地区太过拥挤,物产不足以供给京城所需,不足以为洪泛和饥荒之年进行储备。所以从东南方将进贡的粮米运到京城。[57] 西汉时的主要问题是将粮食迅速地从华北平原运到渭河盆地,而到了唐朝,问题是将粮食从更加遥远的中国东南部运到古老的西北部。需要运输的粮食数目巨大。据记载,在735年左右的3年之间,运输了大约7百万吨粮食。[58] 主要是什么粮食呢?在汉朝时无疑是麦子和小米。但是在唐朝,中国东南部的主要作物可能是稻米。不过早在318年,当北方被匈奴攻占,晋朝宗室在建康(南京)称帝,麦子和大麦就传入水稻产区。据估算在4世纪时迁徙到南方的汉人有上百万,他们一定也对小麦种植在南方的传播有所贡献。[59] 向北方京城运输的生活必需品必须同日益增加的奢侈品竞争。奢侈品五花八门,来自广州的有珍珠、翠鸟羽毛、活犀牛。从广州向北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沿长江支流赣江,另一条沿长江支流湘江,同归于长江中游的湖泊平原;从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顺江而下到扬州,然后往北顺大运河和汴渠到长安。实际上从广州可以全程走水路,穿越南方丘陵到长江流域,再北上到华北平原、进入陕西黄土高原。虽然帝国的京城位于亚洲干旷大草原的边缘,运输货物却有水路相通。公元743年在长安东面挖掘了一个人工湖作为船舶转运地。薛爱华对此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在那一年,兴致勃勃的北方人……看到船只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船舶转运地,船上装载着向朝廷进贡纳税的各地物品:从北方来的是猩红色马鞍毡垫,从南方来的是朱红色柑橘,粉色丝织镶边的粗毛地毯来自东方,梅红色矾土来自西方。将货物装上驳船,驳船上的水手特地装扮成长江船工,他们头戴竹边帽,穿着罩布衫,脚蹬草履。[60] 西京长安的人口将近200 万。100 万住在城墙环绕的城里,另外一半在郊区。东都洛阳居民100 来万。在8 世纪时的唐代中国,人口超过50 万的城市有25 个之多。即使是南方和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 例如杭州、福州、广州,人口也有数十万。扬州居民大约有45 万。 到8 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可能达到7500 万。城市和农村人口增长说明农业产量相应增加。为何获得了这样的增长呢?因为在华夏大地中部和南部耕地面积增加,在北方对土地更加精耕细作。但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可能也有助于提高产量。在大分裂时期,农民占有小块土地,并从朝廷得到田地,允许他们耕作并受益终身。公元624 年唐朝颁布律令,重申“均田土”的原则。[61] 意在抑制土地兼并,保障普通农民的生存。但是很快,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富人开始向穷人买田。之所发生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唐朝的君主并不遵守自己颁布的律令。除了对有权有势者分配大田产,还任意对他们赠与田地。唐太宗曽赠与一位宠臣土地1000 顷,一座豪宅,300 户封地。为数众多的豪门权贵得到5 顷,10 顷或是上百顷田地、府邸、庄园采邑。[62] 而且在内战和安史之乱后,朝廷开始和豪强地主争夺地产。因为战乱所引起的破坏甚至使华夏中部存在大量无主土地,所以朝廷也加入土地兼并之列。[63] 总而言之,在唐朝统治期间,小土地占有制和自耕农让位于大庄园和富有的豪强地主。 虽然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令人叹息,农业生产却可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发展。大庄园主们有财力大量垦荒,小农却无法做到。豪强地主能够更好利用重型农具,例如三铧犁、耧犁(一种连犁地带播种的工具)和耙。他们有为数众多的耕牛骡马和雇工来实行6 世纪出现的“两年三田”轮作制。 十二 山川孕灵异:对自然的感知和保护 显而易见,到唐朝末期,人们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华夏大地的大片地区。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最尖锐辛辣的证据在于文字写作对植被的影响。如前所述,为中国庞大官僚集团制作墨汁需要把松树烧成煤烟,中国北方的松林因而被大量砍伐。由于雄伟壮丽的城市,由于行路的安全,人变得信心十足,对自然的美丽和脆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在汉朝时,尤其是南方森林覆盖的荒野那类大自然对人类仍旧是一种威胁,人们还无法领略自然的迷人之处和转瞬即逝的可爱。但是到了唐朝,自然似乎已从令人畏惧变成岌岌可危。从汉代诗人所作《招隐》,可以看出他们害怕云雾缭绕的山岭,害怕陡峭的深谷,人若跌入其间,则有去无回。但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却以其特有的玩世超然的笔调写道: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问答》)[64] 对自然的感受转化成律令,重新实施古代对庙宇辖地和圣明君主墓地四周的尊崇,这些地方成为不可冒犯的庇护之所,居住其间的所有生灵同受祭拜的死者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朝廷日益认识到森林的价值,发布敕令禁止纵火,禁止无故放火烧地,禁止在公共道路旁点火。[65] 既为了宗教原因,也为了实际目的,朝廷也努力保护分水岭。唐朝律令指出: 凡五岳及名山能孕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时祷祭焉。(《唐六典》)[66] 不论目的崇高还是卑劣,人类的繁忙劳动改变了大自然,改变的证据比比皆是。但是我们不应将唐代中国设想成一个土壤侵蚀,不见森林的国家,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南方,尽管定居的人潮涌进冲积谷地,那里浩瀚的常绿阔叶森林几乎还是人迹罕至。下列事实证实了那里的原始景观:到9 世纪时,广东的山野中仍然野象成群,犀牛仍然生活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湖南西部和南部。华夏北部也远比今天林木繁茂。比如山东,现在那里不见森林,土壤侵蚀,被极为稠密的人口所累。而在9 世纪初叶,那里似乎林木葱茏,气候潮湿, 人烟稀少。当日本僧侣慈觉大师在839 年去山东沿海途中,他遇到朝鲜水手。水手们正将他们在山东半岛烧的炭运到长江下游没有树林的平原。慈觉大师为我们留下难能可贵的史料,讲述当他穿越山东半岛山岭起伏的海岬时的情景: 从海州直到登州以来路境不可行碍,旷野路狭,草木掩合,寸步过泥,顿失前路……入山行,即一日百遍逾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树稠草深,微径难寻……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路次州县但似野中之一堆矣。[67] 慈觉大师的目的地是山西北部的五台山,那里有12 座宏大的寺庙和为数众多的较小庙宇,是唐代中国香客们顶礼膜拜的中心。在今天,除了树荫覆盖的庙宇四周和几个深谷之中,群山光秃无树。它们裸露的山梁和干涸、填满圆石的谷地同慈觉大师日记所述形成鲜明的对比。慈觉大师形容的景色是凉爽、葱郁的大地。山顶的松林和谷地中的树木笔直高大。高山花朵在高坡上盛开。在山顶的平地里冒出清凛的水流,在较深的谷地中甚至有长年不化的残冰。[68] 十三 长安:百万人的大城 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述了已知的物质环境以及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农业技术中的变化,力图展现出中国景观的一些风貌。需要更详尽讲述的是景观中的主要特色:城镇。实际上,华夏大地的人造景观中很少有比围墙环绕的城市更界限分明,更令人惊叹的景色。而且城市的基本格局在以后的年代中极少变化。当一个20世纪初的旅人走近一座中国城市,他遇到的是坚固阔大的城墙突兀矗立于田野之上;他所见到的城市同日本客人慈觉大师在唐朝的所见大同小异。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显然由于商业发展,新兴城市比比皆是,甚至于都城失去了它们的堡垒特性。秦朝终止了这一发展趋势,朝廷不支持贸易,力图以中央集权的控制来摧毁富有的世家大族,其极端性政策要求世家大族迁居到渭河流域的京都咸阳。其结果是咸阳面积扩大,财富增加,但以前诸侯封地中的市镇衰落。在秦朝短暂的统治期间也建立了新城,比如说长江以南湘江流域的郡都县城。但它们是政治行政中心,具有捍卫华夏势力堡垒的功用,在新近开发的国土上这种功用尤其重要。城市不论大小,日趋恢复周朝前期森严壁垒的要塞作用;不过秦朝时所建造的城墙既要控制内部居民,也要防守外部劫掠者的威胁。 西汉继承了秦帝国的中央集权政府框架,包括以首都为中心的道路体系和围墙环绕的城市这类物质性建筑,这些设施使独裁式控制模式便宜可行。汉代都城长安保持并强化自己作为众城之首无可争议的地位,城中宫阙楼阁,建筑雄伟壮丽,其人口大大超过其他城市。在王莽当政的短暂时期之后,当数股势力为争夺帝位而争战时,长安被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帝位争夺战的胜利者建立了东汉(公元25年—220 年),并迁都洛阳。然而,在对长安屠城发生之后,新的帝都无法称霸全国,至少在数字上无法冠盖群城。直到公元111 年,洛阳的人口(居民为101 万)可能还少于富饶的成都。成都城内的人口至少有100 万,郊区还有35 万。[69] 西汉时在高皇帝刘邦到武皇帝刘彻的统治下(公元前202 年—前87 年),延续了将豪门大族迁往都城居住的政策,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世家望族权势的扩大,也没有遏止朝廷的式微。在东汉时期,这种以中央权力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社会控制制度不再行之有效,围墙环绕的城市作为控制象征也日趋衰落。不过根据汉朝的城镇我们可以进行几点综合,因为在中国历史的这段悠长岁月中,这些城市的发展表现出一些同古代及后代均有所不同的特色。 根据宫崎市定(Miyazaki)所述,可以将汉代的市镇依规模划分为3 个等级:县,乡,亭。最小的单位是亭,人口数百。在数个亭中, 其中人口最多的可能超过2000,这样的大亭被叫作乡。同样,人口最多的乡成为郡都或是县。这些市镇的密度和规模可能根据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而定,因为汉朝的城镇实际上主要是农业性的。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城镇而不是村庄可能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们同田野分离,而且居民生活受到严密管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严密组织。 汉代城镇最关键的要素是墙。城墙将居住地同外面的耕地隔开, 由于建立起一个密封的驻地而有助于对内部生活的严密组织。不论大小,汉代的城镇就像被一层层围墙环绕的长方形。城墙或是城郭在四周都有城门。城墙之内的地区被分割成不同的街区,称为“里”。城市的大小决定街区的多少。常用的表达“十里一乡”说明乡的规模。长安城被分为160“里”。“里”之间有街道相隔,而且同样被围墙或是垣环绕。在汉朝时,一“里”只有一个大门通向街道,其中的居民多达百户,每一户同样也被院墙环绕。很细的小巷通向每户人家的院门。居民如果出城的话必须通过3座门:他们的家门,他们所住的“里”门和城门。而且所有的门都有人守卫,在夜间关门上锁。城中的街道在太阳落山之后一定是吓人地空无一人(宵禁)。在“里”境之内,月光下可能会看到年轻的情侣翻墙出入。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浪漫传奇中已成为俗套。翻越院墙会受斥责,但是如果翻越城墙便犯了要严厉惩戒的罪行。[70] 西汉时共有1587个县,6622个乡,29635个亭;总共有37844个城墙环绕的驻地。如果我们假设每个城镇之中平均有居民2000人,那么这说明西汉帝国的所有人口(6000万)都住在大小不一,围墙环绕的地方。宫崎市定便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在西汉时期,很少人住在围墙之外,自从古代以来这便是中国人的居住常态。[71] 当然也存在另外的观点。艾伯华(Eberhard)认为在西周时,商代遗留的村庄同周朝围墙环绕的城镇比邻而居。在封建制下,中国农民在整个夏天离开城去住在田野里临时搭建的栖身之地,在收获之后才返回城镇;那些临时的栖身之所最终变成了乡村。[72] 在东汉时期,城镇的总数看来有所下降。有几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一是因为总人口下降,尤其在华北平原上人口下降更为严重;还因为城镇规模扩大;此外,在新兴的边境城镇附近和新垦荒地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小村庄。在大分裂时期,蛮族占据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依赖重叠墙门进行监督的严格控制体系分崩离析。小的乡和亭衰落了,村庄却增加了。 唐朝的县同汉代一样为数众多。不过唐朝的县较大,居民获得较多自由。汉代时封闭的街区“里”只有一个大门通向街道,唐时的街区通常称为“坊”,“坊”有四座门。在汉时,即使豪门贵族也不能在“里”墙上建门,以便他们的府邸可以面临大街。在唐朝统治之下,不仅豪门大族,而且佛寺庙也可以将自己的院门开在“坊”墙上。[73] 不过“坊”门在夜间关闭。甚至在遥远的边境城市广州,在外国商人活跃的闹市街区,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隋朝和唐朝时的长安就面向正确的方向,三面墙的每一面都有三座大门,祭地的祭坛和帝王的宗庙依据南北轴线位于正确位置。但是包括皇宫的内城并不在城市中心,而是背靠北墙,布局上的改进为官方市场留出地方。市场分为两个部分,都城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东市和西市。据我们所知,长安城的规划成为日本在建造 京都和奈良时效仿的典范,长安无疑也对华夏大地上很多具有政治重要性城市的建筑有所影响。我们仍旧可以在留存到20 世纪中叶的古城中,不论是格子形状的小县城还是北京,发现长安所清晰阐明的城市规划原则。 唐朝的长安是什么样的呢?诗人白居易他描写了长安的夜景: 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 遥认微微入朝火, 一条星宿五门西。 (《登观音台望城》)[78] 长安的夜晚很安静。除了官府的骑者,主要的街道空无一人,坊门紧闭。白天这里却人声鼎沸,尤其是在西市。但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这可以使我们了解这座大都城的规模。[79] 隋朝的开国皇帝规划了长安的宏伟布局,其基本框架为唐朝君主们所继承。长方形的城市从东到西有10 公里,从北到南8 公里。方圆大约80 公里,围墙环绕的城市分成格子状,其主要地点是位于中心的宫城官府,它们靠近外城郭的北墙;还有东市西市、坐落在西南一隅的曲江园、围墙环绕的110 个坊。在25 条宽阔车道边上修建下水道、人行道、栽种果树,街道贯穿长安城。有11 条由北到南,14 条由东到西。南北走向的大道令人瞩目地广阔宽敞,超过135 米宽,东西街道也不逊色太多。当时的人们一定认为这些街道是规整清洁的开放场所,与个人无关,令人生畏,作用是将居民住地“坊”隔开,而不是使它们彼此相连。上层阶级主要住在东城,一般百姓住在西城。所以西城可能居民较多。在两个集市之中,光顾东市的主要是衣食不愁的客人,因此那里并不拥挤,到9 世纪初,东市大部分变成居住区。西市却是个“集市货栈遍布的繁忙喧闹场所,商贩说各种语言,除了说书人,艺人和耍把戏的,不同民族的变戏法的和魔术师也为顾客表演”。[80] 虽然大约100万人住在围墙环绕的长安城中,在方圆80公里的巨大城郭之中也有人烟稀少的地区。城市最南部有一条宽阔的地带,那里居民不多,主要是耕地菜园,也散布着几座庙宇。在东南角是邻水的曲江池,一个美丽的园林,点缀着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为文人墨客所流连忘返。诗人白居易喜欢骑马去那里,下得马来,漫步在岸边的柳林。曲江池树木花草繁茂,有柳树,杨树,粉色的荷花,湿地草类和芦苇,吸引来各式各样的野生飞禽。在每个季节园林中都聚集着城里的文人显要。[81] 第六章 宋朝至清朝 三 繁华富庶、充满活力的宋代城市 商业的重心是宋代时蓬勃兴起的大城市。到1100年,至少有5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只有开封位于北方。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接近5大城市的规模。在1126年女真人占据了宋帝国的北部,但是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南宋城市继续迅速扩展。到1290年,在元代某些地区府州人口似乎增长了2倍、3倍,甚至4倍。人口增长最引人注目的三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杭州、苏州、福州),还有一个位于从长江流域到广州的内陆贸易通道上(饶州)。 以前只有在成为国家都城之后,城市才获得经济重要性。而在10世纪至13世纪之间,城市只有成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商贸中心之后,才被选中成为国家都城。比如说开封,因此成为北宋都城。在被定为都城之前,开封是当地的行政中心,但是它在经济上获益的主要原因是位于从南至北的大运河上。[15] 作为北宋王朝的都城,开封远远不仅是个政治中心。开封发展了工业,为商品输出和当地消费而进行生产。产品包括纺织品、印刷品、墨锭、金属制品和瓷器。[16] 城市日益商业化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后果,即使当它们成为国家都城之后,也不再具有传统上的刻板严格,不再被长方形城墙环绕,城郭之内并非按照古代原则规范安排布局。宋代阔大城池的围墙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在古老的中心区外,商业区发展杂乱无章,然后往往又在商业区外面建起围墙。我们可以回想起在久远的古代,即周朝时的战国时期也发生过类似情况,那是一个短暂的商业发展时期。政治城市的传统形状是长方形,这个长方形依据皇帝有关伟大君主的概念而专断地强加于景观之上,同人口增长无关。开封与此相反,当商业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在城门外杂乱无章地扩建了郊区,又在郊区之外先后建起新的围墙。虽然开封位于平原上,它的发展历史使之缺少以前国家都城所具有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正是后来北京城的鲜明特色。[17] 根据马可·波罗狂热的描述,南宋都城行在(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城市。但是杭州的伟大在于城市的人口、财富及人民的温文有礼,在于城里著名的湖泊、公园、园林。杭州的伟大不在于规模宏大、占地宽敞或是概念上的雄伟壮观。在所有关键之处杭州都没有遵循城市建设的经典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城墙西依湖泊之势,东受杭州湾之辖,环绕着一个参差不齐的区域,城墙上有13 座距离不等的城门。宫城位于城墙环绕的城郭南端,而不是传统上的中心位置或是北部。城市在几何学上的中心位置被一个很大的贩猪市场所占据。而宫城逶迤在林木葱茏的凤凰山东麓,蜿蜒曲折的宫墙依地形起伏而建。御街确实位于城市的南北轴线之上,但是甚至这条主要的干线也没有完全遵守经典准则,御街在距宫墙北边不到1 公里之处顺地势起伏而两度直角转弯。[18] 在杭州,率性而为和人间魅力取代了北方“宇宙性”都城的次序森然和雄伟壮观。比如就规模而言,杭州远不如唐代长安那样堂皇庄严。城墙环绕的地区只有9 平方公里,与唐代长安80 平方公里的宽 敞浩大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御街铺设得美丽豪华,街道的宽度只有54米,还不到长安的朱雀大街宽度的一半。南宋时杭州有众多迷人的景致位于南部的凤凰山麓,达官巨贾在那里修建了住宅。在靠湖的郊区也可以见到阔大的庙宇和富人漂亮的府邸。但是杭州也具有一种市井生活的热烈,与之相比唐代长安的生活似乎黯然失色。 密集的人口在部分上造成杭州的热烈气氛。那里有150万人口拥挤在方圆20平方公里的地区之中,有些在城墙之内,有些在城墙之外。而在8世纪的长安,100万人住在80平方公里的城郭之内。都城里的长安有大片地区实际上是乡村。与此不同,宋代杭州在凤凰山下挤满了房屋和居民。最为拥挤的地区(每亩33人)是御街周围那些狭窄的小巷。[19]建筑用地供应不足,这似乎鼓励人们建造多层房屋。同唐朝风格不同,房屋临街而建,下层当作店铺,出售面条、水果、针头线脑、香火、蜡烛、食油、酱油、鲜咸鱼类、猪肉、大米以及多种多样的奢侈物品。上层可能是住宅,也夹杂着茶馆以及提供歌女情色服务的酒馆旅店。[20] 或许最显著不同的是夜景,夜景最充分反映出自从唐朝末期以来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在唐代城市中,夜晚一片死寂。坊门紧闭,日落西山后,人们只在坊内活动。在坊门之外,除了几个兵丁和奉差出行的骑兵,宽阔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宋代的杭州与此迥然相异,直到深夜,仍生气勃勃,热烈不减。在御街周围,五颜六色的灯笼高悬在饭庄的门口和庭院,辉映着店铺陈列的商品,也照亮了夜色。 作为南宋帝国的都城,杭州以其物质丰裕,文化卓越和政治权力而出类拔萃,这同城市的规模及不合传统的布局无关。至少3座城市,福州、饶州、苏州在总人口上超过杭州。这些城市在规划上同样杂乱无章,它们以及其他一些在规模上相差不远的城市都没有古老的北方城市的严整规范。这些南方城市因商业活动,而非政治权力而举足轻重。在市容上,这种商业化倾向表现为南方城市缺少空间秩序: 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政府监管下围墙环绕的市场之内。经营商业和制造业的店铺作坊散布全城,并扩展到城门之外的郊区。 四 可汗的城市 南宋帝国大城市的发展随心所欲,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蒙古人在北方兴建的、规划有序的都城。这称为可汗的城市或是大都,即忽必烈汗的京城。可汗的城市于1267年开始兴建,城址在金朝(女真)被毁都城的北面(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当宋朝皇帝于1135年选定杭州为临时国都时,这是个繁荣的州府,人口有25万。忽必烈汗的首都却多少是平地而起。它的中心地区只有几座金国留下的夏宫。 尽管城市是为蒙古皇帝而建,而且主要的建筑师却是个穆斯林,可汗城市的设计规划表现出格子式华夏首都所具有的几乎一切传统特征。[21] 如马可·波罗所述,可汗的城市是个几乎完美的正方形,在城墙的每一边都按照规定,建造三座城门。街道笔直宽阔,像棋盘的格子那样排列。在外城郭之内有两块围墙环绕的禁地,最里面是可汗的雄伟宫殿,大明殿。 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可汗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大量人口,城里商业繁荣。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那里时,虽然城市刚刚竣工,里面却已经热闹非凡。在可汗的城市,“城墙里和城墙外都是众多的房屋和行人,没有人能数清他们的数目”。[22] 人口变化同经济变化关,并反映在景观之中。自从1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迅速攀升,长江流域和南方进入经济快速扩展时期,食物供应相应增加,商业发展,大城市崛起。我们前面已经阐述了这个主题。不过中国北方的历史更为坎坷。自从10世纪以来,北方先后遭到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蒙古人最终于1279年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中国。 北方人口无疑随着连续不断的进攻,以及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征服者变化无常的政策而上下波动。征服者们无法确定如何应对被他们所击败的,但是更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当侵略者们企图占领农业用地,将农田变为牧场时,景观发生了剧烈变化。女真人曾企图这样做。窝阔台(Ogodei)在位之初,一些蒙古人也企图将华夏北部的大片地区变成牧场。虽然幸运的是这个举措并没有严格执行,但是在华北平原的北部,有些农田的确成了牧场。直到忽必烈汗明令禁止之后,为此目的的圈地行为才宣告终止。[26] 将农业用地变为牧场可能是中国北方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在元帝国占领整个华夏之后,从长江三角洲将谷物大量运到北方都城。运粮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海运,走海路沿岸用海船运载; 二是漕运,顺新开通的大运河(1266 年—1289 年)用运粮的驳船 运输。 在忽必烈汗统治之下完成的最伟大工程是大运河。以前隋朝所开通的漕渠在设计上是为了供应都城长安,不是元朝的都城北京,所以只是在南段才通行无阻。在元朝、明朝,甚至于清朝,大运河都是南北运输的主要动脉。这说明北方在经济上一如既往地依赖南方。 这种依赖性使北方的首都地区缺乏安全。海上运输线易受海盗袭击,海洋航行会遭遇突发情况。黄河不可预见的决口使内陆运河航行也时时受阻。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增加京城附近地区的粮食产量。至少能生产足够粮食,以便都城人口、尤其是驻军,可以自给自足, 又可节省运输费用。在1352 年元朝皇帝下令,将海河流域平原所有政府用地和以前用于军屯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在起初阶段朝廷还提供工钱、耕牛、农具、种子。朝廷还从长江流域省份请来精于耕种水浇地的农民和水利专家教授北方佃农。虽然这些措施已见成效,但是没有达到北方粮食基本自给的水平。不过在明朝和清朝,人们仍旧对此目的抱有希望。[27] 五 明清两代的城市化 蒙古人建立的朝代被来自中部和南部的汉族起义军推翻。南京成为明朝(1368年—1644年)的第一座都城。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选择,因为南京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根据地,靠近人口和财富中心。中国东南部继续繁荣昌盛,明朝时新建的,围墙环绕的城市大多位于中国东南。虽然规模和重要性已有所不同,但宋代时巨大的城市仍风采不减。比如说苏州,在册的人口一如既往保持在200万以上。在成为国都之后,南京地位今非昔比。环城修建了巨大但是并不规整的围墙。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朝廷迁至北京。南京失去了政治上的地位,但是经济持续发展。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南京同北京比较,对南京颇有好感,南京人口为109万,很可能超过北方的都城。[23] 明朝皇帝使北京 明朝皇帝使北京城具有了它在近现代的形态。明朝的京城修建在可汗城市的基础之上,但是城墙环绕的城郭缩小了,并稍微向南迁移。它仍保持正方形。实际上由于城郭的南移,围墙环绕的内城更加位于中心位置,从而比以前蒙古人(元)的首都更加具有几何学的严整规范。但是当新的城郭于15世纪20年代完工后不久,南墙外兴建起一大片郊区,出现了成千上万户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和外国的商贾在那里开设店铺,修造住宅。于是政府计划修建一道新墙,把南墙外的地方圈起来,但是只建成了其中一段。其结果我们今天仍旧能看见:两个有围墙的城郭比肩而立,一南一北。 继明朝之后统治华夏的清朝或是满族王朝大兴土木,建墙修城。清朝所建的围墙环绕的城镇为数众多,数量可能除汉朝之外超过以前所有朝代。除了在东北、西南和台湾这样的边疆地区建立新城,还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省份发达地区破土兴建。[24]虽然城镇总数增加很多,却并没有为城市景色增添任何令人惊叹的新奇之处。不论是总体布局还是个别建筑的修造,满族人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因袭古代传统。北京是集这一保守主义之大成的例证。满族人统治北京超过250 年,在这期间他们只是维持着明朝的框架,改建宫殿和庙宇,又增加了几座新建筑而已。 在清朝末期最终出现的都市主义新因素并非源于本土的真知灼见,而是从欧洲传入中国。嫁接过程的最鲜明范例便是通商口岸,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矛盾并存。作为政治不公正的产物,通商口岸大多是新城,但是作为西方工商业文明价值观对中国精神渗透的表现,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重新定向。后面两章是关于近现代中国,其主题是讨论西方技术和价值观对中国景观的影响。但此时我们需要回到更古老的中国。在这个国家和文明中确实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但是变化主要发生在灵活变通的中国传统框架之内。 "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地理学大师话说如何山川地貌造就华夏历史。 华裔地理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献给祖国的书。 功力深厚,行文流畅可读,大家小书。 以人文之眼、人文之心,讲解地理如何造就中国人,中国人如何改变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