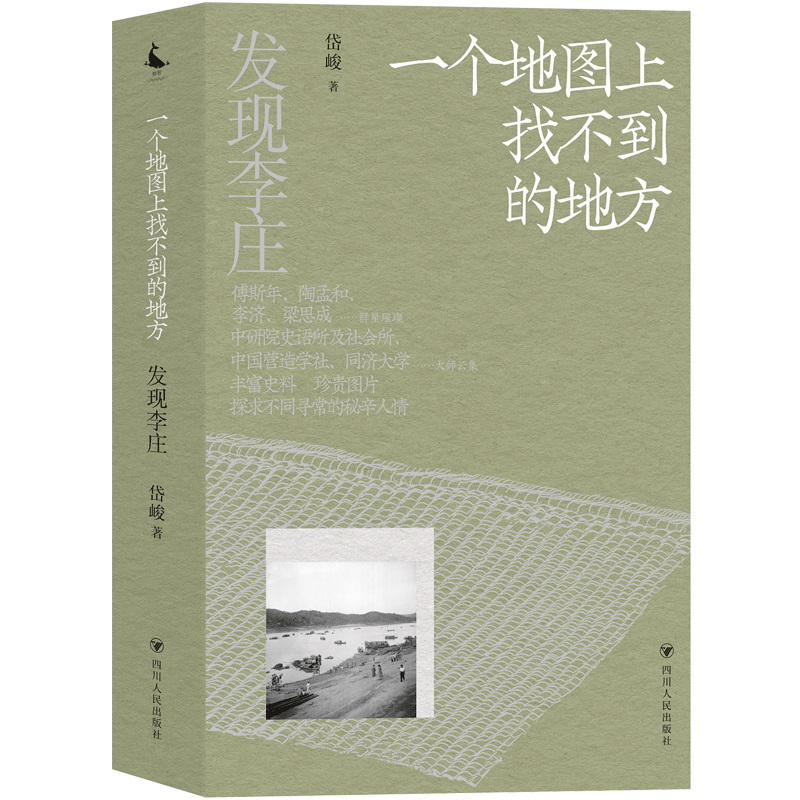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156.00
折扣价: 93.60
折扣购买: 发现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ISBN: 9787220128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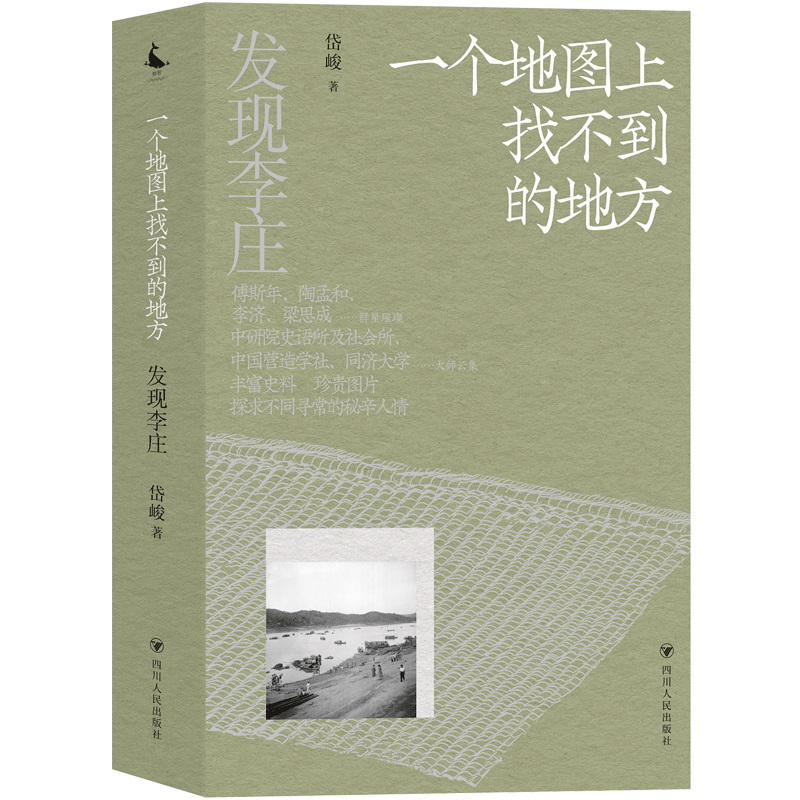
岱峻,文史学者,祖籍四川资阳,定居成都。著有《发现李庄》(三次再版,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初版获《中华读书报》2009年百佳优秀读物;增订本获《光明日报》2021年十大好书),《民国衣冠》(中华读书报2012年百佳优秀读物),《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凤凰传媒2013年“十佳”读物、南京图书馆2014年“陶风奖”十大好书),《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十大好书),《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刘雨虹访谈录》等。
《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样章 第五节?自律与自由 江上渔歌,山坳犬吠,乡间日迟。青年研究员何兹全印象中的板栗坳十分清静,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山上没有电灯,用点着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四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的。睡觉!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我们房子后面有棵大树,树上有一窝猫头鹰,我们头一天到,不知道。次早黎明猫头鹰嘎嘎大叫,我们被惊醒了。 板栗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无尘嚣之乱耳,无跑飞机轰炸之劳形。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抄材料。 刚发蒙的张汉青少不知事,父亲张海州给史语所做事。他天天就在先生中间跳来跳去,那是他生命里一段奇特经历: 牌坊头有棵大的桂圆树,天天赶早先生兮就在这里摆脚摆手。刘海清早上摇铃铃上班,先生夹一摞书来;下午摇铃铃下班,先生夹一摞书去。他们住得很分散,六七个大院子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各上各的班,比我们上课还清静。有事外出要请假。平时是不能随便离开板栗坳。规矩大得很。 从北平到李庄,经历了长沙大火、昆明空袭,多次播迁,每个人自觉把自己镶嵌进这个团体,养成高度的纪律性。 李临轩是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抄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停;请假时间,在以后的星期天扣除。 1943年,马学良从云南调查倮语返回史语所后,闻母病,请假回西安省亲。1944年3月25日,他向傅斯年写信:“家慈病日危,返所无期,而调查材料急待整理,拟借家慈去成都治病之便,将家迁至板栗坳,如此,可早日返所工作,恳请吾师恩赐住房数间,以便早日成行。”同乡、同学、同事张琨也请假回到西安。马学良侍奉母亲,又与好友相聚,便心生流连,“前曾函恳赐住房数间,以便迎养家慈于李庄,惟迄无复。现陕中紧急,恐难成行,兹特再函恳谅情赐假几月,伏乞垂谅。”傅斯年一眼看穿年轻人的把戏,复信:“关于兄去年亏空,因而募捐一事,至先奉母来此伺养,房子无问题。又,兄请假过久,不可再延续,务请于一月内返,至盼。” 事情又生变故。马学良妹妹的同学何汝芬流落西安,母亲作伐,相识月余,匆匆成婚。“这一夜,日本人攻打潼关,枪炮声此起彼伏,西安城一片惊慌。”傅斯年不明就里,一边苦劝,一边亲自出面托人找车。“敝所助理研究员现在西安觅车困难,无法起身返所,敬请我兄用院长名义函请西北油矿局代为设法,并乞询胡副长官(胡宗南)办事处能否即搭该区车来渝?”其后,傅斯年到底还是知晓马学良的洞房花烛情,7月13日致马学良的信颇为恼怒:“天下事有本自显然,强辩无益者。来信于结婚事一字未提,此事岂有不影响兄返所时日者?现岁停薪留职,仍须早日返所。” 7月20日,马学良将现实困难向傅斯年和盘托出:“留西安未返之苦衷,原非尊示所认为强词借口。今与张琨同学商好,九月十五日以前如母病较好,即相偕返川。不知彼时尚能留职否?伏乞早为示知,所方若限于定章不得已而下辞令,亦请早为示知。恳准将调查稿件寄来整理交付所方印刷,如何之处,伏乞裁示。”西北大学闻讯,也在打主意聘任马学良,边政系系主任黄文弼致函傅斯年。8月8日,傅斯年再函马学良:“兄奉母之事,弟极同情,惟决不能为无限期请假之理由。就西北大学事,恐非善法,至于调查稿寄来整理一说,自行不通。总之,快快回来,是为善法,迁延太久,名额已满。” 入情入理,苦口婆心,犹如子规啼血唤春归。几十年后,马学良犹存感激: 转眼到了1945年,傅斯年所长一再来信催促我和张琨回四川工作。傅先生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时,还在开会间隙再次写信,在信中谆谆开导,言深意切,令我们又感动又惭愧,不能不急忙束装返川。这年8月,我告别父母和妹妹,同妻儿登上返回四川的汽车。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学一门外语,1942年2月23日,他向傅斯年呈交假条:“兹因工作需要,拟请求自三月至六月每日赴李庄听德文二小时,尚祈鉴核。”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有一年我每个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济大学旁听德文课,从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来回二十里,我每天穿着草鞋走二十里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恰巧有个印度学者做访问学人,我正自修梵文,就常向他请教。”他说的这位印度访问学者叫狄克锡,原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学考古学,来史语所研究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 1945年周法高、董同龢等赴成都调查四川方言,专门去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向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请教。周法高从李先生处借到德文版那保罗的《根据陈澧切韵考对于切韵拟音的贡献》一书,凭着旁听德文一年的功力查字典,抄完60余页德语原文,边工作边研读,于1948年写成《古音中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把那保罗的学说介绍给中国语言学界。 三十年代起,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注重在学者中选拔官吏,先后延揽了地质学家翁文灏、钱昌照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翁文灏后来在蒋介石任行政院长期间曾官至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物理学家李书华任教育部副部长,还有南开大学研究院的何廉、植物学家李顺清、化学家徐佩璜、物理学家李耀邦等人,都先后在政府任职,加上曾为北平地质调研所所长,又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丁文江等,这些学者一时间尽入党国彀中,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中研院是国府最高学术机构。建院之初,蔡元培就曾说过,中央研究院系纯学术研究工作者所组成的学术团体,它与大学研究院性质不同,大学稍侧重于博大,研究院侧重于精深。凡到中央研究院的人,必抱坐冷板凳,专心问学的宏愿,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 据说,1940年中研院拟设民族学研究所,欲请留美博士、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执掌。李先生向如闲云野鹤,对学问之外的事,向来不涉,宣称“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此时,傅斯年兼中研院总干事,于是,出面请李方桂屈就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傅氏看来,所长只是学术负责人,凭自己与他的交情兴许会给这个面子。结果事与愿违。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就对傅直言:“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此则逸闻,据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辗转求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一位老先生,得到答复:经查史语所现存傅、李两先生档案,确有“设所”之议;但“三等人才”一语,则文献实不足徵。 致仕与治学,也同样考验过民族学家凌纯声。1943年2月23日,他收到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加急电报:“关于请兄担任新省党部执委兼该部研究室主任一案,已得盛主委同意,此案并经常会通过,总裁又定期召见,请速来渝西行,并物色工作人员连同经济调查人员在内共四人偕往。”盛主委即新疆王盛世才,抗战前期,他在各种政治势力间左右逢源,与苏联暗通款曲。此时,已归顺国民党拥护蒋介石。于是,国民政府亟须派员援疆,有人举荐凌纯声。两天后,朱家骅又发一电:“尊事已奉总裁批准并嘱转知来见,希即来渝。”总裁召见,谁敢拂逆?凌纯声遂求助傅斯年,傅与朱家骅交谊厚,在蒋面前也敢言。凌在2月2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谈到“不能赴新省之理由五点,恳向院长代为婉辞并解释一切”。傅斯年当然理解。3月4日,凌纯声回电朱家骅:“现内人病甚,一时不能赴渝应命,去新远行实有种种困难,已托孟真兄代陈一切。”上方催督愈烈,3月6日,中研院干事王敬礼再致电凌纯声:“新省一事,业常会核准,盛电欢迎,总裁极愿传见,事成定局,盼即来渝。”一纸千钧。盛世才已摆出欢迎架势,这也关乎蒋公的面子。凌纯声清楚,蒋是要把自己当作笼络盛世才的礼物,盛世才是要把自己押作人质。3月11日朱家骅再下最后通牒:“此事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无论如何盼速来渝西行。”拖了五天,凌纯声才回电朱家骅:“不能赴新实有难言之苦衷,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回电掷地有声,凌纯声必然惹怒上司,但当局还算隐而未发。 研究所内部“禅让”,也时有发生。中博院主任李济就曾两次让贤举能,他分别致信朱家骅、傅斯年: ——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骝公即指骝先,朱家骅字)便中一商。 ——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成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 史语所档案,有几封信有意思: 1944年10月4日,李济致信傅斯年: 蒙古语典劳兄吹嘘,已以二万元与教育部成交,哈佛燕京社补助费弟受之有愧,务祈代为辞谢。 1945年1月27日,梁思永致函傅斯年: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 傅斯年有多重社会兼职。董作宾在李庄也长期代理史语所所长职,1941年5月31日,他致信傅斯年:“望勿以‘所长兼薪’事向院方进行。”1945年9月13日,“关于兄请假事,请加考虑,最好为兄兼任北大事,弟则维持一非正式代理,然弟绝不克担任正式代理”。9月23日,“所长办公费弟决不受之”。代所长只做事,受累,遭怨,绝不求名受薪。 既为中研院下属研究所,就不能说与意识形态全然无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在李庄史语所,《三民主义歌》也必须唱。1942年,董作宾以“咏南”为笔名所写的《栗峰上的史语所》云:“这一群书呆子,有时也过着整齐严肃的生活,每次纪念周的时候,大家在晨光曦微中齐集第二院,静待铃声一响,便鱼贯而入礼堂,肃立则鸦雀无声,党歌则高唱入云,直待礼成之后,大家才肃然而退。国民月会,也曾有过,各项专题讲演,最后一次是哲学家金岳霖大博士的逻辑,尤其益人智能不少。” 在迁入李庄的学术团体和科研单位中,没有明显的政党派别活动。据1938年年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统计,中研院职员中有国民党党员11人:蔡元培、周文治、刁光辉、阮鸿仪、何桂辛、李行圣、冯騛、李四光、周文龙、吴定良、陈士毅。1939年6月20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转发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函:“通令各级党部对各该地未入党之公务员,尽量劝导加入本党,并函国民政府通饬全国各级机关主管长官,首先加入本党,以资倡导,而期充实本党力量。”中央研究院特将此函转发到各研究所。据1947年的档案资料显示,其间又在中研院发展了15位党员,属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十六区第十三分部,名录显示:萨本栋(中研院总干事)、刘次籣(秘书主任)、王懋勋(秘书)、余又荪(秘书)、王梦鸥(秘书)、辜孝宽(总务主任)、王恩隆(组员)、丁建中(组员)、吕仲明(科员)、吴家槐(科员)、朱宝昌(组员)、程元龙(组员)、刘求实(书记)、彭雨新(社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建章(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以此看来,除社会所彭雨新之外,中研院在李庄的研究所再无一人加入国民党。 1943年3月10日,以蒋介石名义著的《中国之命运》出版。2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发函,要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等均应切实研讨批评,依限呈报”。6月11日史语所向总办事处报送副研究员劳榦、全汉昇与助理员屈万里、周天健等四篇读后感。据《中央研究院各所遵从〈中国之命运〉一书原则拟具工作实施计划案》显示,劳榦对《中国之命运》,提出多达11处需要“斟酌”的意见。其中一处质疑“绝对标准”,“不知何指”;一处质疑“中国的命运的标准”,“不知如何标准”。官方指示,意在“研讨”,不做“批评”。他却以史家的考据方法,辨正《中国之命运》文理不通,“文法上或文义之贯串上有可斟酌者,尚所在皆有”。 中研院有派遣研究人员“放洋”的传统,这是众所瞩目的出国进修机会。据夏鼐日记,1944年2月10日史语所“遣派出国之人选将投票表决”; 2月22日,“所中遣派留学事,由所长全权办理”。最后,各个研究所报中研院,经院务会议批准,派遣史语所丁声树、全汉昇与社科所梁方仲等三人出国。 按照规定,所有出国人员都必须到重庆浮图关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这一组织为蒋氏于1938年所建,其宗旨“在使受训人员真能成为实现主义与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与信徒”。报名注册时,须在专人指导下填写履历表。其中“已入党否”栏,如果未入,即被要求填上“申请入党”字样。 来自李庄的三位及中研院另外两位学者,坚持留空不填。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回忆,当时所有公派出国人员入此团受训后方可领得护照。除周末外,每日上午听报告,下午讨论。报告内容基本不离三民主义理论、国内外形势以及国民政府施政成绩和建设成就等。通过学习,达到使学员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和宣传国民政府之目的。混课,对中研院大学者不过小菜一碟,但要申请加入国民党,不为。据说,以“不入党、不做官”为宗旨的梁方仲,为了逃避训练团三番两次派人劝诫,曾一度从浮图关搬到两路口中研院总办事处“避难”。恩师陶孟和或有所闻,曾以“手示”委婉劝其稍做变通。梁方仲回复陶孟和:“此次全国不入党者,仅十六人,其中中央研究院者占去五人,闻段书诒先生对生等颇表同情,故得幸免。”为其辩说的,还有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他出面解释,中研院的先生都是只做学问的“书呆子”,从来无意党派和政治;还搬出美方已经发出邀请等理由,与多个部门疏通。拖了几个月,他们最后才得到护照。 傅斯年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都站在国民党一边,但他执掌史语所的原则始终是有意疏离政治。他主张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提倡建立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做学问不问实际应用”,“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他在史语所公开表示:“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 史语所学人被称为“史料学派”。“史学就是史料学”,治史者或不免带观点,难以做到客观,为史学尽可能公正,就要力戒主观。史语所的学者在史料收集、整理和注释时,在看似客观的研究中,也有掩不住的现实关怀。 全汉昇1942年完成的《北宋物价的变动》一书之概说,有对物价变动影响民众生活的表述: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经济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物价上升时,出卖商品的商人,生产商品的农民和工业者,莫不喜气洋洋,因为这是他们发财的机会;同样,随物价上涨而工资不涨的不固定收入者可要困难了;因为物价的上升,足以迫使他们降低原来的生活程度,以致过去能够享用的物品,以后不能享用,或须大量地减少。反之如果物价下降,在一般消费者和固定收入者看来,这是最好不过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趁着这个价廉物美的机会,买到许多物价上涨时所不能够买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上自然要宽裕得多了。至于运销商品的商人,生产商品的农民和工业者,当物价低落的时候,不特无利可图,有时甚至要亏本,可要愁眉不展了。物价升降既然给予人民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它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应被忽略的。 作者考察北宋物价变动所引发的问题,战时钞票贬值,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史研究,不能说没有现实针对性。 1946年劳榦出版《秦汉史》,他书中写道:“实际上儒家是讲原则性的,而法制则是必须在客观立场上管理政治,二者之中,一站在道德立场,一站在技术立场,两者正互相为用。中国历来政治,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二者交互使用;不只是汉,中国各朝多半如此。”孟子主张“禅让”,但难于实行,只好以“贵族政治”替代一姓之继承,“贵族”从“皇室”分权,这是走向政治民主化之始。史料学派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就这样不即不离又若即若离。 1944年元旦,板栗坳牌坊头礼堂两边贴有一副大红对子,给阴冷的天地添了一缕暖色。对联由客居此地的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隶体书写,考古组屈万里撰联: 岁序又更新,装了一肚皮国恨家仇,卧薪尝胆之余,何妨散散气; 寒酸犹似旧,剩下满脑子诗云子曰,读书写字之外,且自开开心。 史语所考古组夏鼐独自躲开欢笑,向隅枯坐,在日记中写道:“听着隔院歌声,令人有新年之感,自己十余年各处飘荡,仅去年在家中过了一次新年,今年又仍在客中度新年,不知明年又在何处。” 1.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抗战时期,只用在信封上书“中国李庄”四字,便可将信件寄到李庄。作为四大文化抗战中心之一,李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却成为世界的焦点。 2.背负民族传承,岂有穷途之哭。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众多大师级学者,在艰难岁月坚守对民族的忠诚,以书生的方式参与抗战。 3.群星璀璨,近代学人不期的命运交集。 这些不同领域的大师,在李庄相聚,填补了诸多中国学术的空白。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李庄,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有多大一片空白! 4.**之作的迭代升级。 2004年,一部《发现李庄》让李庄重回大众视野。近二十年来,岱峻又结合大量的采访记录、田野调查记录、文献资料,对《发现李庄》进行了升级,是“历经数年的重新写作”。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小古镇,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座古镇是与成都、重庆、昆明齐名的“四大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信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即可使命*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中博院等文化机构将李庄作为安身之地,李庄的乡绅乡民以博大的胸怀和质朴的情感接纳了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和知识的火种终得以保存。文化不灭,中国不亡,那时的李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几十年过去,李庄的故事已渐渐掩埋于历史的烟尘下。2004年,一部《发现李庄》让李庄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李庄成为旅游热点。如今,李庄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4月26日,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陈列馆同时开馆…… 《发现李庄》的成功并没有让作者岱峻停下手中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岱峻坚持田野调查,采访先生们的后人及当地人,采集了大量口述史资料,同时,他博览文献,持续追踪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多方引证。最新完成的三卷本《发现李庄》比2004版《发现李庄》增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在结构编排上,也与老版完全不同,更具*整性和科学性。总之,新版三卷本《发现李庄》与其说是修订,不如说是“历经数年的重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