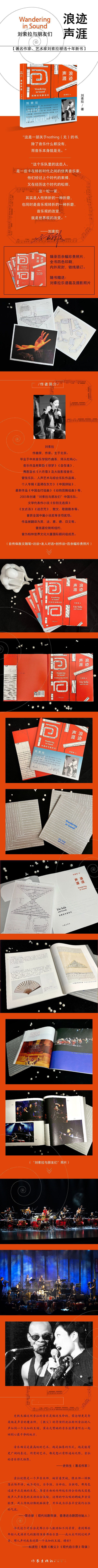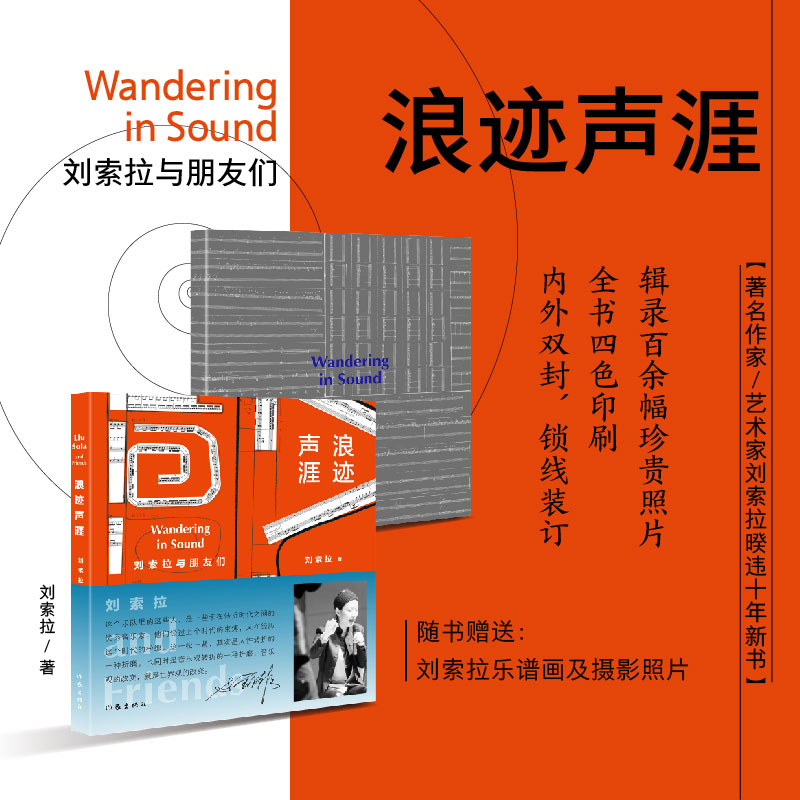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118.00
折扣价: 75.80
折扣购买: 浪迹声涯
ISBN: 9787506398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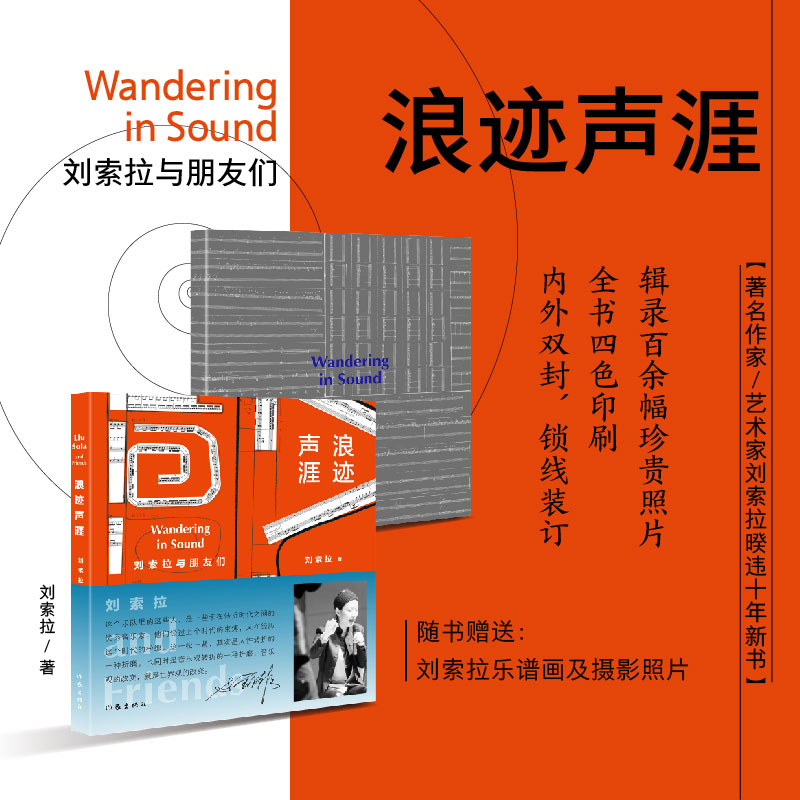
刘索拉 作曲家,作家。生于北京。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 音乐作品有歌剧《惊梦》《自在魂》,舞剧音乐《六月雪》及大批影视音乐、管弦乐队、人声艺术与綜合乐队作品等。个人专辑《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最新作品《中国击打组曲》《动物图腾组曲》等,2003年创建“刘索拉与朋友们”中国乐队。 文学代表作小说《你别无选择》《女贞汤》《迷恋咒》,散文、歌剧剧本等。 曾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项。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德、日文等。 曾旅居伦敦和纽约,曾为柏林世界文化大厦国际顾问组成员。
关于这本书 刘索拉/文 在我们幼年教科书中,有很多高大上的先人,无意中被当成课本和人生标准,于是成了我们幼小心灵中的大山。在课本和琴谱中,有那么一堆固定的大山,一个比一个高大,首先基本上不容易爬上去,再者,爬上去见到的也不过是先人偶像肩头上的鸟屎。还可能会听到先人的诅咒:我已经在这儿了,你来挤什么呢?下去。下来,爬上另一位先人的肩头,只见铜像的眼睛一瞪:没有主见的跟屁虫!一口唾沫,把我们啐到先人脚下。 于是待在先人脚下的巨大阴影里,仰视着,凭借那巨大的影子,觉得自己融于其中也很安全,不时冒出来仗着影子的高大可以指责同代和下代的卑琐,心中生怕走出那大影子,自己的影子登时显小。 其实所有学音乐的孩子都希望能够和莫扎特一样体验那种挥霍音符的狂喜,和肖邦一样体验用手指与钢琴间的奇迹建立自我王国,和Jimi Hendrix(吉米·亨德里克斯)一样体验声音和生命纠结不散的存在和消失。这些音乐的精灵都没有刻意要当山峰,只不过是飞翔于每个音符的瞬间。 只有摆脱地理和社会的界限,才能充分体验到声音和灵魂的关系,让声音帮助人活下去。这一点,似乎在我们的课堂上很少被提及。我只是很清楚地记得在中国音乐历史课上,曾有老师提及古代传统音乐艺人的下九流地位——却很少提及古代音乐艺人在演奏音乐时享受到的飘然状态;在西方音乐历史课上,每个作曲家都是人类思想的贡献者——也很少提及音乐给他们带来的无可取代的纯粹境界。无论极高或极低的生活地位都无法改变音乐家是信息媒介者的角色,任何地域的民族音乐永远是本土文明信息的记载,一位贫穷的演奏家在音乐中的角色并不次于堂皇的作曲家,而作曲家也可能不过是用声音搞装修的声音工头。思想者也罢,工头也罢,媒介也罢,手里抓的都是抓不住的声音,别看它们是抓不住的,但只要它们的振动磁场在你周围,它们就形成了或诅咒或保护你的音墙。 这永远是很有趣的话题,就因为声音无形,它就是最强大最有魅力最难定义的存在,任何声音,重复多了就把人绕进一种迷魂阵、一种魔圈。阳气太多的声音重复多了,人冲动难当;阴气太多的声音重复多了,人沉沦难浮。哪个音水汽太大?哪个音火气太旺? 这书里面既没惊艳的故事,也没什么可嚼舌的私事。属于一种关于nothing (无)的书, 除了音 乐什么都没有,而音乐本身就是无。这书每句都是关于我们乐队和有关音乐的细节,却没有什么大目的大意义。这世上有种种活法,选择哪种,都不容易,都有很多细节牵扯进来。 只要留心,人的一生会一路遇恩师,帮助人走完命中注定的路。甚至一草一木、一音一符、言谈闲友等,都能无形中成为恩师,让创作成为身体和精神的养分而不是野心的重负。 这书的本意是献给我们的乐队——“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大部分关于乐队的内容是贯穿于和乐队键盘手季季的对话之间的。 季季是个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键盘专业、从三岁开始弹钢琴弹到二十三岁后对弹琴彻底绝望的孩子。从放弃到成为乐队的年轻键盘手,她属于那种喜欢思考音乐的孩子。鉴于她对乐队历史的兴趣,我就拿出些照片跟她唠叨。这些照片里的人都是一些整天围着音符转的人,他们的世界其实不大,外面的大世界也不见得都知道他们是谁。但这些人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带领人们进入声音世界的队伍。比如,李真贵是谁?他对于中国民乐界来说,是老大,民乐协会的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老系主任;对于外界来说,他是国宝级演奏家,但不见得所有人都懂得听国宝级演奏;对于我来说,他手下的鼓声展示了中国鼓的魔秘性,从他的演奏中我能听到时间的运动,那些声音是从过去渗过来的,而不像现在人手起手落不过是当下之音。我信命,和他的合作奠基了我们这个乐队的命运,我们这个乐队的存在命中注定会坚持很久。从成立到今天,已经从三代音乐家的合作变成了七代中国音乐家的同台演出。 因为有了李老师,才会有那场在2000年举办的引起巨大争议的民乐实验音乐会。那次音乐 会,奠基了“刘索拉与朋友们”中国乐队的存在。之后这个乐队以新的音乐理念贯穿,而不属于任何已经存在的流派。我为这个乐队创作的作品,不再屈从于任何委约的要求,无需仅仅当西方需要的异国之音,更放弃常规的人声表演与乐队的关系。吉他老五(刘义军)最近鼓励我说:“索拉姐,这块净土一定要保住呀。”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们所有人希望的。所有走进这支乐队的人马上就被声音的本质环绕,以被声音激发后的自我本质,再去激发观众。所有前后参与到这个乐队项目的人,都在声音中找到家人般亲近的乐队关系。 只有在做音乐的时候有毫无保留的精神,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能量,才会找到乐队成员之间及人与声音之间的无保留。因为有了这支乐队,“中国音乐”这个概念对于我这个学西洋作曲的人来说已不再是表面要强调的装饰音,而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中国音乐的神秘处正如一个丰富的野生花园,它的音乐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就像风随时会吹来的种子。听古曲的时候,你不知道琴者什么时候断句或延时,间歇多长,下句要去哪儿,因为每个演奏家处理得都不一样。这就是琴者自由意志的足迹。 但是听惯了常规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却已经对这种国风不熟悉了。中国古代琴曲的散漫正如同不守时的赴约者,说六点到八点才来。听惯了奏鸣曲结构的人,知道了什么时候绿灯走红灯停;但听琴曲,条条弯曲路,前者直走,后者绕走,还有蜘蛛行者。但只要这种漫无边际的声音爬进你的细胞建立了链接,你怎么跟着那声音走都条条路通“丹田”。 季季提到在音院,学西乐的和学民乐的有很不同的方式,似乎西乐学生面临大批的新乐谱,而民乐学生一生只面对有限的乐谱。其实中国有大量的古代音乐等待着发掘和重新整理记谱,只不过进入到当今课程的乐曲有限,就给了学生们错觉,以为民族音乐没有西方音乐的承传丰富。但是有意思的事情正是发生在所谓简单的民乐记谱中,因为那些乐谱看上去简单,又没有固定的演奏法,各派大师的指法都不同,因此给后者留了很多想象的余地去自由处理。这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精华处,哪怕一生只面对有限的乐谱,十岁的时候和九十岁的时候去演奏,是绝对不同的效果,那些乐谱中充满“不可预测”的潜在信息,可以用不可预测的手法来处理。一个人有可能花一生时间才能表现足了那些音符下的隐喻。所以来回换不同角度演奏一首曲子也能成为很有意思的事。 上多了音院的人,其实不见得比业余的音乐者对声音更敏感。但是经过学院训练的音乐家有更多掌握音乐的能力。对声音的敏感以及对音乐的掌握力,这二者如果兼顾,就有了在音乐中的大自由。耳中囊括天下所有的声音,才形成鉴别的敏感性,练习曲和技术含量不过是通向音乐大餐的品牌灶台厨具菜谱等等,如同真正的高等厨师在原始古堡或高级酒店或家庭小厨或野营宿地都能搞出美味来,对声音语言敏感就能沟通条条自由的声音大道,这种敏感性是对部分学院的训练课程也永远是对学院派音乐家的挑战。 怎么摆脱音乐语言的程式化永远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比如弹多了浪漫派音乐的人,表达愤怒或激情,永远逃不出去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式的影响。也有人会反驳问:那么现代派的愤怒和激情是什么?现代派的特征就是把任何容易鉴别的普遍性情绪都转化为极端的个人化情绪。因此,欣赏现代派作品,必须具备对人性扭曲的敏感度。 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音色和处理音乐语言的方法。作为一个受学院训练的作曲者,我几乎没有任何学院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里程碑野心,而不过自然认为音乐是生命的显示,我活着,我的音乐就活着,如果演奏我音乐的人能感受到我给予的活着的音乐提示,他/她本人也继续活在这个作品里。其实很多的现代音乐作品都不是碑文,不是停笔后就定圣旨,演奏家必须一音不差地甚至死照指法去演奏。今天的乐队成员必须具备即兴演奏的能力,才能对音乐和对自我有更深度的认知,从而演奏出今天这个时代的有重叠个性多联的声音。哪怕一音不差地照乐谱演奏,演奏者本人的光彩才真正是音乐的本质。 在这个乐队,没有主角,没有配角。我们共同存在,用声音对话。我在写谱子的时候想着每个人,如果我的乐谱能让乐手在设定的声音指向中释放其特有的个性,就算是写对了。 但什么是特有的个性?不去拼命找,谁都会以为那些别人设定好的程序就是自己会认同的。最近我去了一场著名的诗歌朗诵会,诗人是当代著名诗人,他诗歌的内容往往涉及沉重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哲理,但因为朗诵会上用的伴奏音乐是小资调轻浪漫伤感式的,如同小巷中的葬礼,或被离弃的怨妇阵阵哭诉,加上自告奋勇的朗诵者们用尽了煽情的长呼短嘘,我也竟然被煽得快哭出来了,但心里却抵制地说:这不对的,这个诗人的诗是悲哀的,但不是伤感的,悲哀和伤感不是一回事。终于,我忍不住了,站起来带着哭腔说,这音乐太煽情了,和诗的原意不符。果真,说完坐下,无论音乐再怎么煽情,朗诵者们再怎么煽情喊叫,我都没有同感了。 想寻找自己身上对普遍意义情感的特殊理解,必须要学会即兴创作,让生命告诉你,你其实是怎样的。练习即兴音乐是个漫长的人生经验,先是学会即兴对话,语出惊人,然后学会从身体里拿出“精性命之至机”的声音。 逻辑性的极致和疯狂的总和,就是中国古代人的灵魂。 读读明清小说,句句铿锵有韵,中国古代人和音乐其实是没有距离的,更别说在上古了,音乐主宰人为。人缩小,音放大。光无我或自恋都形不成完整的音乐,音乐需要天灵地气。正如音乐家接不到自己乐器的地气就演奏不好那乐器。这点,中国民乐家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那些乐器和本土的深厚历史。我们常说,一种“老”声儿,就是指声音和生活有漫长的关系。 大家都以为新的音乐仅仅是人们从未体验过的新声音,其实新声音中包含很多的老声音,这些老声音使新声音的出现不再做作矫情。 打击乐的“压缩性”张力我们常能从架子鼓、印度鼓、非洲鼓,甚至日本鬼太鼓那里听到,但中国鼓演奏的张力如何发挥?吉他演奏的疯狂忘形已经被吉米·亨德里克斯杀出先例,但琵琶和古琴演奏者如果要自然回到古代的追求至极状态,首先需要的是摆脱陈规而给自己创造一个至极的氛围。 演奏家如何克服演奏时手下发软或者“混”? 学院训练可以教会人如何控制、有意追求、精致处理等人为的技术,而建立自我则需要补充另一半:放弃、无意、自然、神性。这就是大师的演奏风格:放弃与控制,有意与无意,精致与自然,人神并存。 我不敢鼓励乐手练习灵魂出窍,反正我自己也不会。但在演奏音乐的时候,突然进入到忘我状态,这永远是音乐家最宝贵的瞬间。用声音来刺穿大脑,进入到那个面对声音、一切明了的境界,在那里,只言片语都显得多余。 在这本书里,我不断讨论能量爆发的事,因为在这个乐队成立后的十几年中,这一直是个经常要强调的话题,主要是我们谁都没在音乐学院里学到怎么发疯,那是个如此文明高雅的音乐高等学府,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是淑男淑女的样子,我也曾经带着这副样子和那些身经百战的美国蓝调音乐家对话,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把自己从自己身上扔出去。因此在这个乐队,我希望每个音乐家都有自己的独立能量而不是藏在别人的声音之后;每个人都能掌握爆发力与理性的关系、身体与声音的关系。这是个试图把音乐与自己拉近并把音乐拉进到听众的乐队;即便如此,却不失音乐本质的灵魂性和仪式感,通过这些人的无数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我们看到音乐家的真实生活,音乐家保持孤独同时重视团队之必要;是这些真实的音乐家向我展示着音乐的地气,由于他们我明白了那些所有和演出有关的小事,明白了一个优秀的乐队不仅要有团体性能量的聚集,并要鼓励每个人忘形的演奏瞬间,以及知道如何保护演奏大师们的特殊状态,等等。除此以外,还得吃好。 吃得好,对专业音乐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做音乐是脑力和体力兼顾的事情。有些演奏家去参加“辟谷”活动之后,瘦了许多,但是反应也慢了许多。让音乐家去辟谷,就好比让战士在打仗之前绝食。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乐队的特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被公平合理地“骂”,也就是每个人的错误和弱点都会得到全体的公开批评。年轻的演奏者们很多都被批评哭过,上了岁数的犯错也同样被年轻人指出,我们也得厚着老脸认错。我们互相监督着演奏过程中的每一个音和每一个瞬间,于是就有了这个小小的集体;于是读者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些在漫长的时间中摸索声音的人,简单愉快地活着。 ★著名作家、艺术家刘索拉暌违十年新书。 ★辑录上百幅珍贵照片,由刘索拉精选。锁线装订,全书四色印刷,装帧精美。 ★著名作家、作曲家刘索拉最新力作,畅谈解析“刘索拉与朋友们”中国音乐家们的探寻追索。 ★自传体散文随笔+访谈+友人对话+创作谈+百余幅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