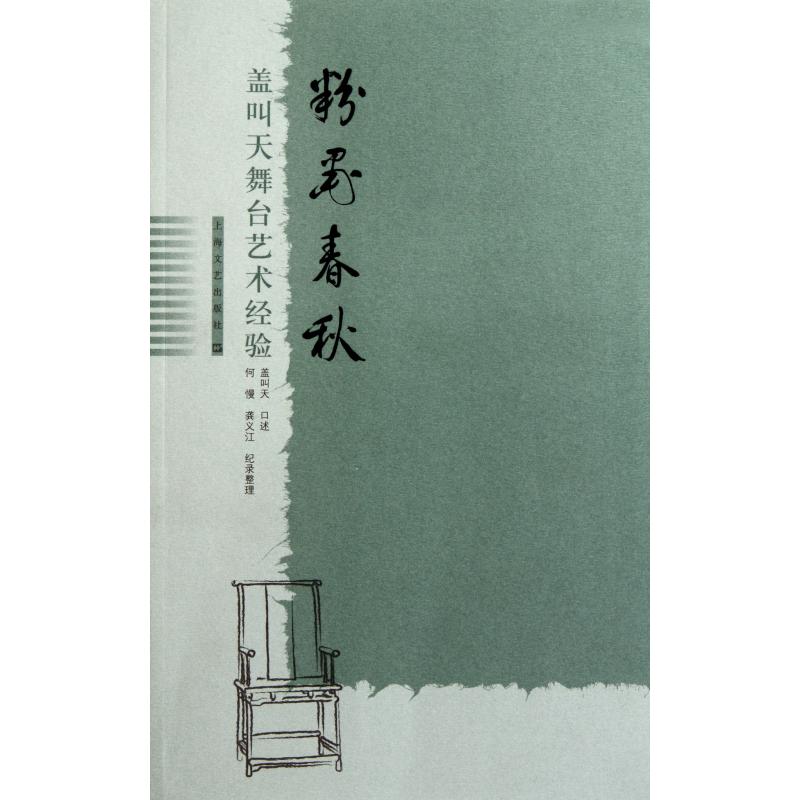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22.50
折扣购买: 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
ISBN: 978753214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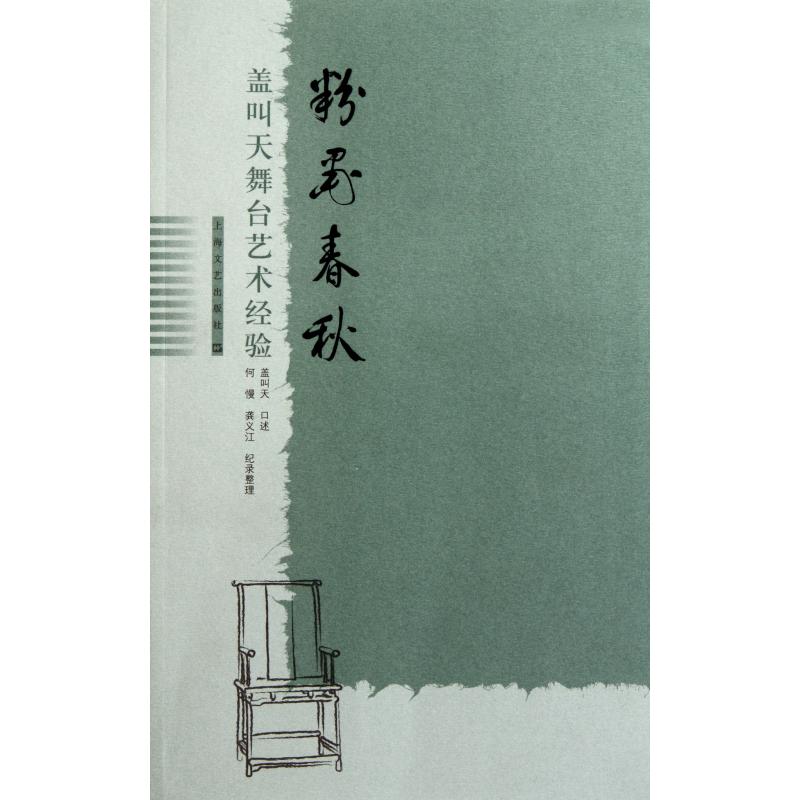
科班里,一天只吃两顿,早晨五点钟就起身,空着肚子练功,哪还像 现在的孩子们,有点心吃。黑面包的饺子,我们逢过年才吃那么一顿,孩 子们馋了一年,这会儿见了饺子可没命了,该只能吃三十的吃五十,吃不 下了还硬塞,直胀得路都走不动。 基本功练到七点钟,再打一点钟的把子,从八点到十一点学戏,吃过 午饭,就随大伙儿上戏馆。 冬天没衣服穿,记得老齐先生给我从旧衣铺里买来一条旧棉裤,人小 棉裤大,穿进去一拉,裤腰比我高出一个头去。就这一条棉裤怎么过冬? 无中生有,我想出个主意来了:把棉裤的下腰两边挖两个洞,手打洞里伸 出去,这不就成了棉背心?把裤腰从脑后翻过来,铰开改缝一下,就成了 个风帽,衣服、帽子都有了。晚上,睡的时候,手缩进来,把裤腰往上一 拉,连头带脸都盖住,再把风帽折叠做一个枕头,这就盖的、垫的、枕的 都齐全了。 这件棉裤连秋带冬,到五荒六月再换件单的。一年就这么两件衣服。 谈到练功学戏,我得先把科班里练功的顺序说一说。 头一年练的功是拿顶、虎跳、踺子、小翻这四样。先学拿顶,最初由 师父把着两腿,两脚朝上;再练能坚持住多少时间——头十天练到能站住 十个字,三个十天就添到了五十个字。第三个月完毕就能站到一百个字。 单这一个拿顶就得练上三个月。练的时候,师父在旁边按着一板三眼打着 拍子,所谓一个字,就是一个拍子,为什么要打拍子呢?一来拍子代表时 间,二来让学生心里跟着拍子默戏,就是拿顶的这会工夫,心里也不能闲 着。 拿顶的时候,一排十几个学生同时做这一个动作,假如其中一个支持 不住倒了,其他的人也都跟着被撞倒,那时候,师父就挨着个儿每人给一 顿揍,这叫“满堂红”。这以后就相互监督着,谁也不能错,因为哪一个 错了,倒霉的不是他一人,大家都得担待责任。 拿顶之后是虎跳、踺子,有了这基础,再花三个月时间,就可以练完 小翻,否则光练小翻练一年也不行。 一年过后,再用八个月的时间练四面筋斗。所谓四面筋斗,就是“出 场”“前扑”“蛮子”“捏子”四种翻的种类,能翻出场,就大体可以出 场跟着打武行了,所以叫“出场”。这以后,白天晚上上台练,上午在家 练。 四面筋斗之后再练“手上的”。所谓“手上的”是指各种拳法。空手 对打,有许多套数。目前武生大都只会这么三五套,能全套的已不多了, 它的套数有:擂头子、拉拳、拿法(统称“硬三套”)、拳头子、头趟擦拳 、二趟擦拳、三趟擦拳、上八掌、下八掌、五折、铁叉风、金刚头子等。 “手上的”练会了,再练把子。把子就是十八般武器的打法,每一种 武器基本都有五套打法。例如单刀把子,就有单刀与枪、大刀、双刀、棍 、空手夺刀这五种基本打法,叫五套,当然也不仅限于五套,其他武器也 都这样。 会了这些把子,基础有了,如何化法,真是“无尽无休”,得看你自 己怎么摘着用了 练的时候快了慢了都不行,慢了要松,紧了要崩,不紧不慢才是功, 一天三遍,一遍三回,一天不挪,百日成功。 这以后才学戏。武生开蒙大都是《探庄》《蜈蚣岭》《打虎》《夜奔 》这几出戏。头一出戏是个重要关键,譬如说先学《探庄》吧,得花八个 月时间,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含糊过去,这一出戏有如一 个“正”字,哪怕笨一些,别歪,处处按着规矩做,千万不能油。否则走 不上正路,再回头改就费事了。头一出戏基础没打好,以后的戏也学不好 。“慢就是快”,有了头一出的基础,二一出《蜈蚣蛉》只消四个月时间 ,三一出《打虎》只消两个月。有了这几出戏的基础,以后的戏给他说一 说,自己就能去揣摩着表演了。至于美不美,还得看各人自己,将来他窍 门开了,自己再去钻研。往往有些人自以为聪明,你一说他就会了,实在 还没有会,开蒙基础打不好,什么也谈不上。所以说头难头难,就是这个 意思。 在学戏的时候,科班里有句话叫“初开蒙,详训诂,学字音,明句读 ”。老师在教的时候,先把戏情、人物,给我们做详细的譬解,唱的时候 一字一音要念得清清楚楚,“山”字不能念成“三”“散”或“伞”。字 音念准确了,唱的时候不能光顾着唱得好听,离开了剧情、人物。譬如萧 恩被无辜责打四十大板,心中一股怨气,唱“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 ”的时候要把老英雄痛恨赃官的感情唱出来,咬牙切齿,恨不能杀了他们 才能消他满腹怨气。要是不顾人物,光顾着自己在这时候耍腔,潇洒是潇 洒了,可与人物当时的感情就不贴切了。 上面是说的学武生,要是学文戏,我们那会儿科班里有个循序渐进的 规矩。 学文戏先打孩子的戏学起,譬如《三娘教子》的倚哥,再是秀才、举 人、进士、状元。到了状元,因为状元还不是官职,金殿题试之后,放了 外官,那就打从七品知县的戏学起,再是知州、知府,然后位列三台,六 部大臣,入阁拜相,方才戴起白满。要是一开始就唱《徐策跑城》,戴着 白满,演老头儿,一咳嗽就不像。 我们学戏,唱知县官的戏,老师就问:“知县管的什么事?管多少百 姓?”从前,据说一个知县管六十四个村子的百姓,一个知州管三个县就 是一百九十二个村子的百姓,这些都得知道,这样知县见了知州是什么态 度,知府见了宰相又是什么态度,心里就有底了。 同时,千人一面还不行,譬如同是挂“黑三”的生角,《宝莲灯》里 的刘彦昌,《打鼓骂曹》里的祢衡,《四郎探母》里的六郎、四郎,《太 白醉写》里的李太白便各有不同。P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