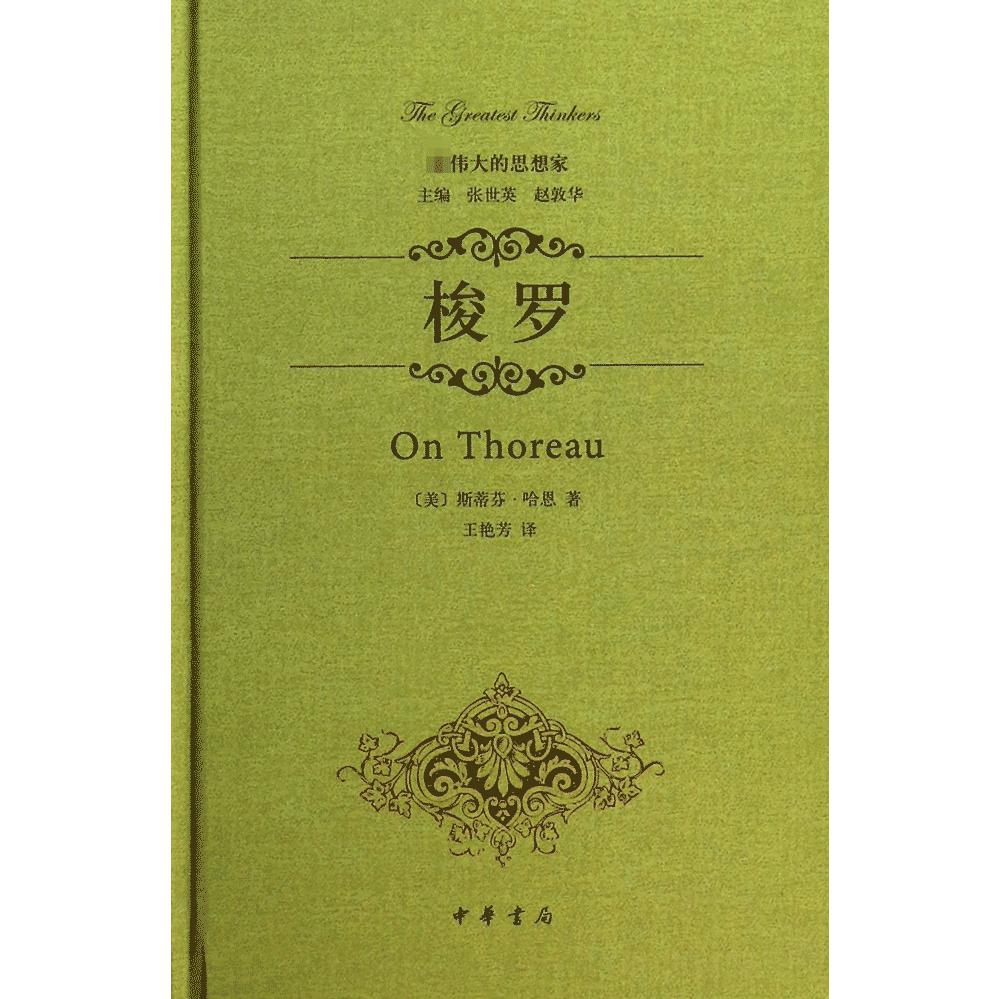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原售价: 20.00
折扣价: 15.00
折扣购买: 梭罗(精)
ISBN: 9787101097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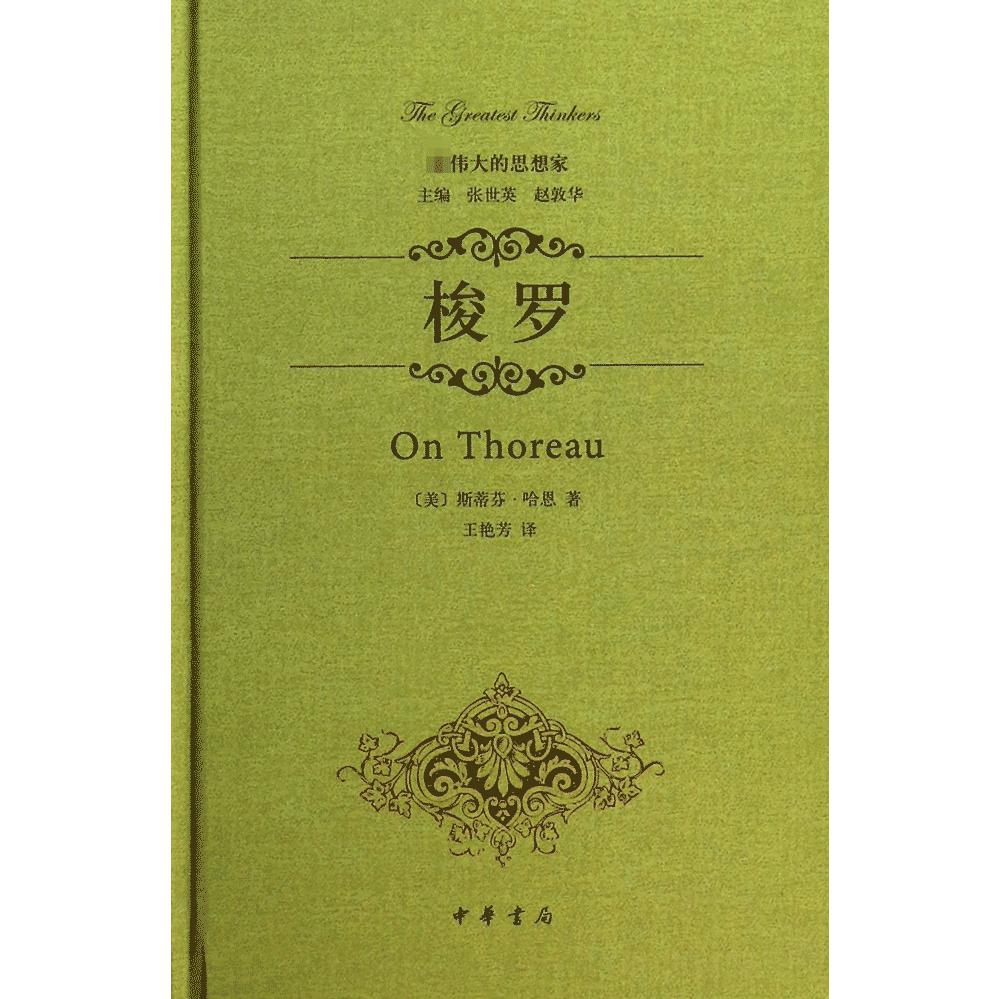
梭罗从1846年开始写《瓦尔登湖》,一直修改了 7稿,1854年才最终出版。那10年被认为是美国的文 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它们中间 最有名的是《红字》、《莫比?迪克》、《汤姆叔叔 的小屋》、《草叶集》。在属于此次复兴第一个阶段 的作家中,只有爱默生和爱伦?坡(逝世于1849年) 的作品要早于上述作家的作品。1836年爱默生发表了 “论自然”一文,居然有一本书那么长,之后又出版 了《随笔:第一集》(1841年)、《随笔:第二集》 (1844年)、《论自然:演讲集》(1849年)和《卓 越的人》(1850年)。当时流行的书主要是一些旅行 手册或“游记”(梭罗曾随意读过几本),麦尔维尔 的早期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模仿过这些书,但他 小说的叙述范围相当大且不断延伸,使之成为结合了 哲学思考的叙事。 虽然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显然是对独居森林实 验生活的一种叙述,但他对那些游记颇有轻视之意, 在书的一开始,他就说:“我乐意述说的事物,未必 是关于中国人和夏威夷岛人的,而是关于你们,这些 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瓦尔 登湖》,2页)梭罗这么说,似乎是要混淆人们对作 品类型的判断,而实际上同时他又给自己规定了一个 相对较小的、直接的受众范围。其间的双关语当然也 十分明显,在新英格兰方言里,“not so much(未 必)”不只是“not at all(一点也不)”的同义词 ,它的言下之意是“but possibly somewhat(有几 分可能)”;而“fain(想望,愿意)”不仅是“be eager(热切)”的意思,而且还是“feign(假装, 相当于make a pretence)”的同音异义词;至 于“said to live[(据说)生活(在新英格兰)] ”则是对“活着”的含义提出了质疑。这段文字的语 气,时而热情诚挚,时而又变成尖锐却含蓄的讽刺, 但那些强烈的用词使文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种语 气互相驳斥的尴尬境地——就像一个人无法同时诚挚 而又冷嘲热讽一样。 西方哲学的演讲或论文的传统形式通常只限于辩 辞、书信、对话、专题论文这几种形式,这样可以使 受众参与到主讲人或作者的问题中来。梭罗的叙述者 从对他意图的解释开始,引出了他的读者,因此他也 是由对他人的注意切入他自己的问题的。然而由于措 词不断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以及语词自身具有模糊 性,所以文章的意图似乎也在自我增加并分化,就好 像坚持让一个人距离非常近地倾听正在说的内容。传 统上,哲学家们通常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词语或名 称具有(或能够具有)清晰和特定的含义,而语言本 身即意味着事物或思想(或是两者)的逻辑顺序,因 而只需用言语或符号的方式进行推理就能得出结论。 当这些假设仍嫌不足,哲学家们则会趋于采用以下两 种补救措施的一种:(1)试图通过探究词根含义和 词源来清除连生词、难以捉摸的词义和行话(即用于 欺瞒外人、隐匿行内秘密的语言);(2)创造一些 新词,或者用抽象符号代替语汇,以获得更加严密的 外延。然而,尽管历史上有太多人使用这些措施,却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以致于语言本身成为哲学的一个 问题。因此,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对语言的关注是 作为哲学的一个主要争端存在的。对于哲学的传统目 的来说,语言被认为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障碍,因 为虽然它作为一种或一系列现象具有可释性,但这种 解释需要足够的稳定性,足以能够寻求永恒真理—— 而语言从来不具备这一点。但随着哲学模式开始有些 变化,梭罗的那些寓言和双关语的作用就显现出来, 使昔日的一路障碍变为一路通途。对语词含义的变化 趋势进行抵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强调它,词义会 更加滑向那一边。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梭罗一样,将 之开发为思想的一种资源。梭罗十分偏爱引喻和一词 多义,他甚至常常用纯言语的双关语转喻,将风马牛 不相及的能指联系在一起,就好像那语音的表面关联 意味着思想或现实的更深刻、更超验的关联似的。 梭罗一贯复杂的言词与先验主义者早期作品中的 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与小说家 (比如麦尔维尔)更接近。因为对哲学中仍存在的问 题,美国超验主义者开始并未采用批评的方式,而是 曾经一度几近于异常无知和冷漠(有人认为这实在荒 谬)。例如在爱默生早年的文章“论自然”(1836年 )中,他这样宣称: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是无法回答的了。 我们必须相信造物的完美性,以至于无论事物的秩序 引发我们的何种好奇,它都能满足这种好奇心。对于 人们提出的疑问而言,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一种形象 的解答。在将这种生活状况理解为真理之前,人们必 须将它视为生命本身。(《论文与讲演录》,7页) P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