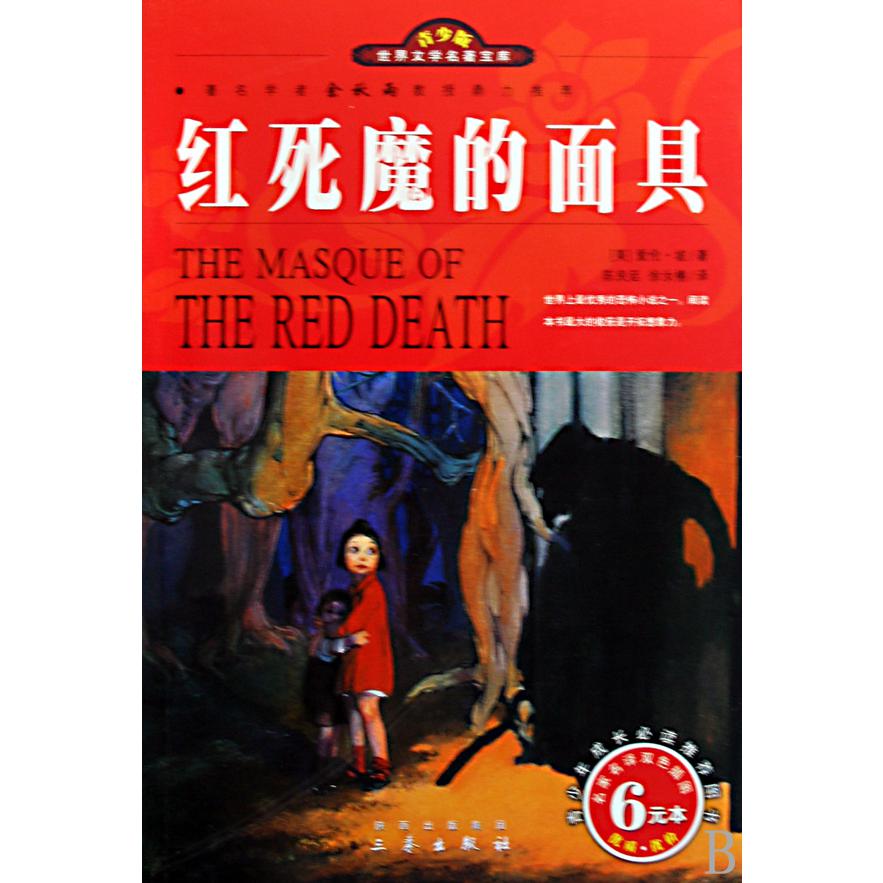
出版社: 三秦
原售价: 6.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红死魔的面具(名家名译双色插图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8073664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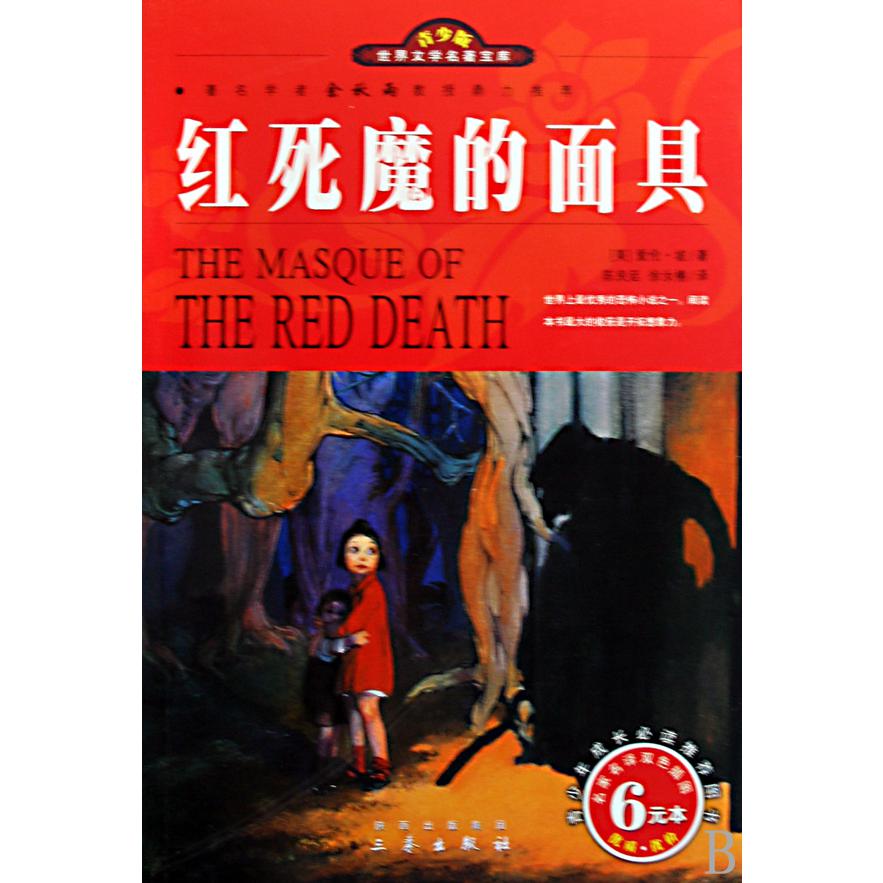
陈良廷,1929年生,广东潮阳人。光华大学肄业。上海作家协会会员。1951年起从事外国文学专业翻译,并与妻子刘文澜合作翻译文学作品。主要译作有《爱伦-坡短篇小说选》、《傻予出国记》、《儿子与情人》、《乱世佳人》及剧本《阿瑟·米勒剧作选》、《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四五十部。 爱伦·坡(Allan Poe,1809—1849),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家庭,3岁时母亲去世,由富商约翰·爱伦收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后因酗酒而退学。21岁时,进入西点军校深造,又因玩忽职守被开除。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写过诗歌、小说、文学批评,后发现哥特式的恐怖小说很畅销,而转向写恐怖小说,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835年,爱伦·坡与表妹结婚,十余年后妻子因病去世,他便从此终日借酒浇愁。1849年在巴尔的孽的一次彻底的痛醉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爱伦·坡一生刨怍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他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先声,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和现代派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因此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和“恐怖小说之父”。
话说“红死”在国内肆虐已久,像这般致命,这般可怕的瘟疫委实未 曾有过。这病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就是出血——一片殷红,令人发指。患者 初时感到剧痛,突然一阵头昏眼花,于是全身毛孔大量出血丧命。只要患 者的身上,特别是脸上一出现猩红色斑点就是染上这瘟疫的预兆,这时诸 亲好友谁也不敢近身去救护他和慰问他。患者从得病到发病,一直到送命 ,还不消半小时工夫。 可是荣王爷倒照样欢欢喜喜,他胸有成竹,天不怕地不怕。当他领地 里的老百姓死了一半的时候,他便从宫里武士和命妇中挑了一千名体壮心 宽的伴当,把他们召到跟前,然后带了他们隐居到他统治下一座雉堞高筑 的大寺院里去。这座寺院占地宽广,建筑宏伟,完全按照王爷那古怪而骄 奢的口味兴建而成。寺院四周围着坚固的高墙。墙上安着铁门。这批门客 进了寺院,便随带熔炉和大铁锤,把门闩全都焊上。他们横下心来,决不 留开方便之门,哪怕今后在里头憋不住,一时绝望发狂,也无从出入。寺 院里贮粮充足,有备无患,他们对什么瘟疫都不放在心上了。外界闹得如 何,悉听自便。再说伤心也罢,挂虑也罢,都是庸人自扰。王爷早已安排 好一切寻欢作乐的设备。有说笑逗乐的,有即兴表演的,有跳芭蕾舞的, 有演奏乐曲的,有美女,还有醇酒。寺院里应有尽有,尽可以安享太平, 寺院外却是“红死”猖獗。 在寺院里隐居了将近五六个月的工夫,这时外边正闹得天翻地覆,荣 王爷却开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化装舞会,请这一千名伴当玩乐。 这场化装舞会啊,真个是穷奢极侈。这里且容我把举行舞会的场地介 绍一下。一共有七间屋子,原是一套行宫。不过若在一般宫中,这种套间 只要把折门向两边推开,推齐墙跟,眼前望出去就一片笔直,整个套间一 览无遗。而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这位王爷就爱别出心裁,其余可想 而知了。这些屋子造得极不整齐,一下子只能看到一个地方。每隔二三十 步路的地方就有一个急转角,每个转角都可以看到新奇的景物。左右两面 墙中间都开着又高又窄的哥特式窗子,窗外是一条围绕这套行宫的回廊。 窗子都是彩色玻璃的,色彩个个不同,和打开的各间室内装饰主要色调一 致。譬如说,东厢那间悬挂的装饰是蓝色的——窗子就蓝得晶莹。第二间 屋子的装饰和帷幔都是紫红的,窗玻璃也照样是紫红的。第三问屋里一律 是绿的,窗扉也是绿的。第四间的家具和映人的光线都是橙黄的。第五间 全是白的,第六间全是紫罗兰色的。第七间从天花板到四壁壁脚都密密层 层罩着黑丝绒帷幔,重重叠叠地拖到同色同料的地毯上。只有这一间的窗 子,色彩同室内装饰不一致。这里的窗玻璃是猩红色的——红得像浓浓的 血一般。在这七间屋子里,摆得满坑满谷,或悬空挂着的大批金碧辉煌的 装饰品中,竟没有一盏灯,也没有一架烛台。在这一套屋子里,根本没有 一点灯火,也没有一点烛光。可是在围绕这套屋子的回廊上,每扇窗子对 面都搁着一只沉甸甸的大香炉,香炉里有个火钵,发出的光透过彩色玻璃 ,照得屋里通亮。因此呈现出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景象。可是在西厢的 黑屋里,火光透过血红的窗玻璃,照射到漆黑的帷幔上,却是无比阴森, 凡是进屋的人,无不映得脸无人色,所以男男女女没有一个胆敢走进屋来 。 在这间屋里,西墙前摆着一台巨大的乌木檀时钟。钟摆左右摆动,发 出的声音又沉闷又呆滞又单调。每当长针在钟面走满一圈,临到报时之际 ,大钟的黄铜腔里就发出一下深沉的声音,既清澈又洪亮,非常悦耳,然 而调子和点子又如此古怪,因此每过一小时,乐队里的乐师都不由得暂停 演奏来倾听钟声;双双对对跳着华尔兹舞的也不得不停止旋转,正在寻欢 作乐的红男绿女不免乱一阵子;这且不说,钟声还在一下下敲的时候,连 放荡透顶的人都变得脸如死灰,上了年纪的和老成持重的都不由双手抚额 ,仿佛胡思乱想得出了神。但等钟声余音寂止,舞会上才顿时一片轻松的 欢笑声;乐师个个面面相觑,哑然失笑,似乎借此为刚才那番神经过敏的 愚蠢举止解嘲。大家还私相悄悄发誓,保证下回钟响再也不这样感情用事 。不想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过了六十分钟,也就是说过了三千六百秒 钟,时钟又敲响了,这时又照旧出现一片混乱和震惊,引起大家沉思。但 是,尽管如此,这场欢宴还是规模盛大,让大家玩得痛痛快快。王爷的口 味毕竟古怪。他对色彩和效果别具慧眼。他对时兴的装饰一概不放在眼里 。他的设想大胆热烈,他的概念闪耀着粗野的光彩。有人以为他疯了,他 的门客却不以为然。不过要确定他没有疯,少不得要听到他说话,见到他 的面,跟他接触过才行。 在举行这个盛大宴会之际,七间屋子里那些活动装饰大多是他亲手指 点安排的。化装舞会的声光特色也是根据他的主导口味设计的。不消说得 ,一切都搞得奇形怪状。真是五光十色,变幻无穷,令人眼花缭乱,心荡 神驰——差不多都是在《欧那尼》里看见过的场面。到处都是光怪陆离的 形象,四肢和打扮都不伦不类的人。一切梦幻般的奇景,只有疯子头脑里 才想得出这种花样。固然有不少东西美不胜收,但也有不少东西伤风败俗 ,有不少东西稀奇古怪,有的叫人看了害怕,还有许多叫人看了恶心。事 实上,在这七间屋子里走来走去的人,无异一群梦中人。这些梦中人映照 着各问屋子的色彩,不断扭曲着身子,竟惹得乐队如疯如狂,宛若奏出配 合他们步子的回声。未几,那间黑屋里的乌檀木时钟又敲响了。于是,一 时除了钟声之外,万籁俱寂,声息全无。这些梦景顿时凝住了。但等钟声 余音消失——其实只有一眨眼的工夫而已——人群中便有一阵几乎强制抑 制的轻微笑声,随着远去的钟声荡漾着。于是音乐又一下子响了起来,梦 景重现,香炉上散射出来的光线,透过五颜六色的窗子照着憧憧人影正扭 曲得更欢。但是,西厢那一间,那些参加化装舞会的还是没人敢去。夜色 渐阑,从血红的窗玻璃中泻进一派红光;阴森森的帷幔那片乌黑,令人魂 飞魄散;凡是站在阴森森的地毯上的人,一听到近头乌檀木时钟发出一阵 闷郁的钟声,无不感到比在远头其他屋里纵情声色的人所听到的更肃穆、 有力。 可是其他屋里都挤得满满的,充满活力的心脏正扑腾扑腾跳得起劲。 狂欢方酣,不觉钟声当当,已入午夜。于是,正如上文所述,音乐顿时寂 然,双双对对跳着华尔兹舞的也不再旋转;一切照旧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 休止。但是,这回时钟要敲十二下,因此玩乐的人们陷入深思默想的时间 更长了,脑子里转的念头也更多了。也许,正因如此,最后一下钟声的余 音还未消失的时候,大家才有闲工夫察觉到来了一个从未引人注目过的蒙 面人。大家顿时窃窃私议,来客的消息就此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宾 客间一片唧唧喳喳,纷纷表示不满和惊讶,末了又表示恐惧、害怕和厌恶 。P1-3